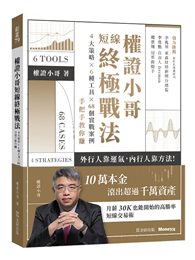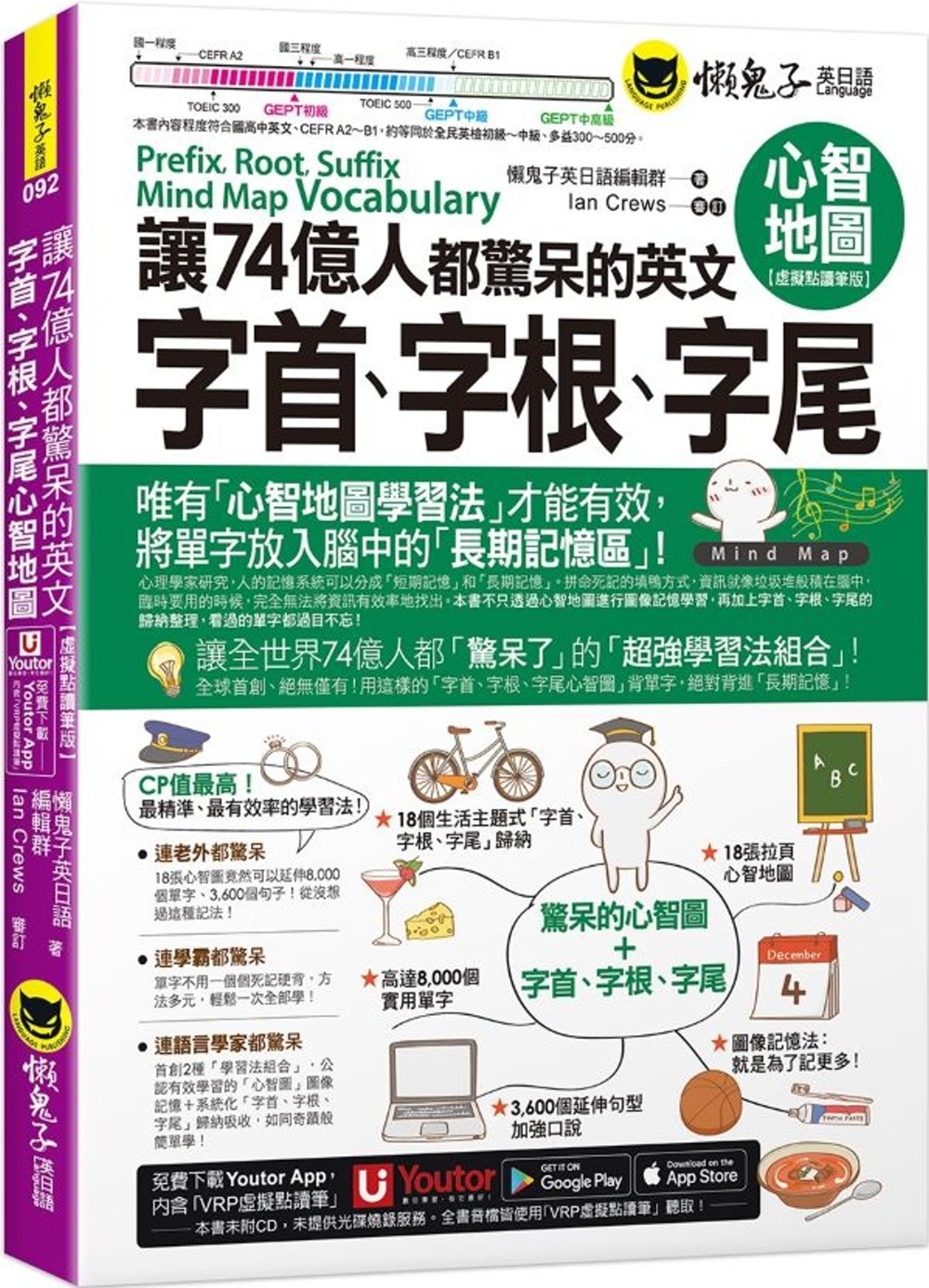序
研究科學的求真精神
最近時代週刊上報導了兩次有關科學家捏造實驗證據以圖享名的事實,事情都發生在美國極負盛名的研究機構,研究主持人也都是在科學上已有非常成就的專家,然而這樣的醜聞竟發生在他們的實驗室裡。雖然捏造實驗證據的行為都是他們手下的年輕科學家擅自作為,但是這種醜聞畢竟使他們的令名沾污。在這兩則報導中,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兩案的主角都是年富有為的傑出青年科學家,在他們研究的領域裡都是極具潛力的優秀人員。為什麼他們要在前途似錦的時候做出這樣愚蠢之舉自毀前程呢?是不是今天科學研究從業者的道德有了問題?那些前輩科學家們孜孜不息為求真理可犧牲一切的清高風範已不復存?
當然,「世風日下」是個普遍性的老原因。不過筆者以為,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科學研究」這一門「行業」的本質已隨時代而改變,因此其從業人員的動機、態度乃至抱負都與上一代有了相當大的差異。在過去,「科學研究」是純學術性的,從事研究者是以興趣與熱忱獻身於知識領域中的探求,對於「求真」抱著極為虔誠的態度,所求者不過是好奇心與求知慾的滿足。在那時,研究科學是無所謂利欲的,有利欲的人也不會獻身其行列。
今天的「科學研究」是一門相當「企業化」了的行業,在人浮於事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從業者是守住一份賴以生活的工作,未必有那麼多的興趣和熱忱,也就未必有那麼多的虔誠和執著。如同其他任何一門行業一樣,這其中難免有不少人為求名利而不擇手段。前面所提到的兩則醜聞中的主角在東窗事發之後,都曾表示他們生活在「極度的壓力之下」。他們捏造實驗證據的行為固不可恕,然而他們所說的那種「壓力」是可以瞭解的,從某個角度來看,甚至是值得同情的。
「科學研究」是一條艱苦而寂寞的路,愈是前進尖端的研究,那種在黑暗中摸索的艱苦與寂寞也愈甚,因為能夠與你分「享」這種滋味與經驗的人少之又少。在摸索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挫折猶在其次,那渴求得到答案的焦慮與面對問題所必具的冷靜造成了長時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心智上往往造成極大的壓力。而今天西方國家的科學家還要再忍受環境所加諸的另一種壓力,那就是在類似企業化及極端強調個人成就的制度下所產生的激烈競爭。在這種種壓力之下,一些急於成大名的科學家,難免就放棄了「求真」的執著而走上欺世盜名之途,這是整個科學界的悲哀。
反觀我國,科學發展可謂剛剛起步,真正在潛心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沒有多少,這裡面也沒有什麼激烈的競爭,前述歐美科學界的種種情形在這裡可說並不存在──即使有,也不嚴重。然而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者也有我國特有的環境壓力,這種壓力出自完全不同性質的來源,那就是國人對於從事研究者急於要求表現成果。雖然在事實上,真正關心國內科學發展的國人並不多,但至少在輿論上總是以「對國人作交待」來要求成果。基本上,這是一件好事,任何有良知的科學研究者在花費了納稅人的錢以後當然應該有所交待。但是這種壓力如果過於迫切地要求每項研究工作都能立竿見影,再加上新聞報導人士基於「求好心切」的心理急於報喜「以慰國人」,那結果是促使部分名利心重的研究人員或大吹法螺或誇張成果,剛擬好尚未動手的計畫就奢談成果,有了一點初步成績就大言趕上國際水準,一點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可以招待記者製造新聞,在報章上一登再登,一辯再辯。其實這些初步成果及「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如果以學習技術及訓練人才的眼光來看,原不失為極寶貴的經驗,對於進一步的研究發展可能極有價值,但是在過分渲染之下,連它原有的價值都為之減低。這是對國人作交待還是在欺騙國人?
其實,我們的科學研究方才起步,大家不必因為急著馬上要弄出一些「驚人成就」來向國人交待,而喪失了在科學上求真的精神。等到科學的水準達到一定的程度,總有一天,國內報紙上頭條新聞所報導的驚人成就,也會在國際報章上成為頭條新聞。
劉兆玄
1974年12月
編按:劉兆玄,台大化學系畢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1971年返國,任教清大化學系。1979年起,開始出入學界、政界,曾任清大理學院院長、清大校長、東吳大學校長;行政院科學委員會企劃考核處處長、國科會副主委、交通部長、國科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院長。維基百科有傳。1979年之前,曾積極參與科月,並曾擔任總編輯,「大家談科學」欄目即其所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