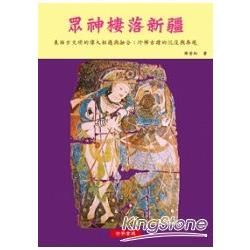作者序
令人眩惑的新疆
新疆是一個人們似乎非常熟悉,卻又異常陌生的地方。
儘管關於新疆的一切,車載斗量,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誰能真正描摹出新疆的面容。
綿延的雪山,茫茫的戈壁,無垠的沙海,星星點點的綠洲。最高和最低、最冷和最熱、最徹底的荒涼和最充裕的富足,都在它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最強烈鮮明的方式一一陳列。
新疆對於世界來說是一個長紗蒙面的美人,關於她美貌的傳說像風一樣四處傳播,但誰也沒有真正一睹她的容顏。
新疆是任何一個個體生命都不可能窮盡的,儘管這個生命一生都可能和新疆廝磨在一起。除非,這個世界上產生了一種超常的智慧和偉大的心靈,而這個生命恰恰是上天為了了解新疆所造的。
新疆太大了,但更主要的不僅僅是它的大。它是造物一時性起以非常規手段造就的,要不然為什麼中國最大的盆地、最大的沙漠、最長的內陸河、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泊,這些偉大雄奇的自然都會集合在新疆大地上?
從溝溝有黃金的阿爾泰山,一下跌入荒涼的準噶爾盆地;從上可捫天摘星的天山,再次落入塔里木的茫茫沙海;從喀喇崑崙山海拔8611米的喬戈里峰,到吐魯番盆地海平面以下154米的艾丁湖,新疆這種大起大落的地勢變化,散發著一種驚險的美麗。
在新疆,你可能一天之內體驗到四季的轉換。山下是烈日炎炎的夏季,愈往山上走,氣候便依次變為春季、秋季,最後是白雪皚皚的冬季,這是一種濃縮的極端感受。
新疆有兩種最主要的顏色,一種是黃色,一種是綠色。
黃色是大片大片的戈壁沙漠,綠色是小片小片的綠洲。黃色的戈壁沙漠實在是太大了,要占新疆面積的96%左右;綠色的綠洲又實在是太小了,只有大約4%。新疆人就居住在戈壁沙漠中的綠洲上。
黃色的沙漠戈壁是亙古的荒涼,任何生命不能生長的不毛之地;但那小小的綠洲又是那樣的豐盈飽滿,充滿了勃勃生機。「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阿娜爾汗的心兒醉了……」如果你在葡萄成熟的季節走進新疆沙漠中一塊塊如阿拉伯飛毯一樣的綠洲,你的心兒一定比阿娜爾汗還要沉醉。新疆綠洲的果實應該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因為它經過沙漠生存與死亡的反覆錘鍊,它飲過雪山冰川最清涼純淨的甘露,沐浴過天空無遮無攔的燦爛陽光。
然而,這一切都是新疆的自然屬性,不管怎樣還是可以讓人感知和理解的。但是,幾千年的新疆所變幻出的色彩卻足以讓人眩暈。誰能搞清楚新疆的人種起源?那些今天我們看到的黃皮膚、白皮膚以及黃白混雜的人和民族,他們從哪裡來的?他們經歷了怎樣的融合與混血?還有新疆的宗教,在今天的伊斯蘭教的底色之下,誰又能分辨出它雜合了多少佛教、祆教、景教的色彩?
新疆作為歐亞大陸的地理中心,這裡曾是華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埃及和兩河文明的交匯之地,現在還存留著非常古老的佛教石窟、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古希臘羅馬的有翼天使遺跡。這裡曾演繹過中亞不知多少古代民族、多少城邦國家的興衰歷史,在過去的人類七八千年的文明史中,新疆這個地方一直都是人類文明相聚的歡場。世界幾大文明千里迢迢而來,原本這裡僅僅是一個人類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誰都沒有想要在這裡駐足和經營,但不經意間,這個十字路口,卻成了人類幾大文明相遇碰撞的地方,也是重新受孕融合的地方,最後也成為新的文明誕生的黃金產床。
這黃金便是那金燦燦的沙漠。現在的死亡之地,過去的人類家園。文明的歡聚之地,文明的埋葬墳場。一些城邦失落了,文明死亡了,但另一些文明卻以另外的方式活著,一直活到今天,決定著今天的新疆性格,決定著今天的新疆顏色,駁雜而紛呈,迷離而絕世。一層文明覆蓋著另一層文明,一滴血液裡有著千萬種幻化。活著的文明繼續活著的方式是混血,死亡了的文明卻因為死亡而保持著純粹與純潔的模樣,在黃金般的沙漠之下。當它們一個個再一次浮現的時候,它不僅僅向人們言說著歷史曾經怎樣,更在多重維度裡證明著人類的種種可能性—人類是什麼,人類為什麼要創造文明,以及人類可以達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間。人類想像力的浩淼無邊,如何像漫漫春水越過堤壩,四溢到整個宇宙空間。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被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問及「你喜歡在歷史上什麼時候的哪個地方出生」時,湯恩比回答:「我希望能出生在西元紀年剛開始的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古伊朗文明和古老的中華文明融合在一起。」
西元紀年前後是人類文明的萌動期,地球上被地理空間阻隔著的、互不知道彼此存在的人類,突然之間像是聽到一聲號召,或者是被神奇的上天之手摸過頭頂一樣,開始了智慧的生存。文明的星星之火被點燃,照亮了野蠻的黑暗,並成為人類文明的經典範式,遷延幾千年至今。蒙昧不再,西方古希臘文明、東方的中華文明和恆河邊的印度文明如盛花般綻放,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基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散播遠方,宗教、哲學、文學、歷史、人類的精神生活達到了從來沒有過的頂峰。人類目光如炬,對所有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人類像一個青懵的少年,渴望探索所有處於黑暗中的未知的世界;人類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追問,關於人,關於神,關於大地,關於宇宙……
人類開始了互相的尋找,冥冥之中的神指引著行進於路途的人們。現在再看世界上第一個人繪出的第一份世界地圖,可能會覺得人類關於自己生存地球的想像是那麼可笑,但正是這謬誤百出的想像,指引著人們走到了今天。
湯恩比一直在尋找著人類文明融合在一起的地方,他把這個地方稱作是「詩意的棲居」。這個人類詩意的棲居之所,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處,這就是新疆。
或者用新疆這個名稱過於狹隘了,新疆只是一個近代的稱謂,這個稱謂的變化,意味著國家和邊界的強烈意識和現實。而在這個地方被稱作西域的時候,或者在被稱作西域之前更古老的時代,它是那麼的遼闊,那麼的無邊無際,它是歐亞大陸的最平坦寬廣的胸膛。這裡的人類最先學會了駕馭馬,創造了馬車,當風起時,草綠時,太陽沉浮四季輪轉,感知到大自然節律的人類便跨上馬,自由自在地遷徙飄蕩,種族與種族之間,城邦與城邦之間,傳遞著文明的,或明或暗的訊息,不同的文明就這樣相遇、交合了。
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地方像新疆這樣,有過幾大文明的匯集,有過無數民族的融合了。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會同時並行20多種語言文字?又有哪個地方會有幾大宗教共同被信奉的奇觀?所以,現在新疆隨便一個沙漠裡死去的古城,或者一個現在還活著的地名,考證起來都會讓一個飽學之士迷惑。樓蘭、尼雅的千古之謎怕是永遠也解不開了,而烏魯木齊這樣一個地名,究竟是來自哪個民族,哪種語言,專家們也在爭論不休。
有那麼多的民族像白雲一樣漂浮過這片遼闊的土地,消失、融合,再消失,再融合。五千年來在新疆生活的民族膚色漸漸變深,最後白色上染上了一層太陽的金黃。
有那麼多的文明在這裡一次次地受孕、混血。文明相遇時迸濺出的火花,落入沙漠、綠洲、高山、盆地,照亮了歷史的夜空。
但是在歷史的某一個時段,沙漠向外擴張了200—300公里,古城湮沒,珍寶遺失,沙漠掩埋了一切。
沙漠以千年的寧靜保留了它們死亡時的模樣,居民的門扉虛掩著,主婦的紡車上還掛著一縷沒有紡完的毛線,國王的公所裡泥封的簡牘還沒有打開閱讀,舉世珍寶鮮艷如新。
眾神曾棲落於新疆。上個世紀,西方的地理歷史學家們驚奇於東西方文明的傳播和交流,他們在總結了這種交流的特質後,將其稱為「絲綢之路」,但這僅僅是一條物質的大道嗎?就算它是一條人類物質文明交流的道路,它又是怎樣的一條路啊!
它是一條由駱駝柔軟的腳掌,在堅硬的礫石上踏出的、纖細而渺遠的路。在這條道路上,源源不斷的各種商品以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流動著;世界幾大古老文明以如此細微的孔道溝通、交流、碰撞,各種音樂、繪畫、雕塑、舞蹈藝術,各種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生活方式都在這裡一一呈現;印度的佛陀、伊斯蘭的真主、基督教的耶穌也從這裡翩然走來……
它似路非路,有著路的名字卻沒有路的形態,有著路的實質又缺乏路的足夠承載;它似乎是抽象的,又似乎是具體的;它似乎是狹義的確指,又似乎是內涵複雜廣博的模糊概稱……它似存非存,似斷非斷,若隱若現地穿行在戈壁大漠、雪山草原之間,像一條突然受驚、快速爬行的蛇,稍一愣神,倏忽間便不見了蹤影。
它有一種夢幻的色彩,一種超現實的性質,然而又是如此實實在在地臥伏在歐亞大陸遼闊的土地上。它遠遠超越絲綢所能涵蓋的範圍,實際上在張騫鑿通絲綢之路之前,人類的先行者已經走在這條路上。草原上那些沉默的石人;太陽墓地裡那些白皮膚金頭髮的男人;小河墓地那些沉睡在紅色的死亡殿堂裡的美麗女人,他們或許是最早來到這塊土地上的人類。他們匆匆地離去、消失,沒有留下他們為什麼要來、又為什麼退出歷史的資訊,甚至,他們連一個背影都沒有留下。
我們今天的樣子和今天的生活是怎樣地被早在遠古時代就決定了的?在人類命運的十字路口,什麼樣的事最終成了我們不可擺脫的前世決定?如果佛說的輪迴真的存在的話,那麼是怎樣的力量決定我們向這個方向走,而不是另一個方向?宿命,當我們回看人類文明的生長與毀滅,如看一朵花的萌動與凋零一般,宿命的軌跡猶如潔白雪地上的飛鴻印跡,那感覺是如此的觸目驚心。
新疆大漠戈壁上、高山河流旁偶爾遺留下來星星點點的人類文明痕跡,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裡被一個一個地收拾起來,每一個接觸它的人,都會被它迷惑吸引,一個個探險家、考古學家、史學家、文字學家雖付出終身的努力而收穫微薄,它們可能是世界上最難解釋的東西,有的一眼就能辨識出它的文化蘊涵,有的不管你如何努力,它都是天一樣大的謎,你愈熟悉它,它就離你愈遠,愈不可解讀,就如夏夜裡跳動的磷火,有火的光亮,但卻幽冥而靈異。
但是,你若想揭開新疆蒙面美人的蓋頭,就必得回到她的過去。這是一個身世複雜的美人,她的每一眼秋波都深如海水,幻如夢境。
南香紅
201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