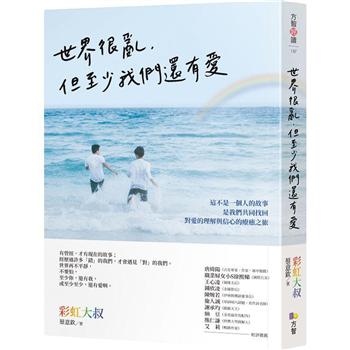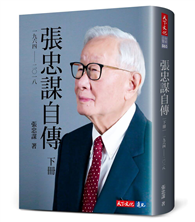第一因 解體迅速
拜訪匠千曉,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三月二十日,春分;那一天我閒得發慌。
妻子利用連假期間,帶著五歲及兩歲的女兒們回娘家過夜;本來我也該同行的,卻藉口時值入學考前後、諸事繁忙,一個人逃之夭夭。這牽涉到某個教人心煩的緣由。
最近,岳父及岳母間的氣氛變得極為險惡;這是因為岳母不知哪根筋不對勁,都一把年紀了,竟然去考了張汽車駕照回來,之後又立刻開車撞傷了人。
對方的傷勢並無大礙,但接下來可就難捱了;岳母每天都必須到醫院報到。
除了探病,還得代替對方的家屬照料對方。我不要求賠償金和醫藥費(結果還是付了),只希望妳能以態度表現出誠意──這就是對方的說詞。
嘴巴上說得動聽,其實根本是把岳母當成女傭使喚。岳母必須代替那些從未現身的家屬,上自飲食、下至收拾一手包辦,還得忍受對方挑三揀四,伺候一整天。
岳母忿忿不平地埋怨自己受人虐待。只要她晚點到醫院,或是表示今天會找人代班,想請一天假,對方便會面露輕蔑之色,只差沒出口罵她是卑鄙小人。幸虧妳撞到的是我這種好人,才能以這麼點負擔了事,但看看妳那種沒誠意的態度,像話嗎?──彷彿自己又遭遇了什麼災難似地,將受害者意識發揮得淋漓盡致。
身心俱疲的岳母有些憂鬱傾向,開口閉口抱怨自己已經忍無可忍;起初岳父還跟著氣憤、感嘆,但大概是聽得心煩了吧,開始責備起岳母來:「誰叫妳一把年紀了還考什麼駕照!」「我已經被欺負得夠慘了,連你都來責備我?你應該幫我說話的啊!」當然,岳母也變得更為歇斯底里。
因此,每當拜訪妻子的娘家,我總是鬱悶不已。岳父與岳母都要我聽他們的苦衷、幫他們說話;要是插手管這檔事,搞不好接下來便輪到我得憂鬱症。
不過,逃是逃出來了,這個假日我並未安排任何節目;既然是以入學考前後諸事繁忙為藉口,我便意思意思到了學校去,但果然不出所料,並沒多少工作可做。別說國中入學考不考英語了,就是其他科目也早已考完。
即使如此,我還是乖乖地解決雜務,等真的沒事可做了才離開學校,卻又無意回到無一人的家中。要去喝一杯嘛,天色又嫌太早;再說,一個人喝酒未免太寂寞了。
正當此時,我想起了千曉。他八成連這種日子都還獨自窩在公寓中吧!
立即登門拜訪之下,千曉果然在家;或許是覺得冷吧,他膝上蓋著毛毯,正看著報紙。我暗想著:「不會吧!」環顧六張褟褟米大的房間,果然還是老樣子,不見暖爐,也沒有暖氣,和學生時代時一模一樣,教我有些傻了眼。這個男人並非沒錢,卻從未在自己的房間裡裝設冷暖氣。
不光如此,他也沒車子,甚至無意考駕照。這我還能理解,但他竟連腳踏車也沒有,移動工具就是自己的雙腳。
問他為何什麼都不買,他只回了句:「麻煩啊!」──大老遠地走到超市購物就不麻煩嗎?真搞不懂他的邏輯。難怪學生時代時,老教授們總叫他「仙人」或「老頭子」。
「保彥啊?稀客稀客。」大概是看見我手上提著罐裝啤酒,千曉的態度顯得格外地熱絡;他這個人最喜歡喝白酒了。「怎麼突然來啦?」
「沒什麼,因為閒著沒事幹。」
「工作呢?」
「今天是假日。」反正這個男人肯定連今天是星期幾都搞不清楚。「再說現在是春假期間。」
「春假啊?當老師真好耶!有長假可放。」
「你在講什麼啊!你一年到頭都放假吧?」
都幾歲人了,千曉還沒有固定職業,不過心血來潮時倒是會打打工。
「唉呀!這麼說我會難過的。」看來伴手禮啤酒奏了效,無論說什麼,千曉都笑嘻嘻的。「欸,慢坐啊!說歸說,你不要緊嗎?太太呢?」
「她回娘家了。」其中的緣由略過不提,但我可不希望被想歪,因此又加上一句:「去給外公、外婆看看孫女,明天中午就回來了。」
「嗯……既然這樣,我們就慢慢聊吧!」千曉請我在僅有的一張坐墊上坐下。他看來格外心浮氣躁,肯定是想快點喝啤酒。
見狀,我從塑膠袋中拿出啤酒罐遞給他;千曉接過手後,高興得簡直不像樣。能讓他這麼歡喜,我這伴手禮也算是值得了。
乾杯後,我不經意地環顧四周;這房間還是一如往昔,除了從書架上滿溢而出、宛若繁殖過後似的大量書籍,以及滾落滿地、猶如戰死兵士般的空酒瓶之外,什麼也沒有。
我看了千曉方才閱讀的報紙一眼,略感意外;本以為那是今天的報紙,沒想到卻是去年十月的。旁邊還放了幾本週刊雜誌,也是去年的。
「你還特地翻這些舊東西出來看啊?」
「咦?哦!那個啊?因為櫥櫃塞滿了,不知道怎麼整理,其他的我全丟啦!舊報紙和雜誌很有意思,一開始看就停不住啊!」
「為什麼只留下這些?」一定刊著相當有趣的報導吧!才這麼想,千曉果然指向某塊版面,上頭印著這樣的標題──『分屍懸案出現重大轉變 嫌犯被捕 宣告偵破』。
這個案子我也有印象。我忍不住停止仰罐飲酒,從頭瀏覽報導;仔細一看,放在報紙旁的全是刊有此案特輯的週刊雜誌。
頭一位犧牲者,是個名叫松浦康江的三十八歲女性。
去年六月五日傍晚,從高中放學回家的松浦理惠發現了母親被殺後的屍首,陷入半發狂狀態。那屍體並不尋常,不但被脫得一絲不掛,還分割為頭部、身體及雙手雙腳等六個部分。
繼姊姊之後,同為高中生的弟弟雄一也回到了家,同樣陷入恐慌狀態;附近鄰居聽見了孩子們的喊叫聲,才報了警。
直接殺害方式是絞殺;凶手先以鈍器毆打死者後腦,待死者昏厥後才勒死她。被割斷的脖子上纏著凶手用來犯案的絲襪,已證實是死者之物;似乎是凶手脫下後直接拿來充當凶器。
殺死被害人後,凶手便進行分屍;切割屍體用的鋸子是松浦家的,直接棄置於現場,上頭無任何指紋。
這是個獵奇色彩極為濃厚的凶殺案。比方說,松浦康江被分屍前,雙手及雙腳似乎抱著自家和室柱子,手腕及腳踝則銬著玩具手銬;死者在這種姿勢下被砍斷了一雙手腳,那像圓木般滾落在地的雙手及雙腳各自被手銬繫在一塊兒,身體倚著柱子,頭顱則掉在身後。
康江的臉部及手臂上有著被拖曳過的擦傷,現場並留有案發當時她身穿的套裝,上頭沾滿了泥巴;由此推測,凶殺現場並非在松浦家,而是在戶外。
不過,分屍現場應是松浦家的和室無疑。由飛濺在地的血跡及脂肪痕跡,便可一目瞭然。
綜上所述,凶手在戶外殺害康江後,又將屍體搬至松浦家,並將她脫個精光、綁在柱子上,以手銬銬住手腳,才進行分屍──這便是第一件案子的概要。
第二件案子是發生於一週後的六月十二日晚間,被攻擊的是土居淑子,二十三歲的上班女郎。
從友人婚宴返家的雙親發現了全身赤裸且不省人事的女兒,立刻報了警。
淑子與松浦康江一樣抱著柱子,手腳銬著手銬,脖子上纏著自己的絲襪。她與前案如出一轍,後腦被毆,頭部負傷;只不過凶手似乎相當慌張,脖子沒勒實,是以淑子不久後便清醒過來。
凶手慌張的原因顯而易見;淑子的雙親發現的不只是女兒的慘狀,在淑子被縛的同一個房間裡,還躺著一具男屍。
那男子名為坪井純也,是個二十五歲的上班族,正與淑子交往中。他的腹部被菜刀刺穿,而凶器菜刀是土居家之物。
警方判斷第二件案子的凶手與之前殺害松浦康江的凶手為同一人;其中一個理由是手法酷似,而最重要的理由是──附著於坪井純也屍體上的頭髮。
鑑定結果顯示頭髮為松浦康江之物,可能是附著於凶手衣物上的頭髮,在凶手持菜刀衝撞之際轉移至坪井身上。
凶手以為淑子單獨在家而潛入,並與松浦康江時一般,毆打淑子頭部,趁她昏迷之際褪去衣物,以手銬限制她的行動,並企圖用她的絲襪勒殺她。假如凶手的計畫順利進行,淑子將與康江一樣在死後被分屍;事實上,現場的確放置著鋸子,同樣是土居家之物,且不帶任何指紋。
然而,此時卻發生了凶手預料外之事──犯案途中,淑子的男友坪井出現,目睹他行凶的一幕。凶手慌忙刺殺坪井滅口,而這起預定外的殺人似乎令凶手方寸大亂,誤以為淑子已死,便匆匆逃走。
這成了凶手的致命傷;根據淑子的證詞,模糊的凶手形象浮出水面。攻擊淑子的是個十幾歲至三十幾歲的年輕男子,眼神銳利,有隻鷹勾鼻,下巴尖銳,「乍看之下有點像洋人」。
從松浦康江的周遭人士,找出了一個相似的男人──植田隼人,三十一歲的無業遊民。
據說植田曾追求松浦康江被拒,之後便一直死纏爛打,令她相當害怕。
警方通知淑子出面指認,而她表示雖然頗為相像,卻無把握,又覺得凶手的個子好像更高一些。
警方調查植田,而植田否認犯案,並表示自己的確曾被松浦康江拒絕,但並未因此懷恨在心,也未曾出沒於她家四周,亦沒殺害她;至於那個名叫土居淑子的女人,他更是連看都沒看過。
康江之事另當別論,但植田說他不認識淑子,似乎並非謊言。淑子指證時,曾說植田是「之前從未見過的生面孔」,而松浦康江與土居淑子之間也沒有任何關連或交集,植田與淑子兩人過去並無可能相識的背景。
然而,警方卻認為植田之所以攻擊素未謀面的淑子,是因為殺害康江後「食髓知味」,開始不特定殺人之故。
這個想法,在附近的居民指證曾看見植田於六月五日從松浦家走出後,獲得了證實。事實擺在眼前,植田便改口翻供,說自己當天確實曾去找康江,但沒殺害她;自己到場時,她已經死亡了。
不過,植田終究因殺人及殺人未遂嫌疑被捕;因為在查證之下,發現他也沒有六月十二日當天的不在場證明──以上便是去年傳遍街頭巷尾的『分屍案』概要。
「我懂了,讓我猜猜看。」我放下舊報紙,再度喝起啤酒來。「你是想重新推理這件案子?雖然警方把植田當成凶手結了案,但你認為真凶另有其人,想要猜上一猜,對吧?」
「咦?」正打算開第二罐啤酒的千曉停下了手,楞了一愣。「不,我並沒這麼想啊!」
「少騙人啦!」我記得千曉酷愛推理,這點從他那佔據了三分之一書架的推理小說藏書便可得知。「你是打算提出異於警方的結論,親手揭發真相,順便以此為題材寫本推理小說吧?乖乖從實招來!」
「推理小說啊?」他咕嚕咕嚕地將第二罐啤酒一口氣喝去一半,表情只有喜悅兩字可形容,教我忍不住懷疑:普天之下,這男人所愛的該不會只有啤酒吧?「原來如此,聽起來挺有意思的;不過我從沒想過就是了。」
「從沒想過?」對千曉來說,光是沒嫌麻煩、反而感興趣,就極為難能可貴了。「那你幹嘛重看這案子的報導?不是因為覺得真凶另有其人嗎?」
「不是啦!真凶是否另有其人,我哪知道?既然警方這麼判斷,那凶手應該就是這個叫植田的男人吧!我不知道你怎麼想,不過我對這個結論沒什麼意見。」
「搞什麼啊,你這小子個性真淡薄耶!既然要重新探討這起案子,至少得有其他的凶手人選吧!」
「瞧你滿嘴其他凶手、其他凶手的,那你有其他的凶手人選嗎?」
「有啊!」乘著興頭,我拿臨時想到的人選來說嘴。「我覺得松浦康江的前夫很可疑。」
雖說是臨時想到的,但這個方向還挺正確的吧?據週刊雜誌特輯所言,擔任二專副教授的松浦康江是個相當強悍的女人,當初還是她主動「休」了丈夫的。據說她曾在友人面前如此大放厥詞:「當初看他是一流大學畢業,才和他結婚的;沒想到腦筋比我還差,我受夠他啦!」男方的自尊心當然會受傷。
況且她的前夫──村上恭一也是個輪廓深刻的高個子。唔……越想我越是興奮,說不定這正是不為人知的真相呢!
「前夫?這麼說……」然而,千曉卻無視滿心雀躍的我,仍處於狀況外:「松浦康江離過婚啊?」
「啊?慢著,你連這個也不知道?」
「我對那個又沒興趣。」
「那你到底對什麼有興趣啊?你是覺得哪裡有意思,才重看這件案子的報導?」
「這個嘛……比如說,」他拿起一本週刊雜誌:「土居淑子和坪井純也的相識過程啊!說來有趣,他們兩個之所以相識,竟然是因為女方開車撞到了騎著腳踏車的男方耶!真羨慕啊!要是能因這種小車禍而結緣、相戀的話,我也洗心革面,來開開車或騎騎腳踏車吧!」大概是發現我一臉怫然,千曉又嘻皮笑臉地說道:「開玩笑的啦!其實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松浦康江的屍體。」
「屍體?」
「是啊!我在想,凶手分屍的理由是什麼?」
「理由?」這問題我壓根兒沒想過,因此有些結巴起來。「應該沒什麼理由吧!」
「是嗎?」
「是啊!勉強說來,可能是因為對康江恨之入骨吧!」
「可是凶手對素未謀面的淑子也打算做同樣的事啊!」
「大概是因為他殺過一次人,腦筋有點不正常了吧?」我忘了自己才剛主張是康江的前夫犯案,又以植田犯案為前提討論起來。「或是切割女人的身體讓他產生快感。」
「也就是變態的一種?或許事實就是如此吧!不過,這樣未免稍嫌無趣。」
「不管有沒有趣,假如事實就是這樣,也無可奈何吧?」
「但是寫不成小說啊!你不是要我寫推理小說嗎?」
「我可沒要你寫,」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我卻一板一眼地訂正:「我只是問你是不是打算寫而已。」
「我啊,覺得最奇怪的就是手銬。」
「手銬?什麼意思?」
「為什麼凶手要銬住康江及淑子?」
「當然是為了限制她們的行動啊!」
「可是你想想松浦康江的情況,她是在戶外被殺後才搬到家中的吧?換句話說,她早死了,死人不會動,對不對?但凶手卻特地銬住死人的手腳來限制她的行動,你不覺得有點荒謬嗎?」
「這個嘛……」原來如此,經他這麼一提,這的確是個疑點。正當我埋頭苦思時,突然靈光一閃:「慢著,說不定康江並不是在戶外被殺的。警方這麼判斷,是因為她的身上有拖曳過的痕跡,且衣服上沾滿泥巴;從這兩點來看,康江或許是在戶外被攻擊的,但無法確定她是否死於起先的攻擊之下,對吧?她雖然被攻擊,但那時還沒死──這樣一想,就沒有任何矛盾啦!」
「也就是說,康江被搬到家中時,其實人還活著?」
「對。仔細一想,搬一具屍體可是很辛苦的。我不知道那個叫植田的男人體格如何、有多少力氣,但就算他是個身強體壯的男人,與其殺害後再搬到家中,還是帶回家裡再殺比較省事吧?」
「你說的沒錯,但手銬還是很奇怪啊!就算康江被帶回家中時還活著,她也應該因頭部被毆而意識朦朧吧?不管凶手是在戶外攻擊時、或是帶回家裡後才下手敲昏她的,總之她已經無力抵抗了,要下手勒死她,不會有多大妨礙;那又為何要銬上手銬?」
「她不見得全無抵抗之力啊!說不定又醒過來了咧!」
「再敲昏她一次不就得了?至少比起讓她抱住柱子、再銬住手腳要來得省事多了吧!」
「嗯……這麼說也對。」
「再說,凶手接下來還得分屍;雖然我沒分過屍,但我不認為把屍體銬在柱子上,分屍起來會比較方便。當然也不是不能分啦,實際上凶手就是這樣分屍的。不過,他明明可以解開手銬再分屍,為何沒那麼做?我覺得,凶手似乎有某種執著;他將被害人銬在柱子上加以分屍,是有理由的──」
「你認為不單是心理變態發狂之下的產物?」
「我越想越這麼認為。」千曉突然靦腆地說道:「我剛剛說即使凶手是植田也無妨,並不是說謊;只不過,凶手若是他,這份執著就只能解釋為發狂之下的產物。和你討論過後,這點顯得更清楚了。」
「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你別誤會,那是在要求手銬及分屍都要有合理意義的情況下,凶手才會是其他人。說不定植田確實是個變態,而凶手也的確是他,案件到此解決。對我來說,這樣也無所謂。」
「不然虛構也好,你試著賦予這件案子合理意義吧!要不然,連部短篇推理小說都寫不成喔!」
「我又沒打算寫。」
「我們姑且以『真凶另有其人』為前提來開始討論吧!」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解體諸因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日本推理小說 |
$ 264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解體諸因
【媒體推薦】 獨步「迷詭」雜誌嚴選60本好看、必看的佳作之一。 獲得「推理之神」島田莊司賞識,西澤保彥一鳴驚人的出道作! 超人氣學生偵探「匠千曉」系列的原點,推理迷必看! 【內容簡介】 分裝於六個箱子中的男人、七顆頭顱依序調換的連續殺人、於短短16秒內被分屍電梯中的上班女郎、切成34塊的主婦;在這部短篇集中,新主角‧匠千曉將挑戰九個手法極盡巧妙的分屍案。 帶給新本格派莫大衝擊的西澤式推理小說,眾所期盼的出道作登場! 【作者簡介】 西澤保彥(Yasuhiko Nishizawa
章節試閱
第一因 解體迅速拜訪匠千曉,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三月二十日,春分;那一天我閒得發慌。妻子利用連假期間,帶著五歲及兩歲的女兒們回娘家過夜;本來我也該同行的,卻藉口時值入學考前後、諸事繁忙,一個人逃之夭夭。這牽涉到某個教人心煩的緣由。最近,岳父及岳母間的氣氛變得極為險惡;這是因為岳母不知哪根筋不對勁,都一把年紀了,竟然去考了張汽車駕照回來,之後又立刻開車撞傷了人。對方的傷勢並無大礙,但接下來可就難捱了;岳母每天都必須到醫院報到。除了探病,還得代替對方的家屬照料對方。我不要求賠償金和醫藥費(結果還是付了...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西澤保彥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8-02-14 ISBN/ISSN:97895710376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