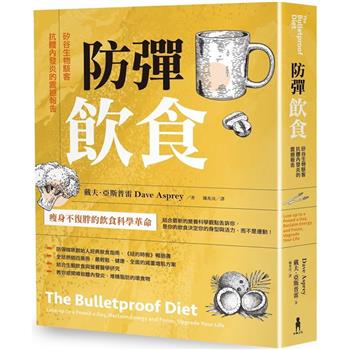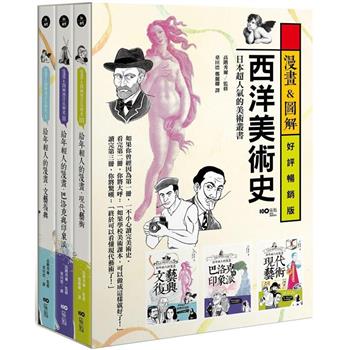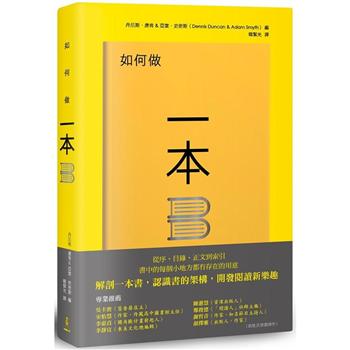破戒門
一
寬永十九年春 ,一支聲勢浩大的異樣行伍,在東海道上揚起了漫天塵砂,讓路旁行人瞪大了眼睛。
這支行伍至少百人以上,大多是手持長槍的步卒,騎馬的武士則有七人。在七名騎士之間,前後間隔幾乎相同,當路旁行人瞥見其間被拖行的人,心中不由得詫異不已。
隨行在兩側的步卒們,也並未特別加以掩飾。每匹馬後面都曳著三人,共有二十一名墨衣僧人,猶如念珠般被串著,身形搖晃地朝前而行。而且,綁在僧人們身上的繩索,並非是普通綁法,除了雙手被反綁身後之外,還套在每個僧人的脖子上,別說是逃走,甚至連步伐慢了或摔跤都不受允許\。
「還不給我走快點!」
「你這傢伙,要是步伐再慢,你身後那老禿驢,可是會被絞首的。」
那些僧人的腰部與脊背,不斷被長槍戳著,身上僧服早已破爛不堪,赤腳之上血跡斑斑。
不過,這二十一名僧人,雖然沾滿了塵土、汗水與淚\滴,而且被折磨得臉色慘白,幾乎不成人形,不過仍舊昂然前行。仔細一瞧,在那行伍當中,有著白鬚冉冉的老僧,也有數名十二、三歲上下的小沙彌。
「這……真是殘無人道——」
「簡直像是趕畜生似的……」
「而且還是僧人……」
路旁行人們抱著胳膊,望著那支令人戰慄的行伍,不知何人,提起那些人是遠從百里之外的高野山押解而來,這更令人毛骨悚然。其中,最教行人們害怕的,是那三隻緩緩走在行伍前頭,瞪著惡狠狠的目光,身型如小牛般的白色秋田犬。
「他們究竟干犯何罪?」
「據聞那群人原本並非僧人,而是逃入高野山的落難武士。」
「聽說是對會津藩主謀反的武士。」
「什麼?!謀反?──那麼──」
提及此事,眾人便屏住呼吸,噤聲不再討論,目送著那一行人離開。
這支行伍來到了藤澤的客棧,離江戶尚有十二餘里 的路程。
在接近藤澤之時,在隊伍前方策馬而行,模樣酷似猴猻的矮小武士,將綁著三名僧人的繩索交給身後的步卒,調轉馬頭往後而去,與其餘騎馬的六名武士,不知逐一交頭接耳地商量何事之後,又策馬回到行伍前頭。
進入藤澤以後,這列行伍並未取道江戶的遊行坂,而是折向南方的岔路疾行,三隻身型巨大秋田犬,也緊隨行伍之後。
「具足丈之進,這是要往何處去?」
一名脖子上套著繩子的僧人狐疑問道。
「這不正是往江戶的方向嗎?」
猴臉模樣的武士,轉身露齒冷笑道︰
「不過,在前往江戶之前,先往鐮倉的尼姑庵。」
「什麼?!」
出聲發問的僧人,約莫五十多歲,長相剛毅樸實,聽到具足丈之進答話之後,露出詫異不已的神情。
「你所說的尼姑庵?指的可是東慶寺?」
「主公曾經交代過,即使得刨出草根來,也要將崛氏一族全部搜出,連幼兒也不可放過。難道你認為,我方不知崛家有三十餘名女子,全都逃到東慶寺當尼姑去了?」
「這我心裡有數,不過──」
僧人沙啞的嗓音,隱約透著不安。
「自弘安 時代以來的三百五十年裡,東慶寺嚴禁止男子進入。」
具足丈之進再度轉身露齒冷笑︰
「你的女兒千繪,不也當了尼姑?主
公對這個長得如花似玉的十九歲ㄚ頭,可說是傾心不已,如今她卻削去了那頭美麗的烏髮,伴在青燈古佛之下,你對主公還真是不忠不義啊!──」
「住嘴!」
僧人怒喝道。
「丈之進,前往東慶寺,究竟意欲何為?」
「此地距鐮倉只有二里半,不過就在附近而已,特地讓你們在生前,見上最後一面,一切都是出於武士道義,你們應該要心懷感激才是。」
僧人沈默片刻,嘴唇微動,以低沉的聲音說道︰「感激──不盡。」隨即伸長了被繩子套住的脖子,回頭朝身後眾僧人喊道︰「喂!似乎要讓咱們與東慶寺的女人們,去見最後一面,眾人還不快快道謝!」
到目前為止,在這趟生不如死的地獄旅程當中,這二十名左右的僧人們,從未曾咽嗚或呻吟,此時卻不禁發出了聲音。宛如早已化為寒冰般的冰冷身軀,瞬間接觸到溫熱的泉水似的感動,僧人們不禁淚\眼盈眶。
「不勝感激。」
「如此一來,心裡對主公的怨恨,也減輕了不少。」
七名騎馬武士,嘴角盡是露出冷笑,在馬上睥睨著僧人們的涕零模樣。
這列行伍從藤澤出發,走了一里,途經江之島,渡過泛著白濤的七里海,再往前行一里半,即抵達了鐮倉境內。
往昔曾為大名府邸所在地的鐮倉,自北条氏滅亡三百年餘以來,如今不過是充斥著無數廟宇佛塔的孤城。迎接此一奇特行伍的,僅有自空飄落,亂人心緒的花瓣。此時已是晚春時節,景象更顯得淒涼落寞。
沿著山之內的街道一路往北,在右方的叢林,可瞧見圓覺寺的屋簷,與騎相對的,乃是位在左方丘陵山腰的松崗東慶寺。
只見三名武士由馬上一躍而下,走上了青苔滿佈的高聳石階,緩緩朝著山門的方向而去。
二
東慶寺雖是嚴禁男子入內的尼姑庵,但也未至無半隻雄貓存在的地步。守門者便是個男子。除此之外,尚有少數男僕。不過,毫無例外的是,這些人全是老人,而且腰間都繫著數枚鈴鐺。
年老的守門者,瞥見三名沿著石階而上的武士之後,彷彿見到天外而來的不速之客似的,連忙掩上山門。
「唉呀!」
三名武士見狀,立刻加緊腳程,沿著石階飛奔而上,然而,還是遲了一步,只聞「砰!」的一聲,三人眼睜睜地看著山門關了起來。
不過,仍可聽見山門內守門者的鈴鐺聲,於是,三名武士報上了自己的名號。
「我等乃會津藩加藤式部少輔的家臣,在下名叫鷲之巢廉助。」
一名身形彪悍,肌肉虯結,滿面鬍鬚的武士喊道。
「在下乃司馬一眼房。」
另一名左眼已瞎,皮膚青腫的光頭武士說道。
「大道寺鐵齋。」
最後的說話者,是名鶴髮長鬚的枯\瘦老人,喉間發出的嗓音,卻有如女子般輕柔。
「這事想必你也知情,就在去年春天,崛氏一族是如何對主公式部少輔大逆不道。我等已得幕府允許\,將他們盡數擒拿,如今即將押解至江戶,但崛主水等人,說是家族的女眷三十餘名,全都寄居在貴庵當中,內心亟盼見上一見,此時他們正在山下等著。請將此事稟報你家主人,要崛氏一族的女眷們,前來與他們見上最後一面。」
「請等候片刻。」
山門之內的鈴鐺聲,漸漸遠去。
三人抬起了頭,重新打量著眼前的山門,這座鑲有鐵塊的巨大山門,相較於尼姑庵的風格,顯得格格不入。
「這扇山門,原本是駿河大納言府邸的大門。」
「據說連客堂、佛堂和掌門的房間,都是從駿河運過來的。」
「原來這是年俸五十萬石的權貴家的大門,難怪如此氣派。」
三人若有所思地彼此點頭。
這三人所提及的駿河大納言,乃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的弟弟--年俸五十萬石的德川忠長,卻被懷疑對幕府有反心,在九年前被迫切腹自殺。這座偌大的寺院,自創建以來,已歷經三百五十年之久,在年久失修情況之下,寺內的建築不斷地老舊腐朽,因此,在忠長切腹自殺的第二年,也就是寬永十一年,以從駿河城運來的建材為主,在此寺進行大幅翻修。
寺內傳出的鈴鐺聲越來越近,但由腳步聲聽來,來者不僅一人。
「會津來的武士!」
寺內發出的聲音,並非先前守門者的聲音,發話者似乎是名老尼。
「方才之事,已稟報敝寺掌門,雖說是難得的機會,但掌門決定不讓他們相見。」
「啊?!」
三名武士神情詫異,面面相覷。鶴髮蒼蒼的大道寺鐵齋,連忙對其餘二人使了眼色,要他們先別開口,隨即以陰柔的嗓言問道︰
「這是為何?」
「不論任何女子,一旦入了本寺,便得泯除世間恩怨情仇,雖說他們想向自己的母親、妻女作今生的死別,其情固然可憫,不過,若是讓雙方相見,那些已誠心向佛的女人們,心湖必將掀起悲痛波濤,人生在世。必將一死,本寺會替那些施主誦經迴向,煩請代為轉告。」
「真令人想不到,信佛之人,竟說出此等毫無慈悲的話語!我們可是基於武士的情義,特意繞道前來鐮倉。」
「武士的情義?!」
那名老尼的聲音,霎時變得嚴厲起來:
「方才,我聽守門人稟報,囚犯們彷彿被當成了牲口,脖子上還拴了繩套,身為武士,做出如此可恥的事,還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竟然有臉提什麼武士的情義。」
三個武士的臉色,顯得有些僵硬。
「即使嘴上說是讓雙方相見,也絕不可能是出自慈悲心,這其中定然有詐,本寺不會中你們的詭計--快快請回吧。」
「不,我等不可能就此回去!」
巨大魁梧的鷲之巢廉助說道。
「我方曾在崛主水等人面前親口允諾,要讓他們與女眷相會,我方可是名震天下的會津七槍,怎可作出食言之事,這可關係到我方的聲譽。」
「那是你們擅自決定的事,敝寺絕不會在明知有詐的情況下,還將那些讓人同情的女眷送入虎口。聽清楚了,松之崗東慶寺,可是個女人的城池。」
「女人的城池?」
皮膚臃腫泛青,頂著光頭的司馬一眼房,在一旁露齒冷笑,同時對站在石階下仰望的具足丈之進揮手。丈之進點了點頭,飛身移至寺廟側面,三頭巨型秋田犬,腳下揚起沙塵,緊跟在他身後。
「聽見妳說這是女人的城池,更讓我想攻進去看看了,老尼!妳就好好護住這座寺廟給我看看吧!」
「你意欲為何?!」
老尼不由得大驚失色。
「本寺乃在北条時宗 御台時期,由覺山尼師太,為救濟落難女子,在當朝的允許\下而創建的,至今從未被男子入侵過。儘管已經改朝換代,歷代幕府從未違反這條寺規,難道你們想觸犯這條禁規?」
此時,寺廟周圍響起陣陣狂吠,與其說那是犬吠,更像是野獸的嘶吼。
尼姑們從各個寺房裡奔了出來,在裡門與側門附近的人,抬頭望了一眼,紛紛驚叫連連。
只見裡門與側門的門簷上,各伏著一頭如小牛般壯碩的巨犬,怒睜血紅雙眼,盯視著下方的動態,不斷發出魔物似的咆哮。
在此同時,鷲之巢廉助也發出了駭人狂嘯:
「破!」
他的左腳在山門前跨出一步,呈現屈膝半蹲的體態,右臂迅如疾風地擊出,同時大喝一聲。
「赫啊!」
鷲之巢廉助的手掌並未握拳,拇指屈起,其餘四指伸直,只見那扇橡木鑲鐵的厚重門扉,宛如薄紙一般被穿了過去。
他隨即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又在左邊約三尺之處刺了出去,高大魁梧的他,身形卻如平蜘蛛般輕盈敏捷。在下方穿出第三個洞以後,舉腳轟然踹了過去,只聞「碰!」的一聲,山門上被踹出個可容人通過的三角形大洞。
這一切都眨眼之間發生,與其說是怪力造成的,倒不如說那肉掌化成的刀,威力強得驚人。--他的確大喝了聲「破!」,又有誰能想像得到,他居然輕易地破毀壞了那扇肅穆莊嚴的禁制之門呢?
三名武士逐一從門上的三角形大洞穿了過去,看見幾近昏厥的老尼之後,鷲之巢廉助冷笑道,「門被我破了,看你能奈我何。」
「眾人快逃!有不肖之徒侵入寺內了,眾人快逃啊……」老尼如母雞般伸長脖子喊道。
霎時,有無數條的白影,從佛殿、住持房以及樹林裡的寺房裡竄出,寺內裊繞的青白色香煙被衝得飄散。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柳生忍法帖(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4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柳生忍法帖(上)
【媒體推薦】 ──孤刃戰七槍,一劍斬修羅── 狂銷突破數百萬冊,獨領風騷半世紀。 日本一代奇想武俠宗師 山田風太郎 《忍法帖》系列巔峰之作! 馳星 周、菊地秀行、京極夏彥等暢銷作家全力推薦。 日本亞馬遜五顆星推薦! 【書籍簡介】 惡名昭彰的「會津七槍」假藩主之命,在東慶寺大開殺戒,屠殺數十名女尼,庇護聖地頓時化為屍山血海──佛門濺血,天地難容!暴虐無道的藩主加藤明成為逞一己私慾,放任七槍恣意殺人,更將不願屈服的堀氏一族斬盡殺絕……震怒的德川千姬,命柳生十兵衛領
章節試閱
破戒門一寬永十九年春 ,一支聲勢浩大的異樣行伍,在東海道上揚起了漫天塵砂,讓路旁行人瞪大了眼睛。這支行伍至少百人以上,大多是手持長槍的步卒,騎馬的武士則有七人。在七名騎士之間,前後間隔幾乎相同,當路旁行人瞥見其間被拖行的人,心中不由得詫異不已。隨行在兩側的步卒們,也並未特別加以掩飾。每匹馬後面都曳著三人,共有二十一名墨衣僧人,猶如念珠般被串著,身形搖晃地朝前而行。而且,綁在僧人們身上的繩索,並非是普通綁法,除了雙手被反綁身後之外,還套在每個僧人的脖子上,別說是逃走,甚至連步伐慢了或摔跤都不受允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山田風太郎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8-02-12 ISBN/ISSN:978957103783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