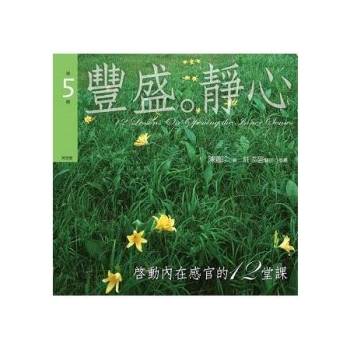序幕
新賈辛圖──維安政府聯盟首都──維特斯海軍基地的大食堂酒吧。
日期:事變日後十四天,霧月最後一週
我不是個喜歡交際的人。不過你們可能早就猜到了。還有一點,不要,我可不要你請我喝啤酒。
要是你認為,我內心還存在著友善的一面,就等有緣人給我機會──我只能告訴你,休想!不過話說回來,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一樣,你就是笨。任憑我說破嘴,你還是忍不住要打這個主意。
「 巴德,別這樣。 別一輩子都當個離群索居的傢伙。給自己放個一天的假。」她的名字叫莎曼.布萊恩; 喜歡嘴巴畫大餅,一身皮衣, 紋身,與我年齡相仿──意思就是按照她的年紀,應該不至於如此愚蠢。 她將一杯滿溢的烈酒杯往酒吧台上用力一叩,然後往我這邊推了過來。「穆勒要教我們下海軍棋。」
「是喔,真讓人興奮,我褲子都尿濕了。」
莎曼遲疑了一下,隨即一把將酒杯攫走。如果杯子裡裝的是狄奇私釀的威士忌,她拿走也好,正好幫了我個大忙。「去你的,」 她應了一聲,氣沖沖地走開。
我實在需要培養馬可斯.菲利那一套功夫。他可以獨自坐在酒吧裡,一整晚都不會有哪個屁蛋敢湊過來煩他。不過,話又說回來,畢竟他是菲利。這不僅僅是榮獲安伯利之星勳章的戰爭英雄才有的氣勢,還有別的因素。就好像這傢伙周圍漂了一圈警告浮標,雖然除了grubs以外,沒有人見過他真的為著什麼細故而發脾氣。
即使傻瓜仍有一絲求生的本能,我是這麼認為。
幹!我真希望有誰來關掉吧台後面那台該死的電視機。只聽到那個混蛋叨叨絮絮談論著打造更美好的什麼鬼東西的未來和機會。他媽的將來又如何?大部分的難民失去家園,連個自來水都是奢求,但是哇哈,我們居然有個不間斷播送的電視頻道。實際上,那只能說是上映靜態照片的收音機。每個人都有一台收音機。公共區域有幾台電視,就讓這裡的平民覺得非常棒了。彷彿是得著一種恩賜,生活有了改善。嗯,好哇,他媽的真是值得歡呼。
愚蠢是一種幸福。我真羡慕這些人。
我是說真的。無知真的是幸福。身處金字塔最頂部那百分之一的難處──沒錯,我就是那百分之一,這麼說會不會讓你坐立難安?──就是你很清楚這世界有多糟糕。而且不可能變得更好。只會不斷改變。但是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任何狗屎都看起來像是有所改善,只要是和過去不同就好。
對人們而言有新的媒體頻道就是好事。你當真這麼認為?哼,普萊斯考主席需要找個管道,來將他那些政令宣傳塞到所有呆瓜的笨腦袋裡。更何況讓那些囉嗦的新聞記者有事情忙,他們就不會做出任何真實的報導,這也是想當然耳的道理。你認為我們應該慶祝,因為grubs一去不復返,而我們可以重新開始了嗎?不,我們只不過是將獸族換成兩條腿的新型害蟲 ──遊民幫派。我們已經將這個世界轟炸成上個世紀的狀態,沉沒我們自己這該死的城市,所以現在我們沒有製造業、沒有基礎設施,不能對錫拉星的其餘地區進行重建工作。
但普萊斯考表示,未來一切光明,因為多虧了Gorasnaya,讓我們擁有用之不竭的燃料。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獨聯那四千名忘恩負義的混蛋嚴格說來直到幾個月前仍與我們交戰中。
你看,我可以永遠說下去。但是,說到這裡,即便像你這樣的笨蛋也應該聽懂了。是吧?
一隻大手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然後像老虎鉗一樣緊緊抓住。原來是柯爾。大多數人會把電視裡的那一套話當成是填鴨的垃圾,但柯爾不是。我就是不懂為什麼這樣聰明的人還可以隨時都那麼快樂。
「寶貝,要不要柯爾給你來一課魅力成長課程?」他俯下身體,並大聲地在我耳邊低聲說。「像你這樣對待女士,你永遠都不會有進展。即便是小綿羊也不會給你甜頭。」
「那是莎曼。」那個臭娘兒永遠想要找男人比腕力、比酒力、比罵髒話的功力。「不是女士。」
「少裝蒜了。你知道布萊恩很想讓你幫她生下一屋子臭脾氣、自以為是的金髮兒孫。」
這番話出自柯爾口中,我完全無所謂。由於某種原因,他從來不會惹火我。「是嗎?那她還不如將賭注壓在多姆身上。」
他幽幽歎了一口氣,當真的模樣,不像柯爾在進行訓練課程時會有的舉動。「我想她有得等了。」
多姆目前一團糟。我不指望有誰可以輕易擺脫被迫要對妻子腦袋轟上一槍的陰影,但他早在十年前當她第一次失蹤時便開始哀悼,並視她為聖。如果當時他就沒能想開,現在又有什麼能改變他?你看,他並不笨。我堅持待在D小隊,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靈長類,而且擁有三位數的智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神智清醒。
於是我與柯爾坐在這酒吧裡,沉默地喝著酒。莎曼在享受她海軍棋,而且發出最大音量。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觀看,以免他們以為我在乎,但如果我稍微轉身過去,看到的一定是棋盤上一個個滿溢的酒杯──白色方格裡擺著私釀威士忌,黑色方格裡擺著蘭姆酒──而不是一顆顆棋子。哦,我明白了。原來是這樣──穆勒每吃下莎曼的一個棋子,他就可以喝光一個酒杯。可是他們怎麼知道要怎麼下這一局?
看,這就是我所謂的蠢蛋。這根本不是在下棋。不過是擺著一個棋盤格好看。但是等他們喝光所有的酒杯時,他們已經醉得無從分辨了。
酒吧的門打開。有人發出歡呼聲。開始在喝釆起哄。「有條狗!」
另一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傢伙插嘴:「別那樣說馬塔基中士。正確的稱呼是『母狗』。」
嘲笑也該有個限度。伯尼.馬塔基只是給他們一個表情,當他們是沒份量的可愛小男孩。這一招總是比莎曼摔酒杯的招式有效。別以為我已經對女性到前線服役一事改變看法──這是個再糟糕也不過的主意,糟糕,而且糟糕透頂──但伯尼就是有辦法讓這幾個傢伙閉嘴。也許是因為她年紀大,而且吃貓。也許是因為她的服役記錄。更有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她剪掉某個傢伙的兩顆睪丸。但她手上真的牽著一條狗。這隻野性十足的大狗一身銀灰色剛毛,至少有三十公斤的重量。
「長得真漂亮呢!」她搓揉那隻狗的耳朵,一雙棕色的大眼睛用小狗無辜的神情仰望著她,就像該死的霍夫曼。整個酒吧裡的客人紛紛放下手邊的事,又是哦,又是啊的,好像從未見過狗似的。「這是麥金。專門獵捕遊民。我借來用一陣子了。」
「會耍寶嗎?」柯爾問道。
伯尼把那隻笨狗牽到我面前。小傢伙的腦袋到她臀部的高度。看起來像是一匹心情不好的狼。「麥金,這裡有位金髮尤物。別磨蹭人家大腿,懂嗎?喂,我這句話是對你說的,巴德。」
我任何的反應都只會鼓勵她。「老奶奶,妳這隻純種狗屁名犬知道妳專吃寵物嗎?」
「只吃貓。他無所謂的。對不對,小伙子?」
「漂亮的小狗狗,」柯爾說。「你幫我們省下不少時間。」
「來吧。讓我們去散散步。」伯尼大可以拿一副馬鞍放在那該死的狗背上騎。我希望可以在直升機周圍這麼做。「如果我們不能趕走那些混蛋遊民,讓我們看看狗能做些什麼。是時候了,至少讓我們找出這些龜蛋到底是躲在哪裡。」
「我們能不能說他們只是幫派或什麼的,女金剛?」柯爾問道。「因為大部分的遊民都像狄奇一樣。沒有惡意,甚至可以說是友善。」
海軍棋對我來說不痛不癢。但是獵殺那些混蛋……這才是能讓男子漢感到自豪的消遣。沒錯,柯爾說對了。這是全新的一種遊民。不是那種遊手好閒的寄生蟲──而是有組織的犯罪、海盜、強姦、謀殺。別跟我假惺惺地說什麼我們現在需要同心協力,因為我們正努力重建人類文明的廢話。現在就是消滅那些垃圾最好的時刻。
「好吧,就叫他們是害蟲,」我說。「而且我投票贊同讓麥金繼續保留牠的咀嚼玩具。」
在宵禁區以外和那裡沒有關係的人都可以是獵物。不是嗎?
不要那樣看著我。你不曉得過去這十五年是什麼德性。我什麼也不後悔,除了後悔有些事沒有及早做。你以為你是誰──我那要命的老娘?
第一章 維安政府聯盟維特斯海軍基地
非平民事故日誌摘要
融雪月一日至霧月三十五日,包括事變發生後第十四天。
攻擊財產:三十五件
攻擊平民:二十件
平民傷亡人數: 六死十五傷。
聯盟人員傷亡人數: 十八人受傷,無人死亡。
叛亂分子傷亡人數: 三十死。(受傷人數資料無法取得。無傷員遭到拘留。)
維特斯海軍基地,維安政府聯盟海軍,新賈辛圖: 風暴月第一週,事變發生後第十五天。
「歡迎到新賈辛圖,」普萊斯考主席說。「歡迎投入維安政府聯盟的保護。希望這新的一年 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霍夫曼不得不交棒給普萊斯考;他總是有辦法將滿口的謊言說成神聖的真理。這兩個人站在碼頭上,而Gorasnaya的派拉克號貨櫃船正在卸貨,卸下一貨櫃的人。這五百名平民來自一個獨立的共和國,據說直到上個月為止還在與聯盟交戰。不論他們喜歡與否,他們現在都是聯盟的一部分。霍夫曼猜想這應該不是出自他們的意願。
「主席,他們臉上看不出歡欣鼓舞的樣子,」霍夫曼說。政客似的佯裝笑容始終掛在普萊斯考的臉上,很可能是為他本地的觀眾而作的秀──聯盟精銳步兵特遣隊、醫療團隊、一些平民代表──而非為了給新抵達的平民看的。
「我希望是不適應加上暈船所致,而不是這些人不懂得感激,」他說。
霍夫曼眼睛始終盯著前進的隊伍,一方面是在尋找潛在的麻煩製造者,另方面也是想知道是否有任何難民語言夠熟練,看得出維安政府聯盟這個頭銜的諷刺可笑處。政府聯盟?剩下來的也只有一個政府,一個不過是城市規模的行政管理單位,而且還遠在一個離提魯斯王國有一週航行時間的偏遠島嶼上。這是全球數以億萬文明在與獸族交戰十五年後碩果僅存者。
但是在像今天這樣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完全不是暴風季節的典型天氣裡,維特斯海軍基地必然是看起來一片榮景,特別是與本土相較之下。過去從沒有任何一個 grub涉足此地,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Gorasnaya的那些混蛋應該感到心滿意足了。拿這麼一個食物充足的安全避難所來換取他們不需要的那些多餘的燃料?這算是很划算的交易。
「也許他們只是討厭我們有這種膽識。」霍夫曼試圖想像將潘度輪戰爭停火協議置若罔聞的這個無足輕重的國家的心態。應該有滿腔嚴重的怨懟。「加入我們是他們領導人的想法。我敢打賭他一定沒經過表決。」
「只希望他們別把這當成是自備飲料的派對。」
Gorasni 當然不是空手來消耗維安政府聯盟有限的資源。他們放棄他們伊姆能源的供應──運轉中的海上鑽井平臺──來換取避難。在一個被付之一炬的廢墟世界,能源與食物是確保明天還有希望的兩大資產。霍夫曼對獨立共和國聯邦沒啥好感,也相當肯定對方不怎麼喜歡他,但畢竟這是危急存亡之秋。
不能對我們的鄰居太挑剔。至少他們不是遊民,他們也沒對我們大動干戈──至少目前為止還沒動手。
聯盟精銳步兵保安特遣隊整齊部列在碼頭,引導難民到位於一個像圍城結構的舊倉庫內,轉由接待團隊接手。
霍夫曼掃視他周圍一張張臉孔,納悶是否戰爭能讓一個人忘記先前的教訓。但是維特斯 當地人從沒有見過獸族。他們記得的怪獸是那些與人類交戰八十年,目前依然隸屬獨聯的舊敵人──包括正在登陸碼頭的那些人。
「混蛋。」普魯恩鎮民代表會的一位老人咆哮了一聲。他破舊的外套上,戴滿了潘度輪戰爭的勳章,包括創盟先賢軍事獎章。不,他不能忘記。「不能原諒他們。尤其是從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表示歉疚的那些人。」
霍夫曼留意到那人胸前滿滿的戰役勳綬,小心斟酌自己的措辭。過去曾經是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如今變成是新盟友,實在很難在這二者之間作明確的切割。反正會讓他怒目攢眉的不是Gorasnaya,所以他大可以保持相當距離來看待這些獨聯的人。
該如此嗎?我很清楚他們做過的勾當。我也知道那個老傢伙的意思。但他們不是唯一的罪人。我們都做過自己無法感到自豪的事情。
「他們是擁有大量能源的獨聯,」霍夫曼終於說出口,他也意識到普萊斯考正在摒息偷聽。那傢伙雖然看上去像是全神貫注在別的事上,但他稍微傾斜著腦袋,說明了他沒放過聽力所及範圍內的一切動靜。「沒有人要你原諒。只是拿他們的伊姆能源作為戰爭賠償。」
這位老人死盯著霍夫曼,彷彿不可置信地看到一個無知的孩子,而不是袍澤同誼。
「我的戰友們就是死在Gorasni 的強制勞動營裡。」 他使勁拉著他的翻領,讓霍夫曼看釘在那老舊軍服上托倫大公軍團的三叉戟徽章。「獨聯可以將他們的能源留著擦屁股用。」
「介意我請問閣下為什麼今天會來嗎?」
「只是想看看他們手裡沒拿著槍是什麼德行。」老人說。他可能已經七十多歲,也許只比霍夫曼年長個十或十五歲,不過也很難說,因為一旦年紀大了,每長一歲似乎總老得特別快。
「每個人都想要親眼直視怪物的眼睛。對吧?」
而所有的怪物都必須要先認罪,才有可能得到寬恕。Gorasnaya 連個邊都沾不上。也許,他們反正再怎麼懺悔都不夠呢。
「對,」霍夫曼回答。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戰爭機器:鐵砧門之役的圖書 |
 |
戰爭機器:鐵砧門之役 作者:凱倫.查維斯(Karen Traviss) / 譯者:張可婷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11-09-2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4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8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25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戰爭機器:鐵砧門之役
以全球最暢銷遊戲《戰爭機器》為背景,描述人類面臨滅絕危機而依然奮戰到底,並勇敢承擔其行動後果的戰爭史詩。
鐵砧門是一座位於卡須克南部邊境城市安維加的要塞,自騎馬時代以來,由於其難攻不落的地理形勢,鐵砧門一直都是防禦卡須克南部邊境的重要據點,與這個國家南方的獨立共和國聯邦的富林共和國對峙著。
鐵砧門圍城戰可以說是維安政府聯盟在卡須克前線對抗獨立共和國聯邦最重要的一場戰役。同時也是維克多‧霍夫曼生涯中最具決定性的一役──
作者簡介:
凱倫‧查維斯(Karen Traviss)
曾擔任英國後備軍人,擔任過報社的軍事新聞特派員。
她的第一本星際大戰系列小說一出版,立即獲得許多好評,為目前最炙手可熱的科幻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序幕
新賈辛圖──維安政府聯盟首都──維特斯海軍基地的大食堂酒吧。
日期:事變日後十四天,霧月最後一週
我不是個喜歡交際的人。不過你們可能早就猜到了。還有一點,不要,我可不要你請我喝啤酒。
要是你認為,我內心還存在著友善的一面,就等有緣人給我機會──我只能告訴你,休想!不過話說回來,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一樣,你就是笨。任憑我說破嘴,你還是忍不住要打這個主意。
「 巴德,別這樣。 別一輩子都當個離群索居的傢伙。給自己放個一天的假。」她的名字叫莎曼.布萊恩; 喜歡嘴巴畫大餅,一身皮衣, 紋身,與我年齡相...
新賈辛圖──維安政府聯盟首都──維特斯海軍基地的大食堂酒吧。
日期:事變日後十四天,霧月最後一週
我不是個喜歡交際的人。不過你們可能早就猜到了。還有一點,不要,我可不要你請我喝啤酒。
要是你認為,我內心還存在著友善的一面,就等有緣人給我機會──我只能告訴你,休想!不過話說回來,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一樣,你就是笨。任憑我說破嘴,你還是忍不住要打這個主意。
「 巴德,別這樣。 別一輩子都當個離群索居的傢伙。給自己放個一天的假。」她的名字叫莎曼.布萊恩; 喜歡嘴巴畫大餅,一身皮衣, 紋身,與我年齡相...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凱倫‧查維斯 譯者: 張可婷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1-09-22 ISBN/ISSN:978957104585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戰爭機器:鐵砧門之役 相關搜尋
奇幻生物孤兒院:榮登亞馬遜網站奇幻小說暢銷榜No. 1!入圍全球最大書評網站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最佳奇幻小說!我不是怪物:英雄真諦
侑美與夢魘繪師(邪惡奇幻天才大神超凡驚豔震撼全球祕密計畫,限量典藏豪華全彩精裝版,隨書附贈燙金藏書票「夢中的你」)
破空.卷二(暢銷華文創作大神級作家,時空跳躍玄幻冒險力作)
創仙誓:玄明聖使傳 第二話 荒城聖域
善惡魔法學院(1):天選之子的詛咒【暢銷新版】
降魔人幽池2:鸞缺篇(♛古典奇幻浪漫小說才女李莎,最新代表作,28萬字的視覺打造,四篇靈與魔交織情仇的故事)
勤儉魔法師的中古英格蘭生存指南(專屬於你的跨次元體驗平裝版,邪惡奇幻天才大神超凡驚豔震撼全球祕密計畫)
地獄反轉(上):亞馬遜當月編輯選書、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NO.1奇幻小說!
地獄反轉(下):亞馬遜當月編輯選書、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NO.1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