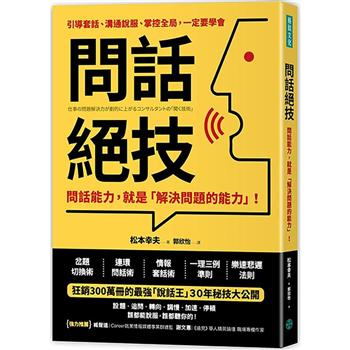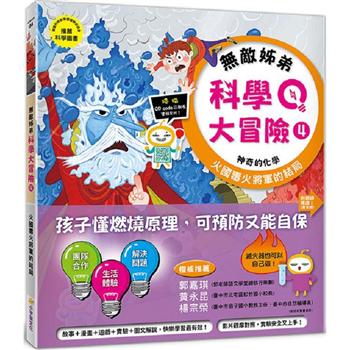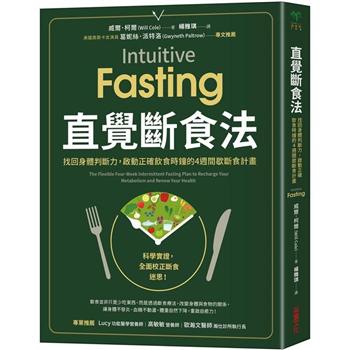「為了拯救摯愛的人,你願意毀滅自己嗎?」
氛圍獨特的野島世界觀、發人深省的絕妙對白,日本萬千讀者感動推薦!
融合「未成年」的黑暗、「101次求婚」的純愛、「一個屋簷下」的溫暖,日劇大師野島伸司又一話題作!
基於上一代的情誼,清人、哲也、直紀和望四名男孩,從小比鄰而居,打從一出生就注定是好朋友。
初春出生的清人,腦袋聰穎、個性溫和,眾人吵架時是扮演和事佬。
仲夏出生的哲也,個性衝動、率直,但極有正義感。
秋天出生的直紀,從小最喜愛的人物是「嚕嚕米系列」的「司那夫金」,個性也像雲朵般飄浮不定,八面玲瓏的個性讓他最有女人緣。
趕在三月最後一天出生的望勉強擠進同一學年,由於早產的緣故體弱多病,加上比女孩可愛的容貌,使他自小便是四家人捧在掌心中的寶貝。
可是,望的身體是男生,心是女生。
面對殘酷的現實,溫柔又美麗的友情、親情與愛情,能否給予救贖?
日本萬千讀者推薦,知名劇作家野島伸司又一感動人心的話題作。
作者簡介
野島伸司
一九六三年生於新潟縣。一九八八年以「有時像個沒媽的孩子」獲得第二屆富士電視台青春劇本大獎,由此成為劇作家。著有「101次求婚」、「一個屋簷下」、「高校教師」、「人間.失格」、「未成年」、「聖者的行進」、「世紀末之詩」、「冰上悍將」、「沒有玫瑰的花店」、「理想的兒子」等多部劇作,以及小說《天鵝湖》、《兔子精靈》、《蘇格蘭警場愛情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