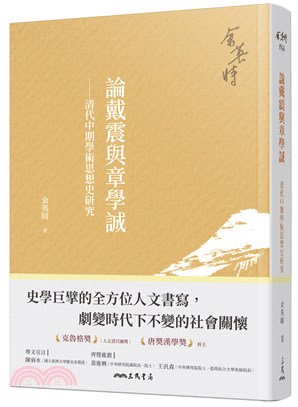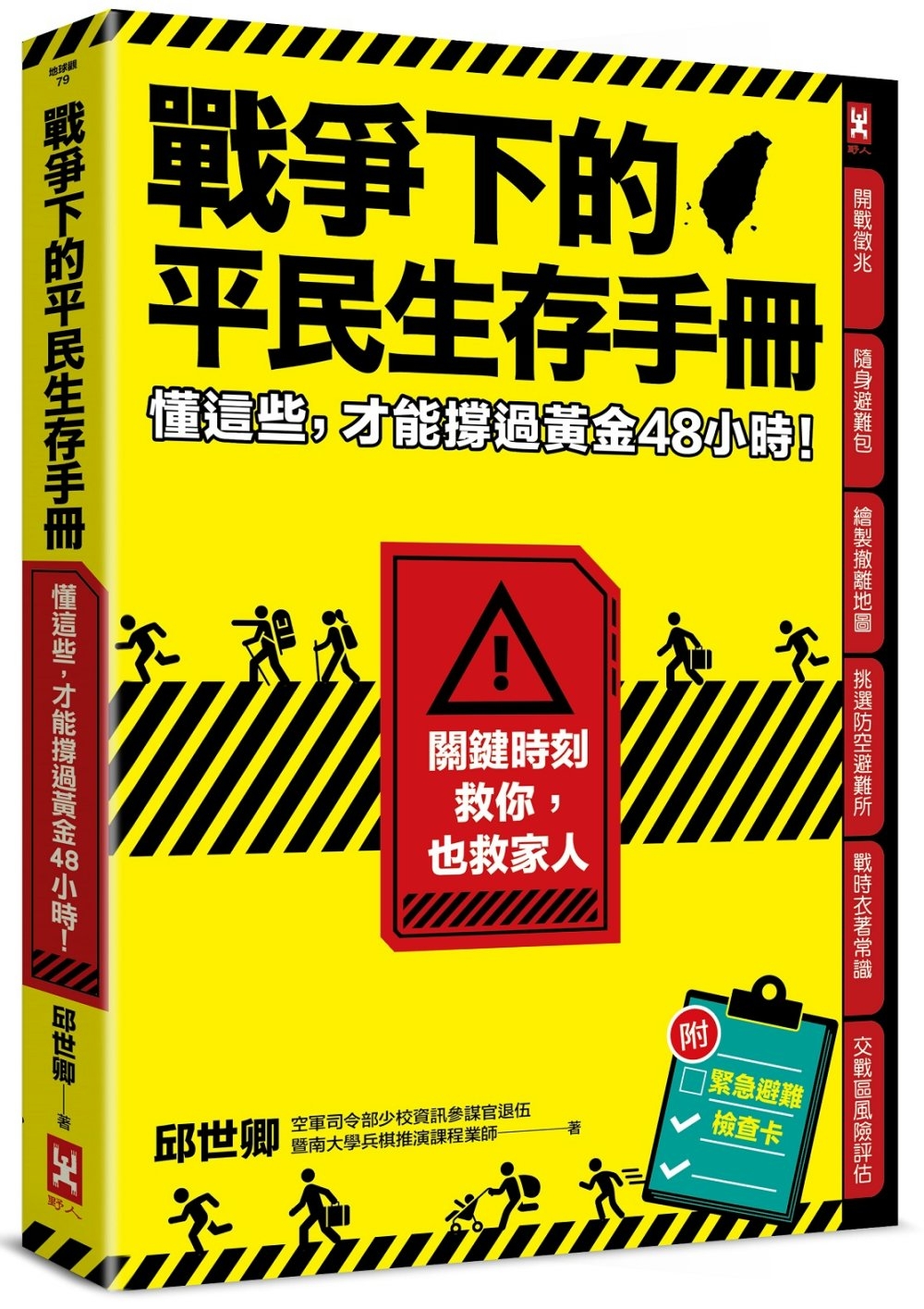自序
《論戴震與章學誠》初版於一九七六年由香港龍門書店刊行,距今恰恰已二十年整。龍門書店大約在十年前便歇業了,故本書已成絕版。二十年前的舊作,其得失優劣早已為同行的讀者所熟知,原沒有重刊的必要。但是一九八五年《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問世,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新資料;經過反覆研讀之後,我竟獲得了一個始料未及的新發現。過去我們讀到章學誠所經常提及的「文史校讎」四個字時,總以為是泛指他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部著作而言,甚至誤認為即是這兩部專著的簡稱。而且自胡適撰《章實齋先生年譜》(一九二二)以來,根據章氏的自述,《文史通義》的草創早於《校讎通義》也久已成為定論。現在我們才能斷定「文史校讎」是章氏特創的專門術語,用以描述他自己的學術「門路」,並持之以與戴震的「經學訓詁」相抗衡。這一關鍵性的概念獲得澄清之後,不但章氏的成學過程層次分明,而且他的文史理論的針對性也更為顯著,這一新發現對於《論戴震與章學誠》的中心論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最初深察及此,則內篇的論證必能更為緊湊,論點也更為集中。由於全部改寫是我的時間所不允許的,因此我特撰〈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一文,作為內篇的補正。凡是內篇與〈考論〉之間分歧的地方,都以後者為準。這一新發現也是本書重印的主要理由。
趁著改版的機會,我也改正了原書中一些個別的錯誤或不穩妥的說法;還有少數地方增添了文獻的證據。初版〈附錄〉曾收入戴震和章學誠的重要佚文多篇,增訂本已全部刪除。這是因為《戴震全集》和《章學誠遺書》已陸續出版,這些佚文不再有重印的必要了。又增訂本外篇補入〈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兩篇長文。這兩篇文字所討論的正是戴震與章學誠的思想史的背景,與本書可以互相印證之處甚多,且可補內篇第三章〈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之簡略。讀者兼觀並覽,更可以明瞭本書立論的歷史根據。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內在理路」闡明理學轉入考證學的過程。因此明、清之際一切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變動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所投射的影響,本書全未涉及。然而我並不是要用「內在理路」說來取代「外緣影響」論。在歷史因果的問題上,我是一個多元論者。歷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變動,其造因都是極其複雜的;而且迄目前為止,歷史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試圖將歷史變動納入一個整齊系統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內在理路」說不過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謂"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須指出,這種「自主性」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學術思想的動向隨時隨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我之所以強調「內在理路」,是因為它足以破除現代各種決定論(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決定意識」之類。「內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嚴格限定的,它祇能相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傳統或學者社群而成立。宋明理學家和清代考證學家都是研究儒家經典的,他們無疑屬於同一研究傳統之內。他們不但處理著同樣的經典文獻,而且也面對著共同的問題──儒家原始經典中的「道」及其相關的主要觀念究竟何所指?這是儒學傳統內部的問題,自有其本身發展與轉變的內在要求,不必與外緣影響息息相關。懷德海(A. N. Whitehead)說,一部西方哲學史是對於柏拉圖的一系列的註腳,也正是關於「內在理路」的一種解說,我們決不能拘泥字面,真以為全部西方哲學史都沒有跳出柏拉圖思想的範圍。無論如何,經典考證早在十六世紀便已崛興,而且確然是由理學的爭論所激發出來的。「內在理路」可以解釋儒學從「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其文獻上的證據是相當堅強的。不但如此,清代學者如凌廷堪、龔自珍等也已自覺到理學之變為考證,曾受「內在理路」的支配。
我在本書中雖然採取了「內在理路」的觀點,但是我並未將它與「外緣影響」對立起來。相反地,我仍然承認清末以來的政治影響說──清代的文字獄──是有根據的。在我的全部構想中,「內在理路」不過是為明、清的思想轉變增加一個理解的層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緣解釋,而且也可以與一切有效的外緣解釋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唯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入「內在理路」,則終不能盡其曲折,甚至捨本逐末。
但自本書出版以來,「內在理路」說曾引起一個相當普遍的誤解,不少讀者都以為我治思想史有取「內」捨「外」的偏向。以正式見諸文字的評論而言,一九七七年我的朋友河田悌一氏(當時還不相識)在《史林》六○卷五號所發表的書評已提出這個疑問。一九八三年島田虔次教授為《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第三卷(京都,同朋舍)寫中國思想史的部分,對本書的「內在理路」說也提出了詳細的討論,認為政治、社會等外緣的因素終不容忽視(見頁283-285)。這些評論是很自然的,但仍不免誤會了我的原意。所以我感覺有必要再重申我的論點如上。
事實上,我研究明、清思想史自始便注重思想動向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在七十年代,我的論述重心確是集中在「內在理路」方面。但是一涉及思想史與社會史的交互影響,我們便必須突破「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這些久已約定俗成的框架。自十六世紀以來,儒家的政治、社會思想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但卻非「理學」、「考證」的範疇所能包括,因此也就不在研究理學和考證學的專家的視野之內。他們往往以為理學與考證學便足以概括明、清儒學的全部或主要內容。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在明、清思想史一方面的研究重心已轉移到外緣的領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和《明清社會變動與儒學轉向》三篇專論。儘管其中主要的儒家人物與本書所論頗相重疊,但取材與問題卻截然不同。所以在這三篇專論中我都沒有涉及理學與考證學。「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各有其應用的範圍,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但是儒學的概念必須擴大,不能為傳統的名目所拘限,這是我必須鄭重指出的。
最後,我願意列舉本書未收但關係密切的幾篇論文,以供讀者作進一步的參證。中文論文兩篇:
一、〈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一九八七),頁405-483。
二、〈《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一九八四),頁77-91。
這兩篇都取「內在理路」的立場。前一篇較詳盡,後一篇則借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典範」("paradigm")說,使一般行外的讀者易於理解。我在初撰本書時並未參考孔恩的新理論,但後來發現他的理論主要也是闡釋「內在理路」的,因為「典範」的轉換基本上出於「科學界」("scientific community")內部的共同判斷,雖然個別科學家決定改變其「典範」也可以受到外緣因素的影響。
英文論文則有下列四篇:
一、"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nos. 1 & 2, December, 1975, pp.105-146.
二、"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Hong Kong, 1982, pp.376-392.
三、"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II, part I, 1989, pp. 79-108.
四、"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p. 121-154.
這四篇英文論文在取材上與本書大體相同,但寫法和論證方式則頗有不同。讀者比較觀之,可以更了解本書的中心旨趣所在。
余英時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序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