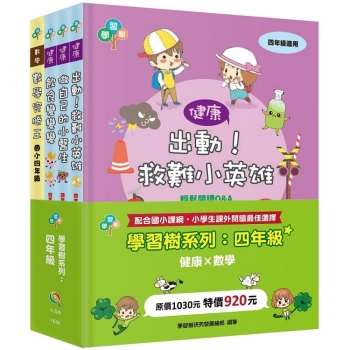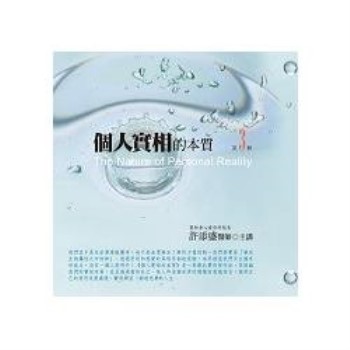保羅在親眼看到安妮之前,心中早已勾勒出她的形象;在真正了解她之前,其實也已經了解她了──否則為何他會不自覺地把她想像成陰沉邪惡的女人?每次她進房間,保羅就想到哈格德(H. Rider Haggard,英國作家,作品以《索羅門王寶藏》最為知名,譯註)小說中,非洲部落崇拜的那些神偶啦、石頭啦,還有悲慘的厄運。
把安妮.維克斯跟《索羅門王的寶藏》裡的非洲神偶聯想在一起,真的很滑稽,卻又恰如其分。安妮是個壯碩的女人,雖然她那件一成不變的灰色開襟羊毛衫下拱著一對臃腫的奶子,但身材實在毫無曲線可言──她沒有渾圓的臀線;家居長裙下,連小腿的弧度都看不出來(安妮外出處理雜事時,會回房間換牛仔褲)。她身材胖壯,全身癡肥笨重,毫不靈巧。
更重要的是,保羅覺得這個女人冷漠嚴峻得令人毛骨悚然,彷佛她身上沒有半條血管甚至內臟;好像她從頭到腳就是一個堅硬的固體。保羅越來越覺得安妮的眼睛看起來雖然會動,卻是畫上去的,就如同那些掛在房裡的肖像畫一樣,眼睛似乎會隨著觀看者移動。如果他用兩根手指比出V字,插進她的鼻孔裡,搞不好會碰到硬梆梆的固體(如果還塞得進去的話);就連她的灰羊毛衫、難看的家居裙,以及褪色的牛仔褲,也都是她那僵硬身體的一部分。保羅會覺得安妮像小說裡的神偶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安妮跟神偶一樣,只給人一種感覺:把人的不安慢慢轉化成恐懼,並把其他的一切都奪走。
不對,等一等,這種說法有失公允。安妮其實還給了他別的,她給他藥丸,給他將潮水引來淹去殘樁的藥丸。
那藥丸就是潮水;安妮.維克斯是月亮的引力,將藥丸像漂流物般引入他嘴裡。她每六個小時為他送來兩粒藥,一開始保羅只能感覺安妮的兩根手指插入他口中(儘管藥非常苦,但保羅不久便學會用力對著探進來的手指吸吮了),後來保羅能張眼看到安妮穿著開襟衫、六件換來換去的裙子、腋下常夾著一本他的小說,進來幫他餵藥。到了晚上,安妮會換上毛絨絨的粉紅色長袍、臉上的乳液塗得油亮(保羅雖然沒看到乳液瓶,卻能輕易得知乳液的主要成分;那強烈的綿羊油味一聞即知),掌心放著藥丸,在窗外那餅明月的照射下,將他從深沉的昏睡中搖醒。
過了一陣子──當保羅再也不能不管──之後,他終於明白安妮餵他吃什麼了。那是一種加了強力鎮靜劑的止痛藥,叫「拿威力」。安妮之所以很少幫他送便盆,一來是因為他只吃流質和膠質食物(之前他還墜在五里霧時,安妮曾幫他做靜脈注射),二來拿威力常造成患者便秘。拿威力另一項較嚴重的副作用是造成過敏患者的呼吸抑制現象。保羅雖然已當了十八年的煙槍,卻不是特別敏感的人;饒是如此,他的呼吸還是至少停止過一次(也許在昏迷中還發生過幾次吧,但保羅都不記得了),那回安妮就是在幫他做嘴對嘴人工呼吸。或許那只是意外,但保羅不免懷疑,其實是因為安妮粗心大意,讓他服藥過量,差點害死他。安妮以為自己懂,其實並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而這只是安妮令他心驚肉跳的其中一項而已。
保羅從黑暗中掙脫出來後的十天內,搞清楚三件事情。第一,安妮.維克斯有一大堆拿威力(事實上,她手上有各種藥品);其次,他對拿威力上癮了。第三,安妮.維克斯是個危險的瘋子。
黑暗之後是疼痛與昏脹;當安妮告訴他事情原委時,保羅漸漸想起墜入黑暗前的事了。他一醒來,便跟所有從昏迷中甦醒的人一樣,問安妮現在是何時、在何地,安妮說這兒是科羅拉多州的塞溫德小鎮,還說保羅的八本小說她至少都看過兩遍,而她最愛的《苦兒》系列則讀過四、五回,也許六回了。她說真希望保羅能寫快一點,她雖然檢查過他皮夾裡的身分證,但還是幾乎無法相信,她的患者竟然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羅.薛頓。
「對了,我的皮夾呢?」他問。
「我已經幫你收好了。」她說,原有的笑容突然一斂,化為滿臉的戒慎,保羅很不喜歡這樣──像是在繁花遍布的夏日草原上,發現一道溝隙一樣。「你以為我偷你皮夾裡的東西嗎?」
「不是,當然不是,只是──」只是我剩下的那半條命都在皮夾裡啊,他心想。我在這房外的半條命、遠離疼痛的半條命,遠離時間、一如孩童口中拉展的粉色泡泡糖一樣沒完沒了的那半條命啊。因為在服藥前的一小時,在藥送達之前,時間真的是漫無止境。
「只是什麼,先生?」她執意問道,保羅警覺到安妮的臉越拉越長。剛才那道溝隙逐漸撐開了,她眉毛下彷彿發生地震。保羅可以聽見風聲在外頭呼號,他突然想像安妮一把將他抬起,像粗麻袋似地將他扛到外頭,然後丟棄在雪堆裡。他會凍死,可是在死掉之前,會因腿痛而哀號不止。
「只是我老爸一向要我看緊自己的皮夾。」保羅很訝異自己可以說謊說得這麼溜。他老爸能不看他就絕不多瞄一眼,而且就保羅記憶所及,老爸這輩子只給過他一次建議。十四歲生日那年,老爸拿了一個錫箔紙包的紅魔牌保險套給他。「把這玩意兒放到你皮夾裡,」羅傑.薛頓說:「萬一你在露天電影院裡發情,記得在開始衝動和太衝動間的空檔裡,把這玩意兒套上去。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私生子啦,老子可不想看到你十六歲就當爸爸。」
保羅接著說:「大概是他千叮嚀萬囑咐地要我看緊皮夾吧,這話已經烙在我心裡了。如果我有冒犯你的地方,請多見諒。」
安妮放鬆下來,微微一笑,溝隙填上了,夏日的花朵再次愉快地點著頭。他很想推推那朵微笑,卻只觸著一片黑暗。「我不會生氣的,皮夾放在很安全的方,等一等──我有東西要給你。」
安妮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湯來,湯上飄浮著蔬菜。保羅無法喝多,但已經比預期喝的多了。安妮似乎頗為開心,保羅喝湯時,她把發生的事告訴他,保羅邊聽邊回想,知道自己怎麼會落到雙腿傷殘的下場,也許不算壞事吧,但是那知道的過程實在令人心驚──彷彿他是故事或劇本裡的人物一樣,而且角色的遭遇不是平舖直敘地說出來,而是像小說一樣充滿了懸疑。
安妮開著她的四輪傳動車到塞溫德買飼料和一些雜物……順便去威森藥局看看書──那差不多是兩週前的星期三了。通常平裝版新書會在週二送到。
「我當時正在想你呢。」她說著把湯舀進他嘴裡,然後熟練地抓著餐巾一角幫他把湯汁拭淨。「好巧喔,對不對?我以為《苦兒的孩子》平裝版已經上架了,可惜沒有。」
安妮說,當時暴風雪快來了,可是當天一直到中午,氣象預告都還斬釘截鐵地說暴風會往南折向新墨西哥和克里斯托。
「是啊,」保羅回憶道:「他們說暴風會轉向,所以我才會去那裡。」他試著移動雙腿,結果換來一陣劇痛,讓他忍不住呻吟。
「別亂動,」安妮說:「保羅,你的腿要是痛起來,可止不住的……我兩小時內不能再給你藥了,我已經餵你吃太多藥。」
為什麼我沒有在醫院裡?保羅很想問,可是又不確定現在可以問,所以還是暫時別問的好。
「我去飼料店時,東尼.羅伯特叫我最好在暴風雪抵達前趕回家,我說──」
「我們離塞溫德多遠?」他問。
「滿遠的。」她含糊其詞地把眼光飄向窗口,二人一陣沉默,氣氛詭譎。接著保羅被眼前的景象嚇著了,他看到安妮臉上一片空茫;黑黝黝的溝隙橫在高山的草原上,那裡寸草不長,深不見底。女人的表情彷彿忘掉了自己的所有事情與經歷,她不僅忘了自己正在描述一件事情,連記憶本身似乎也都忘了。保羅曾經參觀過精神病院──那是多年前他在為苦兒系列的《戰慄遊戲》找資料而去的。《戰慄遊戲》是他過去八年來,四本主要收入來源的第一部作品──保羅看過這種表情……或者更確切地說,看過這種「面無表情」。這種表情有個專有名詞,叫緊張症,但令保羅畏懼且更無以名狀的是:在那瞬間,保羅以為安妮的心智跟她的肉體一樣,變得堅硬如石、百箭不穿,且毫無通融餘地了。
之後安妮的臉又慢慢轉亮起來,心思似乎又流回來了。保羅發現「流」這個字並不恰當,安妮其實更像池子或潮汐造成的水灘一樣,慢慢地注入水;她是在暖身。是的……她在暖身,像烤麵包機或電毯等小家電一樣在暖機。
安妮將三頁打好的原稿放在保羅旁邊的床斗櫃上,保羅等著聽她評論。他很好奇,但不怎麼緊張──他很訝異自己竟能輕而易舉地返回苦兒的世界。那世界雖然粗俗、乖離,但事實上,回到那裡並沒有他預期中的討厭──老實說,反倒像穿上舊脫鞋,讓人覺得相當舒服哩。
因此當安妮表示「這樣不對」時,保羅忍不住張大嘴,吃驚地問:「你──你不喜歡?」他簡直不相信。喜歡其他苦兒系列的安妮,怎麼可能不喜歡這個開場白?這完全是苦兒的翻版,簡直近乎重抄了嘛,藍蜜奇太太在眝藏室裡張羅,伊安和苦兒則像兩個剛從週末舞會溜回家的高中小鬼一樣黏在一起,這有啥不對,還有──
現在換安妮露出不解了。
「不喜歡?怎麼會,我當然喜歡了。寫得真好,伊安將苦兒擁入懷裡時,我都看到哭了,我忍不住嘛。」說著安妮的眼睛還真有點紅哩。「你用我的名字為湯瑪士的保母命名……真是太窩心了。」
保羅心想:也很聰明──至少我是這麼希望的。順便告訴你,小姐,也許你會對這個有興趣;寶寶的名字本來叫史恩,我把名字換掉,因為覺得裡頭的n太多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不,你弄錯了。我沒說我不喜歡,我只說這樣不對,那是在作弊,你得改。」
他竟以為安妮是最完美的讀者?唉,天啊,真有你的,保羅──你不犯則矣,一犯就是大錯。這位孜孜不倦的讀者,已經變成鐵面無私的老編了。
保羅本能地重新調整表情,露出他在聽編輯說話時慣有的誠懇模樣。他稱這種表情為「我能為您服務嗎,小姐?」因為大部分編輯都是那種會把車開到修理站,命令技師限時搞定車蓋或儀表板下奇怪聲響的小姐。這種專心致志的表情通常很有用,因為能哄她們開心。編輯一開心,有時就會放棄一些詭異的點子。
「怎麼會是作弊?」他問。
「嗯,傑佛瑞趕去找醫生這點是沒問題啦。」她說,「那是在《苦兒的孩子》第三十八章裡的事,可是醫生從未趕到,這點你也很清楚,因為傑佛瑞想駕馬從康瑟普那個糟老頭的門上跳過,結果絆到門檻了──我希望那個爛人在《苦兒還魂記》裡得到報應,保羅,我真的希望他不得好死──害傑佛瑞肩膀或肋骨斷掉,在雨裡躺了一夜,直到牧羊的孩子過來發現他為止。就是這樣,醫生才一直沒趕到,對吧?」
「是啊。」保羅發現自己突然無法將眼神從她臉上移開了。
保羅原以為她以編輯自居──甚至自以為是合著者,打算告訴他該寫什麼,該如何寫,但實際上不是這樣。拿康瑟普先生為例吧,安妮希望康瑟普能得到報應,可是並沒有命令他這麼做。安妮雖控制了保羅,卻將小說的創作過程置於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然而有些事就是做不到,這跟有沒有創作力無關,硬要做的話,就像挑戰重力或拿磚塊打桌球一樣,會徒勞無功。安妮確實是位忠實讀者,但忠實讀者並不等於愚昧的讀者。
她不准保羅殺掉苦兒……可是也不許他用作弊的方式讓苦兒復活。
可是媽呀,我確實已經將苦兒賜死啦,保羅疲憊地想,你到底要我怎麼辦?
「我小時候,」安妮說:「電影院經常演章回電影(Chapter Play),一個禮拜放映一段故事。《蒙面復仇者》、《飛俠哥頓》,甚至還放過《獸神巴克》,那傢伙去非洲抓猛獸,他只要瞪著獅子老虎,就可以馴服牠們。你記得那種章回電影嗎?」
「記得,可是你的年紀不可能那麼大吧,安妮──你一定是在電視上看的,要不就是聽你哥哥或姊姊說的。」
安妮的嘴角在僵硬的臉上牽動了一下。「別亂說話,你這個呆子!不過我確實有個哥哥,以前我們每週六下午都去看電影,那是在加州貝克斯田的事,我在那兒長大的。我雖然一向喜歡看新聞影片、彩色卡通和劇情片,卻更期望看下一集的章回電影。我發現自己一整個星期都在想電影的事,如果上課無聊,或幫樓下克姆茲太太照顧她那四個皮得要死的小混蛋時,我就會想著電影。以前我好討厭那幾個小鬼。」
安妮陷入某種情緒中,靜靜望著角落。她的電源拔掉了,幾天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形。保羅不安地想,那是否意味著安妮的情緒跌到谷底了?若是這樣的話,他最好別輕舉妄動。
安妮終於又回神了,而且跟往常一樣,帶著微微的詫異,彷彿沒想到世界依然存在一樣。
「《火箭俠》是我的最愛,第六回《天空之死》結尾時,他在飛機全力俯衝時昏過去了;第九回《火焰未日》最後火燒倉庫時,被綁在椅子上。有時是車子煞車壞了,有時是毒氣,有時是電擊。」
安妮講起這些事來熱情洋溢,情真意切到令人發毛。
「那叫冒險連續片,」保羅插嘴說。
安妮對他皺皺眉,「我知道,自以為是先生。天啊,有時候我覺得你一定是把我當成笨蛋了!」
「我沒有,安妮,真的沒有。」
她不耐煩地對他揮揮手,保羅知道最好別打斷她──至少今天別惹她。「我試著想像他的脫困辦法,那實在非常有意思,有時我想得出來,有時沒辦法。其實我不是很在乎啦,只要劇情沒有編得太離譜就行了。」
她眼神銳利地看著保羅,確認他是否聽懂她的意思。保羅根本不可能沒看到。
「像他在飛機裡昏過去後又醒來,發現座椅下有降落傘,便穿上它,從飛機跳下來,這就編得合情合理。」
只怕所有英文作文老師都會反對你的說法,親愛的,保羅心想,你剛才說的情形有個術語,叫「解危之神」,最早用於希臘圓形劇場。劇作家筆下的英雄遇到沒辦法解決的困難時,舞台上空便會降下一張裝飾著花朵的椅子,英雄坐上去,然後被拉上去,就遠離災難了。就算最笨的阿土也能領略其中的意涵──大英雄被神仙救走啦。可是這個別名又叫「座椅下的舊降落傘」的「解危之神」,終於在一七○○年左右退流行了。當然了,《火箭俠》系列跟《南西杜爾》系列例外。我猜你大概沒看到消息吧,安妮。
在這可怕而令人畢生難忘的片刻裡,保羅以為自己會放聲大笑,照安妮今早的情緒看來,他一定會死得很難看。保羅趕緊用手遮住嘴巴,掩去即將爆發的笑意,然後假裝咳嗽。
她用力拍他的背,拍得他好痛。
「好點沒?」
「好多了,謝謝。」
「現在我可以走了嗎,保羅?你會咳不停嗎?要不要我拿水桶進來?你想吐嗎?」
「不用了,安妮,請走吧。你剛才說的話太有意思了。」
她看來情緒稍緩──不多,只稍稍緩和了一些。「他在座位下找到降落傘,還算合理,雖然不盡然寫實,但還算合理。」
他想了想,心中十分震驚──安妮偶爾展現的洞悉力總是令他驚詫──安妮說得沒錯,合理與寫實在許多層面上也許都算同義字,但在寫作的天地裡則不然。
「結果你另起一個故事,」她說:「你昨天寫的東西就錯在這裡,沒有接著以前的情節寫,保羅,你聽我說,」
「我很努力在聽啊。」
她打量著他,看他是不是在開玩笑,然而保羅的臉色又蒼白又嚴肅──看起來像個乖學生。他原本想笑,可是當他發現安妮其實很清楚「解危之神」的技倆,只是不知其名而已後,就笑不出來了。
「好吧,」她說:「這一章跟煞車有關。有一群壞蛋把火箭俠──但他的身分是個秘密──丟進沒有煞車的車子裡,然後關上車門,將車推下蜿蜒曲折的山路。告訴你,我那天看得簡直如坐針氈。」
安妮就坐在他的床沿──保羅坐在對面的輪椅上。自從他擅闖浴室和客廳後,已經過去五天了,他歷經大難後的復原速度似乎遠超過自己的想像,光憑沒被安妮逮到這點,就令他元氣大振了。
安妮心不在焉地望著月曆,上面的男孩微笑著駕雪橇滑過漫無終止的二月。
「可憐的火箭俠困在車子裡,身上既沒裝備,也沒頭盔。他得同時駕車、設法停車並打開車門,比一個獨臂裱糊工人還忙!」
是的,保羅突然看到那個畫面了──他本能的發現這樣的場景雖然誇張,卻能製造懸疑。畫面上是呼嘯而過的陡坡,接著跳到被男主角踩到底的煞車板(保羅清楚地看到那隻腳上套著四○年代的男鞋)、轉到男主角撞擊車門的肩上、再跳到車門外側,讓觀眾看到焊死的門。劇情雖然又驢又俗,效果卻棒得令人心跳加快。這裡套的不是香醇的佳釀,而是粗烈的私酒。
「接著你看到道路只通到懸崖邊嘎然而止,」安妮說:「戲院裡每個人都知道,如果火箭俠在車子抵達懸崖前無法從車中掙脫的話,就死定了。噢,天啊!車子衝過去,火箭俠拚命煞車撞門,接著……車子飛出懸崖了!然後開始下墜。在摔落途中撞到崖壁,起火燃燒,接著墜入海裡,銀幕上出現結尾的字幕,請收看下集,第十一回,飛龍在天。」
安妮坐在保羅床邊,兩手緊握,豐滿的胸口快速起伏。
「怎麼樣?」她問,眼睛盯著牆壁,沒看保羅。「之後我就無心看其他電影了。接下來的一週,我簡直無時無刻不想著火箭俠,我苦思火箭俠能如何逃脫?卻連猜都猜不到。」
「隔週的週六中午,我站在電影院前,雖然售票亭要一點十五分才開,電影兩點才上映,可是,保羅……後來的事……唉,你永遠也猜不到!」
保羅沒接話,但他猜到了。他明白為什麼安妮雖喜歡他寫的東西,卻覺得不妥當──安妮是以忠實讀者的身分,理直氣壯地在質問作者,而不是用編輯那種有時稍嫌曲高和寡的態度來批判。保羅理解這點,而且他發現自己竟覺得慚愧。安妮說得對,他的寫法形同欺騙。
「新的故事總是先從上一集的結尾演起,火箭俠衝下山,畫面上出現了懸崖、火箭俠猛撞車門、拚命開門等鏡頭。接著就在車子滑到懸崖邊時,車門打開了,火箭俠撲到路面上!車子翻落懸崖,電影院裡所有的孩子齊聲歡呼,因為火箭俠逃脫了,可是我沒歡呼,保羅,我氣炸了!我開始大吼,『上星期不是那樣演的!上星期才不是那樣演的!』」
安妮跳起來開始在房裡快速踱步。她垂著頭,頭髮散亂,一隻手握拳,擊著另一隻手掌,眼中冒出怒火。
「我哥哥叫我別鬧,可是我停不下來,他就用手摀我的嘴要我住口,結果被我咬,我繼續大叫,『上星期不是那樣演的!你們怎麼那麼笨,都不記得嗎?你們都得健忘症啦?』接著我老哥說,『你瘋啦,安妮。』可是我知道我沒瘋。戲院經理走過來說,如果我不閉嘴,就得離開,我說:『走就走,因為那電影在騙人,上星期才不是那樣演的!』」
安妮看著保羅,保羅看見她眼中的殺機。
「他沒有逃出那輛天殺的鳥車子!車子翻出懸崖時他還在裡頭!你明白嗎?」
「我明白。」保羅說。
「你明白嗎?」
她突然一臉兇相地向他跳過來,保羅雖然認定安妮想跟以前一樣傷害他──也許是因為她沒辦法揍那個欺騙觀眾、讓火箭俠在車子翻落懸崖前逃出來的劇作家吧──身體卻動也不動。保羅可以從安妮剛才敘述的往事,了解安妮目前情緒不穩的原因,不過他也對安妮既孩子氣、又純然真實的義憤填膺有些敬畏。
安妮沒有打他,她抓緊保羅的衣襟,將他拉向前,直到兩個人的臉幾乎碰在一起了。
「真的嗎?」
「真的,安妮,我懂。」
安妮瞪著保羅,漆黑憤怒的眼神大概看穿了他的心意,因為一會兒之後,安妮又很不屑地將保羅摔回椅子上了。
保羅痛得肝腸寸斷,片刻後疼痛才逐漸減緩。
「你明白哪裡不妥囉?」她說。
「我想是的。」雖然我他媽的完全不知道要從何改起。
另一個聲音立即響起:我不知道老天是要整你還是救你,保羅,不過有件事我倒是很清楚:如果你不想辦法用安妮可以信服的方式讓苦兒死而復生,這肥婆就會宰掉你。
「那就去改吧。」安妮短短撂下幾個字,走出房間。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換不同的紙。」安妮回來把打字機和紙張放到板子上時,保羅說道。
「跟這不一樣的紙嗎?」她拍拍紙上的泡棉問,「可是這是最貴的紙啊!我去紙店時問過了。」
「你媽沒告訴過你,最貴的東西未必是最好的嗎?」
安妮臉一沉,原有的抗拒頓時化為不悅,保羅猜想,繼之而來的將會是狂怒吧。
「沒,我媽沒有,自以為是先生。她只告訴我說,一分錢一分貨。」
保羅發現,安妮的情緒就像中西部的春季,滿載著龍捲風,等待隨時狂飆。如果他是農夫,若看到天色變得跟安妮目前的臉色一樣,一定會立即衝回家人身邊,將他們趕到地窖避難。安妮眉頭泛白,鼻孔不住張縮,像聞到焦味的野獸。她的手又開始快速地張開握緊,不斷將空氣抓到掌心裡。
他需要安妮,在安妮面前,他手無縛雞之力,他知道自己應該讓步,及時安撫她──如果他還有時間的話──就像哈格德的小說中,對神偶獻祭,以安撫憤怒女神的部族一樣。
可是他心中還有另一股更精明也較勇敢的聲音提醒他,如果每次安妮發脾氣,他就害怕而軟語相應,他便無法勝任莎赫札德的角色了。如果他態度硬一點,安妮會更生氣吧。那聲音分析道,若不是她對你有所求,應該會立即將你送到醫院,或將你殺害,以免被雷蒙斯發現──因為對安妮來說,世上的人全都是雷蒙斯,他們躲在每一株樹叢背後。保羅啊,如果你現在不跟這臭婊子周旋,我的孩子,你就永遠也辦不到啦。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戰慄遊戲的圖書 |
 |
戰慄遊戲 作者:史蒂芬.金 / 譯者:柯清心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153 |
社會人文 |
$ 350 |
驚悚/懸疑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戰慄遊戲
暢銷書作家保羅.薛頓剛完成可以參加美國書卷獎的大作。他駕著名貴跑車,打算度假,好好放鬆一番時,在半路遇上暴風雪,出車禍困在車內,被安妮.維克斯救起。安妮.維克絲是保羅.薛頓的頭號書迷,細心照料他殘破的身軀。不過,保羅也成為安妮的獵物,被拘禁在與世隔絕的屋舍中。安妮希望保羅專為她寫一部最棒的作品──《梅瑟琳還魂記》。安妮有許多鞭策保羅的辦法,一是針筒,二是斧頭。若兩者皆無法奏效,安妮還有許多法寶可以派上用場……史蒂芬.金的驚悚力作《戰慄遊戲》,描寫瘋狂女書迷變相綁架作家,更用激烈的手段左右小說的結局。本書是全台灣史蒂芬.金小說迷引頸企盼的《戰慄遊戲》中文全譯本;在1990年改編為電影,女主角凱西.貝茲以本片榮獲奧斯卡影后;她所演出的安妮.維克絲在美國電影學會票選的「百大螢幕英雄與壞蛋」中名列第17。
TOP
章節試閱
保羅在親眼看到安妮之前,心中早已勾勒出她的形象;在真正了解她之前,其實也已經了解她了──否則為何他會不自覺地把她想像成陰沉邪惡的女人?每次她進房間,保羅就想到哈格德(H. Rider Haggard,英國作家,作品以《索羅門王寶藏》最為知名,譯註)小說中,非洲部落崇拜的那些神偶啦、石頭啦,還有悲慘的厄運。把安妮.維克斯跟《索羅門王的寶藏》裡的非洲神偶聯想在一起,真的很滑稽,卻又恰如其分。安妮是個壯碩的女人,雖然她那件一成不變的灰色開襟羊毛衫下拱著一對臃腫的奶子,但身材實在毫無曲線可言──她沒有渾圓的臀線;家居長...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史蒂芬.金 譯者: 柯清心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7-01 ISBN/ISSN:9789573258148
- 裝訂方式:平裝
- 商品尺寸:長:21mm \ 寬:148mm \ 高:209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