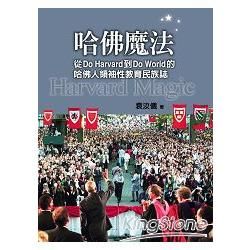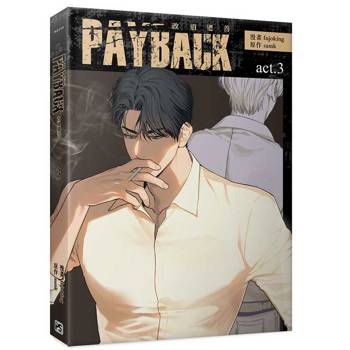導讀
《哈佛魔法》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除了文字流暢、概念清晰之外,最主要的有三個理由,一是《哈佛魔法》讓我看見「宇宙」、「旅人」、「旅程」的概念,二是《哈佛魔法》所顯示的民族誌魔法,三是透過《哈佛魔法》所揭露的美國價值。
《哈佛魔法》的宇宙、旅程與旅人
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瞭解一下七○年代末的科幻電影《星際大戰》。我這麼說,是有原因的,因為我認為《星際大戰》是《哈佛魔法》書寫底層的美國喻涵架構(metaphor or metaphorical framework)。
我和袁汝儀是老朋友,八○年代,她和她的先生與我都留學於美國奧勒崗大學,雙方家庭交好,經常分享彼此的想法。記得有一次,我們再一起聊天,剛好聊到科幻電影,袁汝儀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潘英海,你一定要去看《星際大戰》,帶著老婆小孩一起去看。」接著,在我的詢問之下,她娓娓說了許多要去看的理由。晃眼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的細節已不復記憶,但是,我永遠記得當時她提到《星際大戰》時的興奮神情。我們一家去看了,都很喜歡,之後便也成了《星際大戰》的影迷。《星際大戰》這部電影,是描寫一個遙遠銀河系中各種旅人的旅程,也包括為了維護和平正義使命的絕地武士,穿梭於各種宇宙之間,與各種邪惡勢力鬥爭。
重點不在於去瞭解《星際大戰》,而在於《哈佛魔法》中四位旅人(約翰、黛君、茹絲、潔西卡)的旅程、他們的會合點(哈佛AIE機構)、以及揭露哈佛魔法的三個主要宇宙(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並藉此我們得以接近美國的宇宙觀、價值觀以及教育觀。我認為,如果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理解「宇宙」、「旅人」、「旅程」這幾個基本概念,這是具有理論性的「隱喻」。詮釋學大師保羅.里柯(Paul Ricouer)認為「隱喻」是「文本」解讀的最重要關鍵。1在「隱喻」與「文本」的辯證性過程中,借用人類學者葛茲(C. Geertz)的概念來說,讀者就可以深入瞭解作者的意圖,對「文本」進行「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2
《哈佛魔法》的民族誌魔法
解讀《哈佛魔法》,我想還要理解另一個魔法,那就是,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ethnographer's magic)。
袁汝儀的藝術教育研究,一直採用人類學的長期田野工作研究法。這是她第四本以人類學田野工作研究法,蒐集教育民族誌的資料。第一本是在她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當時是以台北市的龍山寺為田野地點,企圖瞭解在地的美學觀。3第二本,是在一所小學裡進行的青少年次文化調查,4第三本,她踏上歐洲,探索荷蘭的藝術師資教育與制度。5第四本,就是這本以美國的哈佛大學為田野地點,研究哈佛的碩士級藝術教育。四次的長期田野研究,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老練。坦白地說,台灣的人類學者雖然有不少到異地研究的學者,但是還沒有像袁汝儀這樣,以歐美國家為田野地點,並進行長期研究者,我認為這點是特別值得肯定的!
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奠基者馬凌諾斯基(B. Malinowski)曾以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說明民族誌的魔法效應。6民族誌的魔法,是將田野工作者的異地體驗與瞭解,透過文字的敘述,帶領讀者穿梭於想像的時光隧道,進入陌生的異文化宇宙,開展異文化之旅。通常,民族誌的魔法只能讓我們體驗一個宇宙,但是《哈佛魔法》讓我們體驗哈佛大學的三個宇宙:公司宇宙、明星宇宙、聖戰宇宙。當我看完《哈佛魔法》的時候,我拍案叫絕,深有所感。
1996-1997年我在國科會補助之下,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前往哈佛。我一到哈佛,最深的感觸是哈佛的人文與學術揉和著濃濃的資本主義氣息。記憶中,哈佛旗下擁有超過460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營利發展非營利的組織。如果我們不從「公司」的角度來理解哈佛的經營,我想我們無法理解資本主義下的哈佛。《哈佛魔法》的重要貢獻之一,我認為,就是透過民族誌的書寫揭露哈佛的「公司宇宙」。
其次,《哈佛魔法》的民族誌書寫,揭露了哈佛亮麗的「明星宇宙」。哈佛大學網羅了數不盡的諾貝爾獎的主,數不盡的各領域名師。哈佛,不僅只是一種學術品牌,更是學術界的好萊塢。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培育哈佛人特殊的領袖氣質,將哈佛人培養成一顆顆閃爍的明星。袁汝儀在AIE(Arts in Education)的研究,顯示「哈佛人」的形塑,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的整合;而「哈佛人」的明星氣質,還賴「領袖性」教育的薰陶,才能讓明星站在高處。
再者,做為一個「哈佛人」是有使命的,對人類要講貢獻的。每個「哈佛人」要面對各自的聖戰,也許是學術的、也許是世俗的、也許是人類文明的……。聖戰宇宙,不僅賦予「哈佛人」使命感,更是創造「哈佛人」認同感與歸屬感─不是單純的學校歸屬感而已,更是一種「聖戰宇宙」的人生價值觀。
《哈佛魔法》的美國價值
台灣的文化與價值觀,雖然是多元的,但是自從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一直深深地受到美國的影響。即使到今天,留學美國還是首選,政治經濟還是受美國左右,文化思想還是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是,我們對美國文化的價值真的瞭解了嗎?我認為,我們的瞭解仍流於瞎子摸象,特別,是對美國教育。
如同《哈佛魔法》在結論中所指出的,「哈佛人」的認同教育,是與哈佛人的「領袖性」教育,同步進行的。學生們入學前的個人聖戰,入學後,由「做哈佛」的聖戰,朝「做世界」的聖戰發展。而這種「追求」的故事,就是美國價值之展現。要之,文化認同,即為一種文化價值的呈現。《哈佛魔法》說明的,不只是一個哈佛的認同過程,也是美國文化價值的內涵及其形塑的歷程。
《哈佛魔法》可以談論的地方很多,個個都值得讀者借鏡、思考。以上三個要點的陳述,只是一種閱讀。閱讀的方式與角度很多,從詮釋學的觀點而言,作者完成「文本」之後,「讀者」最大,不同「讀者」的解讀與同一「讀者」不同情境下的解讀,都顯示「文本」理解的多元、多樣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也都代表一種未來性。7更進一步,「文本」所隱藏的意圖,自有其自主性,與讀者的解讀產生辯證性的理解,帶領讀者進入各自的「旅程」。
《哈佛魔法》不僅只是寫給藝術教育的人看,對哈佛有興趣的人、對教育改革有興趣的人、對領袖教育有興趣的人、對民族誌書寫或教育民族誌有興趣的人,以及想要瞭解美國價值的人,我認為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
潘英海
【導讀者簡介】
潘英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教育文化與生計發展中心主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生活與文化主題小組召集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人類學組召集人。潘教授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文化合成理論、族群研究(平埔族、畬族)、民俗知識、儀式研究、詮釋人類學、知識人類學、數位文化與資訊社會、物質文化研究。
作者序
1997年2月,我教書之外還兼任系主任,剛為我工作的單位: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完成一份申請設立藝術教育碩士班的文件,內容是靠參考各方文獻來編寫,拼拼湊湊的,雖及時送出,但自覺對於「藝術教育碩士級教育」的整個設計,所知實在太少,將來不論通過還是不通過,全案都必須再修訂,執行細節也需要思考。這些工作實際上要如何進行?我並沒有什麼概念,一切問題只能放在心裡。
同年寒假期間,我來到哈佛大學所在的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城郊的劍橋市,訪問我的好友,當時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訪問學者的潘英海教授和他的家人。那時節,雪下得很大,亞熱帶來的我凍得受不了,躲在屋子裡一點也不想出去。到了快要離開前三天,天氣微晴,潘夫人陳淑花女士鼓勵我去哈佛大學看看,我不好意思推辭,決定披掛出門。出發前,因恐在雪地裡亂走太辛苦,先打了一個電話到哈佛大學的總機,問有沒有藝術教育方面的單位─當時就我的了解,哈佛是沒有這樣的單位,與總機人員聊天,純粹是碰碰運氣。哪知總機小姐竟說,一年前教育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正好成立了一個相關的碩士學位單位,應該跟藝術教育有關,我一聽大喜,心想:看這個就行了,一方面對潘夫人有個交代,一方面也了解一下別人藝術教育碩士班是怎麼設計的,將來若需要重寫申請案的話,也可有個參考。
那天,我見了這個碩士班的主任潔西卡.霍夫曼.戴維斯(Jessica Hoffmann Davis),當我們坐下來說話時,卻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碩士班叫一個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的名字:「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簡稱AIE)專班。儘管潔西卡很耐心地說明,說這個班不是從事「藝術教育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rt-education),不是「藝術教師的教育」,不是「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of art),更不是「教育的藝術」(art of education),而是「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是「一種藝術教育上的創新作法」。然後她又說,AIE提供的是「教育者,包括藝術教育者,的訓練」,但重點是教育,不只是藝術或藝術教育。我聽得一片糊塗,似乎我過去對藝術教育的一點概念,及對美國藝術教育的粗淺認識,都落在「不是……」的範圍內。
我知道"Art Education"是我的專業領域的名稱,有時候,為了突顯藝術教育的整合性以及專業性,藝術教育者會使用"Arts Education"這個詞;有時候,為了強調藝術教育的平民化、多元化特質,藝術教育者會使用小寫的"art education"或者複數的"arts education";另外,藝術教育界還有"Education through art"或"Education in the arts"的說法,分別代表「環境論」與「本質論」的觀點,可就是沒聽過"Arts in Education"。再者,潔西卡又說AIE的碩士學生,不用寫碩士論文,修業一年即可獲得學位。如此短促的形式,學生豐富的內涵設計要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個碩士班?老師的教學重點是什麼?學生實際上又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學習參考的地方?一連串的問題及懷疑,引出無窮的好奇心。在大約二十分鐘的會面時間結束前,我倆決定,由我申請來教育學院做訪問學者,若能通過學院的審核,就可以花一年的時間,好好弄個清楚。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此開啟的,是我和AIE長達十年的緣份。
我原初的研究動機非常簡單,我想了解這個所謂「教育中的藝術」的碩士班,到底是什麼?我想使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方法收集資料,用文化詮釋的概念分析資料,了解這個碩士班的藝術教育情形,以便決定AIE的設計,能如何有益於我自己的工作。1998年7月到1999年8月這一年,1我在AIE很努力地旁聽各種課程,積極地進行各種田野調查該做的工作,訪談、觀察、紀錄(日誌、筆記、錄音、錄音帶複製及轉拷)、攝影、蒐集文獻(包括各種文件、影音資料、書籍與期刊)等等,每天忙進忙出,晚上與週末則盡量用來繕打與整理資料,追蹤所有的線索。
在這一年年頭時,在臺灣的系裡,將我一年前提出的研究所設置案,略作修改後又提交出去,到了年尾,我聽說審查通過了,我的原始研究動機霎時消失了大半,然而新的研究動機,卻比之前還要強烈。一年下來,我的田野經驗和累積的資料,足夠我描述與討論AIE,可是我漸有理由相信,AIE不只是AIE,我看到的並不是「全貌」,AIE的教育內涵應不止於必修課堂與傳統所謂正式教育活動之所見,如果執意切割,則我所報告的絕非有意義的片段。
事實上,這一年的工作,讓我覺得整個研究的設想,應該從「以AIE為脈絡的核心」,修正為「在脈絡中的AIE」,也就是仍將AIE當作焦點,但是畫面大為擴大。這麼做的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AIE只有主任與助理共兩人,面對四十幾個學生的,就是這兩人,其他列名的教師只是學生們的選課教師,不參與AIE行政或決策,即使AIE的內部和外部顧問,一年也才見兩次面,這些加起來只有一小群人,不可抹煞的倒是AIE背後的龐大機構。第二、「哈佛」這個名字,對這個大學裡的所有人,和大學以外的人,具有出乎我意料的、強大的符號意義,我無法切割也不可能跳過這個因素,就算以我一人之力,並無可能徹底處理如此大的田野,至少我應該從中選擇一條突出的線索,做進一步的探究。後來我選擇的,就是各種哈佛文獻中不斷強調,而我手中已有的資料也顯示可能有意義的線索:「領袖性」教育。
再度重整之後的研究目標,仍維持以民族誌的方式,描述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院「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但是放在「領袖性」教育的眼光下觀看。所以,這份報告不是要評估AIE的成敗,而是要以「領袖性」教育的觀點,深入描述或詮釋一個藝術教育現象。
就這樣,我釐清了一些疑點,也開闢了新的研究方向,而海外研究一年的期限也已到達。接下來,我必須回到工作崗位,應付一面在臺灣教學、一面在美國做學術研究的現實。2001年暑期7月初到9月上旬,我又回到哈佛教育學院待了三個月,這次時間多花在探索AIE以外的學院行政與大學行政。2004年2月到9月,2趁教授休假期間,除了田野工作,開始一面進行一些院級與校級人員的訪談與資料蒐集,一面閱讀與分析資料、動手寫報告,此次正逢潔西卡退休,史帝夫.賽戴爾(Steve Seidel)繼任。2005年暑假,我除了繼續田野工作與寫作之外,主要是閱讀圖書館中收藏的文獻。2007年寒假重回田野3,主要工作是至各地追蹤旅人(journeyman)現況。2008年完成初稿,暑假來美,向重要研究對象報告研究狀況,補充文獻與田野資料,並就稿件內容向幾位我特別敬重的朋友請教。如此,田野工作約計二十八個月,文字報告重寫、重組無數次,整個研究斷續進行了十年。
研究哈佛AIE,可以說,是明確地挑戰了我的美國留學以及西式教育背景,讓我更加體會到:「跨文化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並非易事,聲稱在美國受過教育,與了解美國並因此而更了解自己,有很大的距離。十年來,我雖常苦於不斷停頓與再啟動,新的觀點與長期的田野工作,卻也幫助我理解了頭一年的田野資料以及後續的發展。時間是民族誌研究效度與信度的最佳保障,時間解決了研究關聯性的疑慮,也化解了我眾多的誤解、盲點與疑問,時間幫助我觀察到只有時間能篩選出來的文化元素,讓我親見變中的不變與不變中的變,並讓田野中的現象能自然地交互解釋,發展至較大週期與較高頻率模式的出現時刻,使田野工作能順勢抵達一個可以合理結束的終點。
將一個教育單位,當作一個文化機構,以文化觀的角度,切入其教育表象,了解其文化的傳承形貌,是教育民族誌的主要工作。這次我研究AIE,與之前研究臺北龍山寺寺廟參與人、臺北縣M國小五年級學生及荷蘭多德瑞克師範學校,比較起來,至少有兩個不同之處。首先,哈佛AIE的環境中,有很多學術性文獻,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將學術文獻孤立看待的習慣,試著將這些學術文獻一體視為文化產物,不只是從個人的學術成就表徵這個角度,來看待學術報告,更注意這些文獻,在其文化脈絡中、從當事人(研究者、作者、解讀者、應用者、出版者與資助者……)的角度,領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後設與前設作用。這個經驗對我來說,是活化學術性文獻的意義,並領會文化觀的在啟發思考上的價值。其次,比起荷蘭的研究來,哈佛這個環境對英語表達的要求,較荷蘭為高,用字遣詞不輕鬆,為免訪談雙方負擔,正式的對話前,我會先準備問題,並要求錄音,其餘則盡力筆記。在田野初期,由於約會時間常嫌短促,我設計了一些幾乎不需要我多插嘴、但具有開放性的訪談架構,譬如說請受訪者圍繞著AIE,談談個人的AIE之前、之中、之後經驗與感受,不想,如此所得之內容十分珍貴,成為後續訪談很好的基礎,並促成最後研究報告,以旅人的隱喻開始切入撰寫,仍依之前、之中、之後的方式,劃分章節架構。
本書中人物身份的透露與否,有下列幾個原則。本書出版時已過世者、歷史人物或名人,用真名。在世者中,哈佛教師部分,除極少數是經同意全面使用真名外,一般教師之學術或專業身份不變,報導者身份隱藏,其餘人士則均使用假名。特殊情形下,會改變或隱藏人物特徵,或略過文獻出處,以避免暴露身份。機構名,無法隱藏者如哈佛大學、教育學院、AIE、零計畫等,予以保留,其餘,若無關緊要則可提,否則避過。批准我進行研究的教育學院,十分尊重我的研究工作,過程中僅由院長發信要求不得對外宣稱研究結果係獲該院認同,或代表該院的意見。
研究資料上,就跟所有的研究一般,僅限於許可之下可取得、可使用、可引用者,寫作也盡量兼顧研究目的與倫理原則。沒有作者、未公開出版或者非學術性資料,引用時在註腳中說明,並盡量顯示原文,學術性資料或公開出版資料,則在註腳中簡單顯示,詳細出版資訊則置於「參考資料」之中。資料量方面,直接與研究經費資源有關,故現有的,已是我可調度資源的極限。訪談資料,均事先請對方簽署同意書與授權書。旁聽課堂係先經教師同意,由教師告知學生,或由其邀我在課堂上做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之後才開始。田野初期,在雙方互信尚未穩固之前,學生的訪談是由AIE安排,後來漸漸開放,但我的謹慎並未鬆懈。
資料整理與寫作是很大的挑戰。本書的寫作,是在沒有預設課題或結論的狀況下就開始動筆,寫作時心裡極為振奮,因寫作本身就能促進思考與分析,越寫越清晰,越寫越知道下一次田野中要問什麼、哪些資料還需補充等等,因此寫作與田野是同時並進的。大量的資料如何合理地依序呈現,並導向合理的結論也是挑戰,不論是章節的安排與定調、與研究對象的敘事距離、文字的風格、閱讀節奏的設定、讀者認知狀態的推斷,以及多元證據的逐漸呈現等等,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寫中緩慢成形。經過一番雕鑿與汰換後的文稿,較能完全專注於結論的呈現,不將資料、分析與討論截然劃分,而是三者依序融合,以更貼近讀者的方式將我的發現寫出來。同時,為了閱讀順暢起見,我將所有的來源註及其他註釋都放在註腳中,僅保留部分原文,以助了解。
閱讀本報告時,有必要注意幾點。首先,本研究借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方法,以藝術教育為焦點,試圖了解研究對象團體(AIE)所展現的藝術教育現象,形成某種有限之文化詮釋,以及教育啟示,因此讀者宜抱持平常心與平等的態度,避免以「優良教育案例」、「教育評鑑報告」、「國外課程研究」等的心情閱讀本報告。其次,有關哈佛的研究、評論與大眾讀物,不計其數,我的最後文稿是從AIE著手,發現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實況,再回到對AIE藝術教育的理解,但主要是個有關人的研究,而不只是一個機構研究。再者,本研究中不特定人的第三人稱代名詞,採用「他∕她」,以維男女平等之精神。最後,本研究是秉文化人類學解讀文化的精神進行,研究對象與讀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文化距離,但中文世界的讀者仍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仍是地球村的一員,因此我和讀者之所以能透過文字,一起體會書中主人翁的旅程,乃是因為大家都共享著許多相通之處:文化的也好、超越文化的也好。
我在研究之初,以為哈佛終會是聰明、富貴、幸福、成功的總合,結果發現哈佛竟是受苦、負重的代名詞。這讓我意識到,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我對這個時常出現在媒體與工作中的標籤之認識,仍是異常短淺,仍必須倚賴長時間累積的田野資料來重建。我分享此一珍貴的再認識過程,就是希望能呈現:哈佛教育學院的「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不只是一個培養藝術教育碩士的場域,同時是其師生在哈佛的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中脫胎換骨旅程的發生地;田野資料顯示,這個碩士班具體而微地說明哈佛的教育魔法,不但建構了師生的「哈佛人」認同、滋養了師生的「領袖性」,並且,由於三宇宙對主體及其使命的特有淬煉,師生們「做哈佛」(操作哈佛的三宇宙)即如「做世界」(操作各人周圍的世界、改變哈佛以外的世界)之演練。
本書的第1章,先藉描述哈佛的三宇宙,來揭開哈佛魔法的序幕,並說明我的研究架構。第2章,將眼光投向教育學院的當下與過去,討論美國教育界與各大教育學院的浮動本質,點出商議的意義與重要性,並由對照「領袖」的教育、「教育領袖」的教育以及「領袖性」教育三者,來突出「領袖性」教育這個的研究焦點。第3章,主要是介紹四位主要人物之中的三位,描述他∕她們進入哈佛AIE之前的旅程,並以另外三位AIE同學為對照,建構AIE人進入哈佛之前的面貌。第4章,集中介紹第四位旅人,即潔西卡,並將她放在家庭、哈佛與美國藝術教育界的脈絡之中,開始窺見哈佛教育對個人的影響。AIE是四旅人旅程之會合點與共同起點,所以第5章,描述潔西卡創建AIE的歷程,討論此歷程為何可被視為成功的「做哈佛」案例。第6章,解析AIE人核心課的理路與特徵,也是顯示AIE教育是哈佛文化的產物。第7章,旁觀核心課實施的情況,看見旅人的互動以及其間的「領袖性」教育。第8章,觀察核心課外AIE學生與教育學院內其他學生的非正式學習歷程,顯示學生在哈佛的內在旅程,亦屬「做哈佛」過程,突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之情形。第9章,追蹤四位旅人在哈佛會合後以及自哈佛畢業後的旅程,尋找十年間個別發展的情形,除再次顯示「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並進一步顯示,師生畢業前的「做哈佛」與畢業後的「做世界」,兩者間有關聯性。最後一章,整合前面各章的發現,指出AIE不只是從事藝術教育,AIE的教育,是哈佛魔法般教育歷程的一部分,其深層的文化傳承有三:「哈佛人」認同教育、「領袖性」教育,以及由「做哈佛」邁向「做世界」的教育。本章結束前,並簡短討論未來應用此研究之可能。
本書的完成,要特別要感謝書中的幾位關鍵性的旅人,感謝他她們樂於助我完成我的研究,不介意我到處跟班發問、追蹤刺探,即使離開哈佛,仍繼續見面維持聯繫。「願意配合研究」這個條件,表面上看來也許消極,但想想他∕她們是歷經十年而不悔的被研究對象,就必須改變以為他 / 她們是消極的想法,並佩服他∕她們對我的耐心與愛護,或者對一個學術價值並不明確的工作的期許與肯定。
最後,我要感謝充滿藝術教育理想與熱情的AIE人(包括前後兩位主任、兩位行政助理及學生們),教育學院高瞻遠矚的五任院長、行政主管與行政人員,眾多哈佛教育及其他學院的教師與博、碩士生,極富知識服務精神的葛特曼圖書館(Monroe C. Gutman Library)歷任館長與館員,「哈佛零計畫」的多位研究員與工作者,慷慨容許我參與旁聽的教師與學生,照顧國際學生與學者的哈佛大學國際辦公室,關切中西文化發展的燕京學社、燕京圖書館、東亞中心及劍橋新語的各位師長,睿智的哈佛大學秘書長,令人敬佩的AIE外部顧問與演講系列的各位講員,美國藝術教育界多位前輩,關切旅外學人的駐波士頓辦事處官員與工作人員,幫助我在劍橋安頓下來的陳淑花女士,多位給我精闢回饋做我明鏡的學者:(以姓氏筆劃序)王雅各教授、呂金燮教授、李卉老師、黃慶祥教授、潘英海教授、閻鴻中教授,遠流出版公司寬弘的王榮文發行人與堅持品質的編輯團隊,我的助理侯淑鳳小姐、章敏小姐、林華鈴小姐,以及在背後鼓勵我、支持我的家人,您們對我的研究和我本人的幫助,均將永誌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