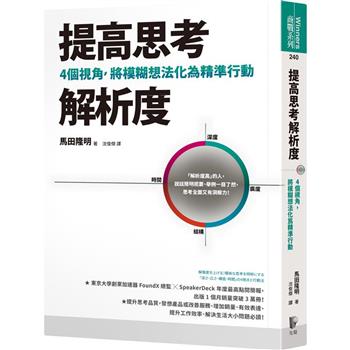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台灣被判歸給中國統治,這塊土地再度易主。
我的祖先來自中國福建省同安縣轄下的一個小村莊,至於是哪個村莊?來台之後我是第幾代?我自己都說不上來。小時候曾經在父親手邊看過祖譜,但事隔幾十年,已不復明確記憶,如今這本祖譜更是不知去向。若真要追查,其實並不困難,但我的親屬觀念和鄉土認同感並不是那麼強烈,實在沒有追問的動機。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給當時的台灣居民(特指由中國移民來的漢人)一段時間,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去留:一、自由離開台灣;二、用外僑(即清國人)的身分繼續居留;三、以日本子民的身分,做為新領地的人民。
當時大部分台灣人選擇了第三種身份,因為他們早已在此地生根,異鄉已經成了故鄉,不願再次離鄉背井,面對更多不可知的命運。我的祖父葉文游就是如此,他向現實妥協,選擇繼續居留在新竹,安心當起順民,也讓後代變成日本人。
但是,還是有些台灣人難以放棄原本的國土與文化認同,不願意當「亡國奴」,因此變賣財產回到中國原鄉。例如我的伯祖、前清秀才葉文樞,原本在新竹開館授課,就因不願接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回中國老家。他的兒子,即我的堂伯葉國煌,後來還在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當教授。一九九二年我到廈門大學訪問時,一時興起,還向該校教授查問此事,證實堂伯確曾在該校任教過。他們問我需不需要替我查詢堂伯子孫的去向,但我並不積極,也就作罷。根據記錄,雖然我的祖父後來曾經回到福建遊歷,拜訪過伯祖,但是,看到民間種種的「慘景」,還是決定回台灣來,即使過的是被殖民的生活。倒是我的伯祖,在祖父殷勤邀請下,跟著祖父又回到新竹來,借居我家,成立私塾,重持教鞭傳授起「漢學」來。當時,新竹許多仕紳家庭的子弟都是伯祖教出來的學生。總之,祖父與伯祖的不同選擇,整體勾勒出日治初期台灣人的一種生存夾縫處境。
我的祖父出身地主階級的仕紳家庭,原本準備參加科舉以求功名,但還來不及應考,在他十三歲時,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了。面對新來的陌生統治者,除了做個悠閒「吃租」的地主仕紳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發揮的空間。
根據祖父留下的文字記錄和長輩描述,他天天吃的是閩南式的菜肴,喝福建茶,過著典型台灣仕紳的日子。我發現,祖父讀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書籍,如鄭板橋的詩集,《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小說《花月痕》等等。總的來說,以詩集為最多,奇怪的是,卻沒看到過有四書五經之類的「嚴肅」書籍。同時,從祖父留下來的筆記,我發現,儘管他也學習日文與英文,還自學代數等等「新」知識,但是,看起來純粹是玩票性質,學得並不是那麼有勁用心。他用毛筆來記載日文與英文字母,以及簡單的代數公式,最令幼小的我覺得不可思議。
祖父雖選擇當日本順民,但他與新竹地區文人成立詩社,吟詩填詞,蒐集古玩,還曾參加報社舉辦的詩作比賽得到全臺冠軍的頭銜,接受台灣總督的召見。這一切顯得,新來的日本統治者,似乎與他的實際生活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日本文化更走不進他的世界,他還是繼續生活在滿清時代的中國文人世界之中,悠遊自在。
我的祖母名叫曾嫦娥,更是始終活在滿清時代裡。她並沒受過教育,看來應該是不識字的,直到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多年了,她過的日子仍跟年輕時代一模一樣:抽吸鴉片、到戲院看「大戲」(歌仔戲)、穿著清代的閩南式衣服、頭上依舊綁著鑲塊綠玉的黑頭巾。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鴉片燒起來後滿屋子的香味,稱得上一種特殊的芳香。我還記得,抽菸桿子的裝飾很精緻,桿頭部分用銀鑲著,桿上配有玉石,桿尾嘴吸的部份,也鑲有金屬片,是銀是銅,還是其他的金屬,我說不上。當時鴉片很貴,據說貴的時候,一兩鴉片就是一兩黃金,但家裡那時候似乎還付得起,因為不只祖母自己抽鴉片,她兩個外甥也跟著在我們家抽。當時,我母親告訴我,他們在家裡當食客之外,每個月我祖母還給零用錢呢。
我那時不懂抽鴉片是壞事,只知道會被送到戒勒所,日治時代雖然官方禁抽,但大戶人家送點錢給警察就可以照抽,光復後情形亦復如是,國民黨政府哪管得了那麼多,你付得起就抽嘛。有一陣子我父親也抽,還好他沒有上癮,我祖母則是上癮了。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長期抽鴉片,她那幾根用來握煙桿的手指頭,都被薰得黃黃的。
祖母去看戲時都是包場的,以前歌仔戲團一來,一演都要至少一個月,京劇團也是如此。譬如,演出三國演義時,總是至少從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或呂布鳳儀亭私會貂蟬,一直演到關公敗走麥城或顯靈,所以大戶人家都是先訂好長期票,安排相同的位置。我祖母看戲時,一定帶著丫環,位置總是前排比較好的座位。據說,她只要看到喜歡的戲子出場,就立刻站起來,把錢往舞台上灑。大家都知道,這是葉家的四奶奶,因為我祖父先後娶了五房妻子,祖母排第四,所以叫四奶奶。而且,也因為祖母皮膚白皙,鼻子挺拔,有白種人的樣子,所以,有人稱她「阿督阿」(台語發音)娘娘。就此,我懷疑祖母那一邊有阿拉伯人的血統。我所以有此懷疑,是因為我與我大妹血液的RH值都是「負」的,而這多見於高加索種人,蒙古利亞種人可以說是甚少甚少的。
或許是受到祖母的影響,父親也喜歡看戲,不過看的是京戲(平劇)。我從小就跟著他去看,也是一看就是連演一兩個月的整齣戲。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跟父親去看戲。說來,那個年代的大戶人家就是這樣過日子的,這是許多與我同世代的台灣人可能不會有的特殊成長經歷吧!這個以演歌仔戲為主的戲院,離我家不遠,座落在靠近城隍廟的長安路上,當時叫新華戲院,後來,歌仔戲沒落,才改演電影,戲院也更名為中央戲院。經過了幾十年的變遷,現在還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新華戲院的設備是相當簡陋的。不過,到現在,我仍依稀記得整個戲院所營造的氣氛,更有一份難以名狀的溫馨懷念。一排排木頭長條椅子,椅背上方釘有一串打洞的板子供觀眾置放茶杯,開場前,觀眾可以點茶,服務員則手提包裹著一層厚帆布的大水壺,在觀眾席中穿梭著,不時添加茶水。不添水時,他則兼賣起瓜子、花生米、蜜餞零食,在我的印象裡,夏天好像也賣著冰棒之類的。所以,整個戲院倒比較像個小市集,地板一直都是散佈著瓜子殼、花生殼、蜜餞核等等,十分髒亂,但是,大家似乎都視若無睹,習以為常。
看戲時,觀眾看到精彩處時就吆喝,要求再唱一遍,或鼓掌叫好,當然,也有人跟著哼唱起來。在看得乏味時,不耐煩的,就與身邊的觀眾聊天,什麼都談。這樣的劇場場景說起來比較像個菜市場,或者說,一種嘉年華會的場景,觀眾跟演員仍然保有著一定的互動空間。這讓我想起俄國哲學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在描繪十六世紀作家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的《賈剛大與潘大魯》(Gargantua et Pantagruel)(台灣譯本稱為《巨人傳》)時所呈現的眾聲喧嘩場景。
來自西方之理性化的現代劇場,講究的是觀眾與演員的絕對隔離,演員是經營整個場域的焦點中心,因此,只有舞台上有燈光、聲音與動作等等,坐在觀眾席上的觀眾,被要求安坐在黑暗裡肅靜地觀賞著舞台上的表演,所有心理的情緒感受必須予以控制,只能在有限的適當時段才可以宣洩,而且是有限度的宣洩。在這樣的情形下,演員與觀眾基本上難有營造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套用英國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這即是所謂「文明化」的現象。我幼年所經驗像菜市場或嘉年華會的劇院場景則不一樣,我們看到的劇院比較像是一個營造人們互動的空間介體。人們到劇場看戲,說來比較像是一個名義或藉口,重要的是,藉著劇情故事、演員的演技與唱工、佈景、觀眾席的安排等等,讓人們有著營造某種程度之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得以陶醉在眾聲喧嘩的感應氛圍之中。這體現的是人類的初始社會常見到的集體亢奮與感應的場景,一切沒有明確的分化,也不需要、不希望是分化的。讓整個情境有意的混沌化,加上有機會產生情緒的共感共應,讓人有機會參與共享歡愉的遊戲,而非只是做壁上觀的冷靜「他者」觀眾。我總感覺到,這是另一種帶著原始野性的「文明化」過程,與理性化的現代劇場場景比起來,並不見得不「文明」,至少比較溫馨,有人情味,不是嗎?
祖母不只抽鴉片,還抽香菸,菸癮還蠻重的,她最常抽的是幸運牌(Lucky Strike)的香煙,不過,有時也抽駱駝牌(Camel)洋菸。我後來到美國讀書時才知道,駱駝牌在美國香菸裡面口味算最重的。其實,在那個時代裡,女人抽菸是少見的,甚至被認為是不正經的。我祖母出身並非紅塵,雖非書香名門,但至少也是小家碧玉,何時染上抽大煙與香菸的習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姑姑(父親的姐姐),還有外祖父的兩個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婆)也有相當大的菸癮,或許,當時,這是富家小姐的時髦表現吧!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那兩個姑婆,倒是當時新竹赫赫有名的兩隻「黑貓」(台語發音,即相當時髦的小姐,男的則稱為「黑狗」)。
當年家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不時有食客,這恐怕是當時之「大戶」人家常有的情形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福州婦女常到家裡來兜售玉石、鐲子、朝鮮人參、中國藥材等等。她來的時候就會叫我一聲「小少爺」,總是在家裡磨蹭一大陣子,甚至晚上會安哄我入睡。諸如此類生活上的小事,如今回想起來,總叫我內心起了一種難以言狀的奇妙感覺,有點古典,像《紅樓夢》中描繪的場景。
祖父在四十四歲那一年的端午節(後來也是詩人節)當天,到十八尖山去作詩,回來吃過一顆大粽子,即因為腦動脈破裂,隨即過世。當時父親才三、四歲,我自然是從沒見過祖父的。祖母則活到五十多歲,晚年眼睛因白內障而致失明,她整天坐在大床上,常常要我過去摸摸抱抱,口中總叫著我這個長孫「金孫」。祖母過世時,我八歲左右,已經有足夠的記憶,至少可以從她的身上,拼湊出祖父母那一代台灣人活在兩種文化夾縫中的一些零碎圖像。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作者:何榮幸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3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人物傳記 |
$ 213 |
社會人文 |
$ 221 |
歷史 |
$ 252 |
台灣人物 |
$ 252 |
中文書 |
$ 252 |
台灣當代人物 |
$ 252 |
社會人物 |
$ 25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葉啟政出生在日治時期末年的新竹,在肅殺的1950年代就讀於學風開放的新竹中學,培養了對於思想、電影的興趣,並不顧家庭反對,以優異的數學成績考入台大哲學系。
大二轉入心理系,跟著楊國樞先生讀書,當時正是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當道的年代,葉啟政一方面受實驗心理學的訓練,另一方面也種下日後出國改唸社會學博士的種子。
葉啟政赴美唸書時,正逢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勃興;回台任教,則碰上台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穩定、但文化認同的問題與自由民主的推動則漸漸浮上檯面的階段。葉啟政以台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建言、興辦雜誌、發表文章、集會結社,更透過教學啟迪年輕的心靈──後來許多學生在1980年代末參與學運、投身媒體、從事政治。
儘管葉啟政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眾聲喧嘩中曾經發出議論,但他最嚮往的還是獨自一人從事思想工作。從台大社會系退休之後,應世新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帶領讀書會,潛心著述。
透過葉啟政學生何榮幸的整理執筆,捕捉了年屆七十的葉啟政回憶過往的點滴,把這個人的生命歷程,鑲嵌進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軌跡。
作者簡介:
葉啟政
1943年生於新竹,新竹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心理學學士、碩士,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社會學博士。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2007年退休,現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何榮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
被撕裂的土地
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
»看全部
作者序
從世俗的眼光來看,我這輩子沒有過什麼豐功偉業,既沒錢、沒名,也沒權,對社會,談不上有任何說得上口的貢獻。這絕不是謙虛客套的話,打從心底,我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若說有什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話,那頂多也只不過曾經是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如此而已。我知道,許多人認為,能夠當上台大教授本身就是成就;但我可不這麼認為,因為能夠在台大當教授的,雖說未必如過江之鯽,但是從創校至今,少說也有上萬人!單就數量來說,就一點也不稀奇,何況,在台大教授中,我也只不過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教書匠,...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前奏 一個不確定島嶼社會的不確定時代
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第二章 走上學術之路
第三章 台大社會系三十年
第四章 書生論政與社會實踐
第五章 知識份子的風骨
前奏 一個不確定島嶼社會的不確定時代
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第二章 走上學術之路
第三章 台大社會系三十年
第四章 書生論政與社會實踐
第五章 知識份子的風骨
商品資料
- 作者: 何榮幸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1 ISBN/ISSN:97895732730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社會人物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