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吉敷探案的最後一部長篇,
卻是開啟所有謎團的第一把金鑰!
「謎樣女人」加納通子令人落淚的傷痛過往終於揭曉!
「柔情鐵漢」吉敷竹史為了至愛與正義,不惜衝撞全世界!
傅博─總導讀
既晴─專文導讀
只要一開啟,無論如何也止不住,
無限的淚水伴隨著無數傷痕,
從過去,流向了未來……
警視廳刑警吉敷竹史的前妻加納通子,帶著女兒雪子住在京都天橋立的一棟老房子裡,這房子,是與她情感深厚的麻衣子姊姊過去的老家。只是,麻衣子死了、母親死了、父親也死了,結婚又離婚,還扯上離奇命案……通子的人生幾乎有一大半都在傷心中度過,而另一半則深受在冰天雪地中,被一名無頭男子追殺的幻影所苦。
為了解開這個謎,她偷偷去尋求心理治療,沒想到在深層催眠中,卻喚醒了一段又一段恐怖的記憶,原來她小時候不但目睹了命案現場,還見到了兇手!
通子回憶起的,其實是三十九年前發生在姬安岳山裡的一宗三屍命案,兇手殘殺了全家人,而丈夫被砍掉的頭至今仍不知去向──眼前,吉敷竹史也正為了這件陳年舊案大傷腦筋,因為他懷疑被判了死刑的嫌犯很可能是冤枉的!
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吉敷和通子竟然不約而同地推開了同一扇禁忌之窗。這扇窗戶之後,到底隱藏著什麼駭人的秘密?……
《淚流不止》是通子揭露一生秘密的最終作。從第一章〈無頭男子的擁抱〉開始敘述通子的童年、少女時代,她的前半生被捲進近代日本的社會問題裡,關於她的婚姻恐懼症、關於她與藤倉兄弟間的恩怨,都將真相大白。《淚流不止》不但是吉敷探案的最後一部長篇,也可視為在島田作家生涯第二個十年裡,承襲了「新.御手洗」的書寫規模,吉敷探案的唯一一部巨篇,亦是吉敷探案的總集成了。
──既晴──
作者簡介:
日本推理小說之神
島田莊司
一九四八年出生於日本廣島縣福山市。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繪畫和音樂造詣均十分深厚。專事推理小說寫作之前從事過多種工作,三十三歲時以首部長篇作品《占星術殺人魔法》嶄露頭角。
島田莊司是當今日本推理文壇的重鎮,在八○年代「社會派」」當道的推理小說界,島田以空前絕後的詭計謎團和充滿說服力的文筆,獨力開拓出無數「本格派」的死忠讀者,當代「本格派」的推理作家無不受其影響,「新本格派」的開創者綾辻行人甚至尊他為師。他的作品曾多次獲獎及進入暢銷排行榜,其中《占星術殺人魔法》更被日本推理作家協會選為二十世紀十大推理小說。
島田的推理小說主要有兩大系列,一個以占星師兼業餘偵探御手洗潔為主角,代表作包括《占星術殺人魔法》、《異邦騎士》、《黑暗坡的食人樹》、《魔神的遊戲》、《眩暈》、《御手洗潔的問候》、《龍臥亭殺人事件》、《龍臥亭幻想》、《斜屋犯罪》、《水晶金字塔》、《異位》、《摩天樓的怪人》與《螺絲人》等;另一個則以刑警吉敷竹史為主角,代表作包括《寢台特急1/60秒障礙》、《出雲傳說7/8殺人》、《北方夕鶴2/3殺人》與《奇想、天慟》等。而《犬坊里美的冒險》則是島田第一次以女性為主角所開創的全新風格作品。除了系列作品外,他的單篇推理作品也同樣擁有極高的成就,例如《被詛咒的木乃伊》即曾入圍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直木賞」。
自一九八一年推出首部長篇小說以來,島田莊司已出版包括長、短篇小說、評論等著作共百餘部。除推理作品外,他對汽車評論、死刑廢除論與日本人論等主題亦有高度興趣。島田現已移居美國洛杉磯,並自二○○○年起不定期出版內容包括小說、評論與隨筆的個人雜誌《島田莊司季刊》。
為表彰島田莊司對推理文學的卓越貢獻,他家鄉的福山文學館已兩度舉辦「島田莊司展」,島田更於二○○八年獲頒第十二屆「日本推理文學大賞」!島田對提攜後進也一向不遺餘力,而為鼓勵華文推理創作,他不但大力支持皇冠主辦「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並於二○○九年九月在台灣舉辦「密室裡的大師──島田莊司的推理世界」特展,堪稱華文推理界有史以來的空前盛事!
譯者簡介:
羊恩媺
一九八一年生,淡江日文系畢業,目前從事編譯工作。
章節試閱
1
天橋立下著雨。隔開外海的沙洲內側,陰暗內海上,雨不斷滴落。
深夜,通子彷彿化身成飛過黑夜的海鷗,清楚想像著雨水在漆黑、寧靜的內海上留下一片漣漪的模樣。雨滴不停地落在古舊窗戶木頭窗櫺的單調聲響,也讓通子的想像天馬行空。
這是場久違的雨,一個人躺在墊被上聽著雨聲,其實非常愜意。身邊的雪子發出鼾聲,行駛在遙遠車道上的汽車輪胎發出「唰──」的聲音,也能清楚聽到。通子索性享受著這樣的氣息。
比往年熱得多的這個夏天,就此畫下句點。報紙和電視上因缺水而起的怨聲載道,也會稍微和緩一些吧!這個念頭也是讓通子心情愉悅的理由之一。
孩子早早上床,通子之後先在廚房清洗東西,並將工作整理到一個段落才就寢,從很久以前就是這樣的生活模式了。睡不著的通子已經聽了好幾個鐘頭的雨聲了,她一個勁地聽著雨聲,身體明明應該很累了,卻還是清醒得不得了。
外頭的雨聲變得更激烈了,夜晚的能量似乎正緩緩地高漲。雨勢增強了,通子甚至聽不到躺在身旁的雪子的鼾聲。夜晚帶著強烈的能量直逼通子而來,她感到恐懼,在棉被底下伸手握住雪子的手。
雨的威力相當驚人。之前每個晚上都熱得讓人無法入睡,今晚卻令人發涼。通子甚至在一瞬間感覺到一股寒氣,不由得將棉被拉至下巴。
剛開始還令她覺得很舒服的雨聲,現在卻漸漸讓她感到痛苦了。涼快變成了寒冷,最後成為寒氣襲來。理應讓人心情平靜的雨天寧靜的風景,卻令通子逐漸覺得悲傷,並不知不覺地煩躁起來。說到底,無論是涼爽的秋天氣息,還是穩定情緒的雨聲,都還是要在安定的心情下,才能好好享受。
在恐懼消失後,通子放開了雪子的手,慢慢地在枕頭上側躺,接著,她心情不佳地重重吐了一口氣,輾轉難眠地又仰躺回來。可是,這一切都讓她覺得毫無意義而無法忍受。一個人待在這樣的城市,為了養育孩子而奮鬥,結果還是什麼意義都沒有。真是無聊至極,明明跟別人接觸、聊天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通子也可以開心地做到。一個人悶著,只讓她看什麼都不順眼,她好想在越益激烈的雨聲中大聲尖叫。
她的下巴開始顫抖了起來,嘴唇也不時地抽搐痙攣。某個溫暖的東西從左眼眼角滑落耳畔,她才知道自己哭了。
煩躁和憤怒的情緒讓她無法忍受,她忍不住把下巴靠在枕頭上,稍微抬起頭,本想就此坐起來,不過沒有這麼做的理由,於是又重重地躺下。結果,竟然出乎意料地發出了啜泣聲,連她自己都嚇了一跳,覺得自己就像變成了別人似的。啜泣越演越烈,最後竟然哭到幾乎喘不過氣來。
外頭的雨聲漸漸變弱了,通子的情緒也隨之稍微鎮靜了一些。
唉,多麼令人討厭的房間呀,多麼令人厭惡的家呀!通子已經知道這個家的秘密了──尤其是二樓。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過這裡還是女主人過去接客的地方。那是戰前的事,通子聽說後來已經改建了,不過這裡發生過那種行為的事實,絕不會因此而消失。她覺得人類的下流,全都滲進這個家的每一根樑柱以及牆壁的表面了。
通子打從心底輕蔑人類的這種膚淺。為什麼無論男女,都會做那種事呢?難道真的不那麼做就活不下去嗎?更何況是為了性行為付費,女人們則是收錢把身體寄放在別人那裡,通子完全無法想像。要是自己也落到不得不跟某個人做這種事的田地,她應該會逼自己愛上那個男人吧!如果不是自己甘願跟隨同進退的男人,通子完全無法理解要如何擁有那樣的關係。就算不這樣,明天的飯就沒著落,換成是自己,還是不會選擇這條路,甚至寧可一死。
只不過,倘若是為了孩子又會如何呢?……要是為了守護孩子,而且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自己會不會那麼做呢?……想到這裡,通子決定不再繼續想下去。
情緒莫名地低落下來,於是通子茫茫然地看著天花板,然而這樣子的停擺,正是她開始向某種誘惑低頭的證據。她決定不去想孩子的事。等她回過神,才發現自己正努力地試圖忘掉躺在身旁的雪子的存在。由於雨聲很大,一度蓋過了雪子的鼾聲,通子才會在今晚不由自主地起了那種慾望。
雨聲持續著,滴滴答答,片刻都沒有停息,外頭充斥著黑暗。我會藏住妳的秘密的──那個聲音在通子的耳畔這麼呢喃──所以不管妳現在想做什麼,都不會有人知道。好了,安心享受吧!
通子一邊無聲地哭泣,一邊把右手放上腹部,維持這個姿勢猶豫了一會兒之後,最終她還是慢慢地撩起睡袍。她輸給了呢喃,雙手放在赤裸的肚子上,有種溫暖的觸感。自己的雙手帶著令她不敢置信的熱度,不僅熱,而且微微顫抖。
下定決心後,通子的右手緩緩地向下爬,鑽過了內褲的鬆緊帶,劇烈的恐懼在同時湧了上來。真的不想這樣做,我不是禽獸,就算不這麼做也能活下去。不要,我不要,我好怕,我不是做得出這種事的女人,所以在此之前,無論獨守空閨的我有多麼寂寞,我都絕對不會這麼做。神啊,這祢應該最清楚吧!是這場雨害的,是這場雨的錯。
通子閉上了眼睛。雖然很想忘記,但是雪子的存在仍舊在她心中的某個角落──無論何時都在,這甚至讓通子覺得很詭異。就不要發出聲音吵醒孩子吧!通子下定了決心,絕對不能發出聲音,因此,她必須咬牙忍耐。
無心,然而一接觸,通子還是即刻按捺不住發出呻吟的渴望。雨聲遠去,快感解放了身體深處,讓通子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忿忿不平的感覺逐漸消失,彷彿不曾出現過一般。短暫的幸福。通子的情緒高漲,呼吸急促,身體起了反應,讓她覺得飄飄然的。甜美的快感漲滿了體內,令她不由得發出了聲音,所以她再次緊緊咬住了嘴唇,同時,恐懼感也直線上升。為了逃避這股感覺,通子緊緊地閉上了眼睛,然而,這個舉動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啊,要來了!馬上就要來了!
無頭男子出現在眼前,通子發出了尖叫。她感到無比後悔!怎麼會這樣?果然!我真是個大笨蛋!明明千萬不能做這種事情的!我明明發過誓了!
當通子從無意識的世界中抽身時,她的視野化為一片白色。那是一個純白的世界,通子在唯一一條軌道上奔跑,空氣冷得要命,周圍毫無人煙。
無頭男子突兀地站在那裡,汩汩鮮血仍舊不斷從頸部的切面噴灑出來。男子穿著白色上衣,鮮紅的血汩汩地流在純白布料上,並且向下朝著腳的方向,在身體前方滑落。然後,他向著通子過來,鮮血也飛濺在白雪上。他將點點血跡留在後頭,直逼通子而來。
通子「哇」地大喊一聲,轉向旁邊,她的雙手都離開了身體,一切也完全恢復了原狀。
回過神來之後,通子發現雨聲依舊。她一邊調整呼吸,一邊刻意花一些時間,等待身體的熱潮退去,然而,她的雙腿卻不停顫抖,令人驚訝的是有時還會痙攣,這顫抖彷彿像在渴求男人似的,讓通子對自己的性慾感到絕望。明明那麼恐怖,自己卻還想要那樣做嗎?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她輾轉反側,試圖把下流的慾望忘卻。想一些開心的吧,快點想起快樂的事吧!今天做了什麼事呢?然而,這個方法一點用都沒有,通子的腦袋完全停止運轉,根本無法思考其他事情。顫抖越發嚴重,痙攣也已經波及全身了,她覺得下半身好重,彷彿不是自己的一樣。
自己身上流著的淫蕩血液再次令通子感到絕望,在這個家裡接客的女人,就是自己的祖母。多麼糟糕的因緣呀!
宛如遭遇到強烈的寒氣一般,通子的下巴不停地發顫,連齒根都無法咬合。痙攣遍及全身,眼淚也不停地流出來。
一面顫抖,一面因恐懼而哭泣的通子作好了心理準備。她咬緊牙關,緊閉雙眼,仰躺著的她再次將指尖往下爬,愛撫。閉著眼睛的她,感受到些微的刺激,接著,激烈的慘叫幾乎要從喉嚨衝上來,害得她都要把嘴唇咬流血了。
不一會兒,通子便感受到麻痺全身的快感。鬱積的能量全都湧了上來,下一瞬間,那個無頭男子出現了,他在雪地上朝著這裡跑過來,已經近在眼前了。
通子驚嚇地轉身,尖叫著全速逃跑。那是在鐵軌上,雪和枕木絆住了腳,讓她沒辦法好好跑。她哭著大喊:救命!救命!誰來救救我!
她不知道男人在想什麼,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追自己。她當然不可能知道,畢竟男人根本沒有表情。他沒有頭,所以也沒有臉,通子自然一點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得見我?他明明沒有眼睛啊!
通子拚了命地奔跑逃命,同時也確實感受到男人逼近自己。第一個證據就是血腥味,其次是男人踢散著雪的腳步聲,還有男人的身體散發出類似熱氣的能量。
通子早已沒了身體渴求的歡愉,只有不斷逼向自己的劇烈恐懼而已。那是不逃走自己就會被殺死、就會遇到慘事的恐懼,在恐懼的追逐下,通子的慾望急速直升。
接著,一堵牆擋住她的去路。無路可逃了,男人就要抓到她了!
恐懼貫穿了通子的身體,全身不停地痙攣顫動,在開始之前的決心已經毫無用武之地了。她不斷地發出慘叫。愉悅、悲傷、恐懼──自己的這些情緒全都被逼到了極限,徹底失控,她已經無法理會身邊有誰了。
通子在牆壁前方停下腳步,一回過頭,頸部的斷面就在眼前,鮮血仍舊持續從紅黑色的肉中央的洞噴灑出來。無頭男子伸出被鮮血弄髒的雙手,猛然抱住了她。劇烈的慘叫聲從她的喉嚨竄出來,恐懼讓她的心七零八落──
鮮血也濺上了通子的身體,並不斷地噴上來,沾污了通子的臉龐、頸項以及衣服。通子染上了無可挽回的髒污,變成了地獄的居民。她發出尖叫,因為恐懼而痙攣,並瘋狂地哭泣,可是,這也都只是暫時的。通子的身體變得像棍子一樣僵硬,也沒了氣息。她完全無法呼吸,動彈不得,也發不出聲音,身體還因為痙攣而抽搐著,這就是死亡。全世界的男人的手壓住了通子的身體,掩住她的口鼻,奮力讓她窒息。她的肩膀和雙腳腳踝都被抓住了,並被用力朝著她的頭、腳兩個方向拉扯。
不能動也不能呼吸的痛苦讓通子不停地流淚,動彈不得的她只有眼淚無言地流出來。這個狀態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通子的視野之中什麼都沒有。就在她快要認清死亡的時候,力氣卻一點一點地回來了。氣息恢復,通子開始可以呼吸,也開始聽得見雨聲了。
她再次哭了起來,這次,是大難不死的喜悅眼淚……
2
通子慢慢地追溯著記憶。久違的自慰行為所帶來的超乎常理的激烈衝擊,徹底敲碎了通子的精神安定,讓過去活生生的情感灑了滿地。
快感的餘韻讓通子失神了一陣子,思緒也飄向了過去,結果一陣令全身寒毛直豎的衝擊突然襲來,讓她沒來由地回想起那個黃昏的事。發生了某件事之後,拚命跑過雪路回家的自己、道路左右積雪的黑色髒污,以及因為結凍而打滑的腳下路面,全都一股腦地回想起來了。還有好不容易抵達家門時,那股打從心底感到放鬆的心情,和眼前漆黑濡濕的木門紋理……
通子等了一會兒,不過現在她想得起來的就只有這些。不對,打開木門走進家裡以後的事,她覺得自己也應該想得起好幾件,只不過在那之前的事,她卻不管怎麼努力都想不起來。從記憶中甦醒的只有跑過雪路以後的事,之前的部分則完完全全無法回溯。
長久以來,通子一直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那樣的男人是怎麼跑到自己的性之中的?打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國三的時候,通子第一次自慰達到了高潮,那名無頭男子也同時出現。通子嚇了一跳,並且害怕得不得了,所以暫時停止了一段時間。和男性發生性行為的時候,通子看不見那個男人,那是只有通子一個人自慰時才會跑出來的幻想。不,說是幻想,也未免太真實了,所以一定是自己的某段隱藏記憶。
就通子的印象,她並不記得自己見過那個男人,所以絕不可能是從什麼親身經歴過的事情衍生而來的,她如此確信。可是,要說是小時候看過的書或是電影,也更不可能,就算是虛構的,通子也不記得自己有過那種經歴。
那股恐懼如假包換,感覺也千真萬確,是書和電影之類的間接體驗絕對不會有的,這點通子可以保證,那百分之百是真的。那種恐怖、那種膽怯、那種害怕被殺死的恐慌,正是實際體驗所帶來的恐懼,是自己確實經歷過的。
如果要說是什麼時候的話,就是通子小時候的事了,這點她很清楚,原因就在於自從她懂事以來,便不曾有過那種經歴。在雪路上拚死命跑回家的那一天,就是通子經歷那件事的日子。可是事情發生在哪裡?又是什麼樣的事件?這些詳細情形,通子卻完全想不起來,只有強烈的印象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
或者,其實不是真正的經歴呢?那搞不好是自己還是個小女孩時,環繞在身邊所有不愉快且無法理解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的綜合效果,說不定並非實際的偶發事件──通子也試著這麼想過。或許是當時所有的不快記憶難分難捨地連結在一起,產生了那種東西,成為反應通子內心的表徵。自己成長的秘密、家族的秘密、父親的秘密,以及母親和麻衣子的秘密,這些秘密大概也都有所關聯。
這麼一想,通子便突然感覺到重重的不安,因為這些秘密對她來說是無論如何都想逃避、最黏膩下流的黑暗面。
然而,她已經下定決心要好好回想起來了,她想要了結這一切。以前她只是一股腦地逃避,但光是逃避,事情並不會因此結束。她不希望自己一輩子都是個有缺陷的人。自己已經長大,也成為母親,稍微強悍一點了,就算有什麼東西突然迸出來,她也已經可以覺得自己不會有問題了。
可是陰影太深,超乎想像地嚴重,光是「坐在椅子上努力回想一個鐘頭」這樣的心理準備完全沒效,必須專心一志地探尋過去才行。通子的過去裡,有太多事情被刻意隱瞞了,連誰生了她,又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通子從來都不知道。
隱瞞事實的是通子的雙親,尤其是父親,可是他們有什麼必要這麼做呢?自己的根在哪裡?小時候一直相信是自己母親的人究竟是誰?還有父親又是來自什麼地方的人?從事什麼工作?等到通子長大成人,生活穩定下來之後回顧,卻發現相關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倘若想要知道,除了自己尋找之外別無他法。
要靠自己尋找,首先就要先揭開雙親那一代的秘密,這需要實際走訪調查,於是通子也這麼做了。為了找出被藏匿的自己,得先找出藏匿的理由,為此,她必須追溯到雙親、乃至於祖父母那一代才行。
這是困難的工作,不過也大致完成了,只不過還有一個不清楚的地方。就算打探出自己的過去,所得到的這把禁忌之鑰,仍無法解開棲息在自己的性當中的那名無頭男子之謎。
一如所料,自己的根源相當令人吃驚,甚至已經遠遠超乎她的想像。隨著事情的全貌赤裸裸地攤在眼前,事件背後的怨念彷彿也如影隨形,令通子雙腳發顫。她也清楚了解雙親隱瞞的理由,然而,在那段令人驚訝的過去當中,她還是沒有發現和性中那幅影像相關的東西。只有無頭男子的事情仍懸在那裡,直到現在都揮之不去。
這陣子,通子一直不斷重複地挑戰過去,雖然還沒有完全補齊,可是就像前面說的,短時間的堅持是行不通的,必須積極讓自己投入才可以。這讓通子非常抗拒,不過,當她下定決心為了搜尋記憶而自慰之後,每一次劇烈的恐懼都會帶來少許收穫。
這天晚上也有,而且這次的收穫很大。挖掘記憶就要這樣龜速前進才有效。在外頭的雨聲當作背景下,自己見了無頭男子之後的行動,也隨著大量的兒時記憶一起迅速在腦海裡甦醒。要說明通子當時的情形,只有將周遭的狀況一段一段仔細地描寫如下。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個黃昏,通子其實平安無事。明明發生了那種事,她卻毫髮無傷,連擦傷都沒有,然而,她卻有著自己赫然發現手掌沾了血的記憶……
1
天橋立下著雨。隔開外海的沙洲內側,陰暗內海上,雨不斷滴落。
深夜,通子彷彿化身成飛過黑夜的海鷗,清楚想像著雨水在漆黑、寧靜的內海上留下一片漣漪的模樣。雨滴不停地落在古舊窗戶木頭窗櫺的單調聲響,也讓通子的想像天馬行空。
這是場久違的雨,一個人躺在墊被上聽著雨聲,其實非常愜意。身邊的雪子發出鼾聲,行駛在遙遠車道上的汽車輪胎發出「唰──」的聲音,也能清楚聽到。通子索性享受著這樣的氣息。
比往年熱得多的這個夏天,就此畫下句點。報紙和電視上因缺水而起的怨聲載道,也會稍微和緩一些吧!這個念頭也是讓通子心情...
推薦序
【導讀】
島田莊司的冤獄現場
推理作家、評論家◎既晴
Ⅰ
本作《淚流不止》發表於一九九九年,是吉敷竹史系列繼《飛鳥的玻璃鞋》(一九九一)以來相隔八年的力作。
九○年代的島田莊司,累積了第一個十年的寫作經驗,嘗試過獵奇、幽默、懸疑、青春等各種題材,此時終於聚焦於本格派與社會派的創作上,原本涇渭分明的派別,在他的筆下卻能齊肩並進、相兼相成。
首先,在本格路線上,「新本格」浪潮席捲日本推理文壇,島田也乘勢讓御手洗潔復活,展開「新.御手洗」的實驗性的探索,挑戰大格局的敘事、製造大翻轉的詭計,並對不同屬性的文類進行大融合。這樣的創作實驗,不僅使「新.御手洗」的篇幅拉長為一般長篇的三、四倍長,成為巨篇推理,也讓其他本格推理作家起而傚尤,蔚為風潮。
在社會派路線上,源自《奇想、天慟》(一九八九)的主題,島田持續地關注日本近代的「冤獄問題」,完成《秋好事件》(一九九四)與《三浦和義事件》(一九九七)兩部罪案紀實作品,及《死刑基因》(一九九八)的死刑、冤獄的論述文集,贊成廢止死刑、倡言陪審團制度的鮮明立場,使他從一位小說家變成一位社會議論家。
然而,在這段時間裡,吉敷探案出現了一個長達八年的大斷層,與八○年代一年動輒兩、三部的活躍盛況完全不同。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因為島田專心致力於本格派巨篇推理創作,另一方面,則是相對於御手洗系列而言,島田在吉敷系列的寫作上遭遇了瓶頸。
當然,所有的類型小說都可能陷入模式化的瓶頸,因為類型原本就是一種模式。密室殺人、孤島謀殺、時刻表詭計、貪污黑幕,都是十分常見的模式,讀者們一方面喜歡這些模式,容易進入故事,期待得到新的解法;一方面,卻也終究會對一而再、再而三的相同模式感到厭煩。如何調配模式與創意之間的比例,就成為推理作家的重要課題了。
基本上,島田莊司並不是一個喜歡重複模式的作家。他確實喜歡寫分屍案,也確實喜歡在小說裡闡述人類論、社會論、文明論……但,這應該算是他的風格、他的偏好,而不是故事模式。他比較喜歡在本格推理這個框架下進行各種不同探索,儘可能地玩出新花樣,倘若新的花樣在某種模式下玩不下去了,他就會另起爐灶,重新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御手洗潔從《占星術殺人魔法》(一九八一)的占星術師,變成《黑暗坡的食人樹》(一九九○)的私家偵探,再搖身為《魔神的遊戲》(二○○二)的大學教授──偵探身份一再改變、故事舞台一再擴增,都是為了因應島田創作路線的調整。
相對地,吉敷竹史卻不是這樣的角色。吉敷從頭到尾都是搜查一課的刑警,儘管可以趁休假期間往北海道、北陸跑,順便解決案件,卻沒辦法像十津川省三跑到法國、韓國去處理別國的新幹線時刻表詭計,他甚至未曾插手過國際犯罪事件。
因此,就在御手洗探案不斷延展其故事格局、實現島田創作探索欲望的同時,先天上活動範圍、案件類型受限的吉敷探案,跟不上他大題材、大架構的追尋腳步,也不願屈就一直辦小案、解小謎,最後只好擱置一旁了。這樣的困境,一直到了島田在冤獄問題的研究上有所斬獲,吉敷竹史終於才有了一個夠龐大的容器得以書寫,也才完成這部《淚流不止》。
Ⅱ
吉敷的前妻加納通子,首次登場於《北方夕鶴2/3殺人》(一九八五),這也是吉敷首次提及自己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當時,兩人已經離婚五年。加納通子突然與吉敷聯繫,卻避談關於自己的近況,立即掛了電話,吉敷深覺有異,經過多方追查,才得知通子成了一樁謀殺案的嫌疑犯。
在這部作品中,除了島田首次在吉敷探案裡運用大型詭計、甚受推理迷推崇以外,吉敷冒險犯難、殫心竭力地設法解救通子,表現出鐵漢柔情的一面,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通子在洗清罪嫌後不知去向,對自己的心路歷程也隻字未提。吉敷只知道自己破了不可思議的命案,卻無法理解通子迴避曖昧、莫名所以的言行。
到了《羽衣傳說的回憶》(一九九○),前往銀座的吉敷信步走進小巷裡的畫廊,偶然見到了通子的金雕作品「羽衣傳說」,於是開始追查通子的下落。此書並非島田典型的解謎作品,反而更像是追憶往日愛戀的抒情小說,雖有謎團但小巧,純屬點綴。
故事裡花了許多篇幅,描述吉敷與通子邂逅、相戀、結婚、在刑警職業與家庭生活的不平衡下忍耐,最後因彼此認知差距太大,終至離異的過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子忽然哭鬧、忽然平靜,猶如雙重人格般的怪異行徑外,還有她有極端的婚姻恐懼症──她認為,自己只要一結婚就會死──羽衣仙女的傳說,也影射了通子無法結婚的心結。吉敷雖然再次與通子重逢,卻未能將她留在身邊。
接下來的《飛鳥的玻璃鞋》,敘述兩人分居兩地、藕斷絲連的互動。吉敷依然深愛通子,但一直感覺到通子口頭上說要常聯絡、實際上卻越漸疏遠的冷淡態度。他終於無法壓抑自己的情緒,離開東京前往通子經營的金雕店,才發現通子早已歇業。吉敷察覺通子又開始欺騙她,設法找到通子,但通子卻逃避吉敷的質問,不願告訴他實情、也不願見面,最後在電話裡吵了一架,關係再次決裂。
而在石岡和己首次擔綱偵探角色的《龍臥亭殺人事件》(一九九六)裡,出現了一對長期住在貝繁村龍臥亭旅館的母女,阿通與小雪。事實上,阿通即是加納通子。故事裡提到了她的體質十分敏感,有鬼壓床的睡眠症,也提到了她的丈夫從事回家時間不固定的工作──不過,吉敷的名字並未出現在故事裡。從時間順序來看,通子就是在金雕店歇業後來到貝繁村的。
終於來到《淚流不止》,這是通子揭露一生秘密的最終作。從第一章〈無頭男子的擁抱〉開始敘述通子的童年、少女時代,如同島田在自作後記所提到的,她的前半生被捲進近代日本的社會問題裡,關於她的婚姻恐懼症、關於她與藤倉兄弟間的恩怨,都將真相大白。
其後,又經過多年歲月,《龍臥亭幻想》(二○○七)讓貝繁村的眾人重新聚首,再加上御手洗潔與吉敷竹史兩大名探連袂出現,可說是島田筆下陣容最豪華的一作。在故事裡,吉敷終於與女兒小雪會面,一家團圓。
Ⅲ
針對冤獄問題,島田在九○年代做過深入研究,而被公認為吉敷系列最高傑作的《奇想、天慟》,可說是他言及冤獄問題的濫觴。
不過,《淚流不止》所談的冤獄問題,與《奇想、天慟》並不相同。島田撰寫《奇想、天慟》時,他的創作焦點放在如何將幻想型的本格派謎團與寫實型的社會派動機予以融合,至於冤獄問題,則是行川老人悲慘遭遇的其中一件,戰爭對人類的殘酷影響,才是島田的書寫重點。附帶一提,戰爭一直是島田關心的問題,類似的取材,還出現在後來的〈天使的名字〉(二○○○)、《俄羅斯幽靈軍艦之謎》(二○○一)與《利比達寓言》(二○○七)裡。
一九九三年初,島田在《Friday》雜誌撰文連載《世紀末日本紀行》,這是一部漫談環境污染、現代人精神病等社會問題,充滿現實性驚悚的報導文學,後於一九九四年集結成書。當中一篇文章談及死刑,島田申請死刑犯處決後的遺體、處決設備等照片,遭到法務部拒絕,原因是法務部不希望公開死刑的執行細節,以避免引起國民的反對輿論;後來,島田為求更了解死刑問題,寄了問卷給多名死刑犯,並開始與死刑犯們通信。
其中一名死刑犯秋好英明,與島田展開長期聯絡。秋好於一九七六年涉嫌殺害妻子一家人,並在一九八五年初審判處死刑。隔年,島田將此一案件寫成罪案紀實作品《秋好事件》及非系列小說《昇天之男》(一九九四),其後更將兩人往返的通信內容,整理出版為《與死刑犯.秋好英明的書信集》(一九九六)。
後來,島田參與了更多冤罪救濟活動,也接觸到了熱心調查俗稱「洛城疑雲」一案的相關人士。本案是一名商人三浦和義在洛杉磯旅行期間,涉嫌殺害妻子並詐領保險金,因為是在國外犯案,且涉及日美兩國不同的法律制度,因此備受各界關注,知名度非常高。島田獲得了相關人士的協助,取得許多寶貴情報,將本案始末寫成罪案紀實作品《三浦和義事件》。
在兩部罪案紀實作品中,島田均未主張嫌疑犯無罪,而是陳列多方線索、提供各種可能的推論讓讀者自行思考。其實,島田之所以調查這兩樁可能是冤獄的案件,更主要的目的是針貶日本社會的弊病,提出建言。
而多年來這些對冤獄問題的思索與累積,正是撰寫《淚流不止》的關鍵素材。
《淚流不止》的核心案件恩田案,是一名燒烤店老闆恩田幸吉,涉嫌殺害木材業者河合民夫一家三口、並將河合民夫砍頭藏匿的謀殺案。恩田不但無端被警察逮捕、審訊、拷問、栽贓,還因為教育程度不高、不了解法律而聽信律師的建議認罪,在嫌疑裡越陷越深,翻供而不可得。其妻繁子經過了幾十年的奔走努力,年華老去,依舊無法證明恩田的清白。
吉敷偶然遇見繁子,不但發現案發地點就在通子的故鄉盛岡,負責偵辦恩田一案的刑警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峯脇。這樣的巧合,吸引著吉敷開始進行調查,而他的遭遇也如同恩田一樣,想要遺忘事件的關係人、隨時間而不斷流失的證據,都讓吉敷在案件裡越陷越深。除了找到真憑實據,別無出路。
「恩田案」的構想,極可能是取材自一九五○年在靜岡縣磐田郡二俣町某戶一家四口的滅門血案「二俣事件」。當時警方認定一名年僅十八歲的青年須藤滿雄涉有重嫌,主導偵查的刑警紅林麻雄,立即以竊盜案先將須藤逮捕,再脅迫他坦承罪行、偽造物證及偵訊報告。地方法院判決須藤死刑。
然而,有一名刑警山崎兵八卻對調查結果提出質疑,並向報社舉發紅林麻雄拷問嫌犯、偽造證據。山崎此舉,被警方視為叛徒,反遭警方以偽證罪逮捕,檢方聲稱山崎精神異常,罹患妄想症,因此判以不起訴處分。而警方則在事後將山崎免職,山崎自宅甚至遭不明人士縱火。
另一方面,經過高等法院審理,確認警方所宣稱的證據全屬捏造,須藤無罪開釋。而專以拷問取供、入人於罪的刑警紅林,後來也被證實與數起重大冤罪案有關,紅林因而辭去警職,不久因腦溢血去世。
然而,在《淚流不止》以後至今,島田莊司全心投入自己所定義的「二十一世紀本格」路線之創作,至於吉敷探案,僅發表過一部短篇集《發光的鶴》(二○○六)而已,顯示近年來,這個系列已不再是島田莊司的創作重點了。因此,《淚流不止》不但是吉敷探案的最後一部長篇,也可視為在島田作家生涯第二個十年裡,承襲了「新.御手洗」的書寫規模,吉敷探案的唯一一部巨篇,亦是吉敷探案的總集成了。
【導讀】
島田莊司的冤獄現場
推理作家、評論家◎既晴
Ⅰ
本作《淚流不止》發表於一九九九年,是吉敷竹史系列繼《飛鳥的玻璃鞋》(一九九一)以來相隔八年的力作。
九○年代的島田莊司,累積了第一個十年的寫作經驗,嘗試過獵奇、幽默、懸疑、青春等各種題材,此時終於聚焦於本格派與社會派的創作上,原本涇渭分明的派別,在他的筆下卻能齊肩並進、相兼相成。
首先,在本格路線上,「新本格」浪潮席捲日本推理文壇,島田也乘勢讓御手洗潔復活,展開「新.御手洗」的實驗性的探索,挑戰大格局的敘事、製造大翻轉的詭計,並對不同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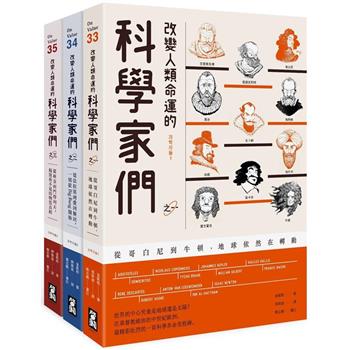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我開始看推理小說是肇因於松本清張,然而會成為推理小說迷則是受到島田莊司作品的吸引。推理小說界有所謂分成「本格派」和「社會派」兩大流派,不管本格與社會兩派之間的異同或紛擾為何,島田莊司是少數可以作品橫跨兩派的作者,而且他並不是社會本格派那種混合流派,他的作品中,本格與社會兩種流派涇渭分明。 身為社會派支持者的我,自然會傾倒在島田莊司的社會派風格的作品下。島田大師的社會派推理作品,多半是圍繞在刑警吉敷竹史的辦案與故事上頭。 我先列出島田莊司作品中屬於刑警吉敷系列的: 1984年:寢台特急1/60秒障礙 1984年:出雲傳説7/8殺人 1985年:北方夕鶴2/3殺人 1989年:奇想、天慟 1990年:羽衣傳說的回憶 1991年:飛鳥的玻璃鞋 1991年:ら抜き言葉殺人事件(字謎殺人事件) 1999年:涙流れるままに(淚\流不止) 這一系列的作品中有幾個特點: 一、 旅情:警探為了辦案而東奔西跑,順便將筆調帶到當地的人文風景或名勝古蹟,像本書所提到的便有盛岡(通子的故鄉)、北海道(通子沉淪的地方)。 二、 冤獄:從『奇想、天慟』開始,島田莊司就透過刑警吉敷去探查一個個冤獄。 三、 跨越時代:書中的命案都不單純,其動機與起因都可以回溯到一二十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藉此寫出濃濃的懷舊,或是對老舊陳窠的批判。 四、 犯罪心理:島田莊司的這一系列作品,並不會完全走本格路線,作者會鉅細靡遺地描述犯罪者與被害者之間的關係、人脈和心理層面,同時連辦案的主角刑警吉敷也有更詳細的內心戲的陳述。 五、 堅持本格:作者一定會安排驚天動地的命案,或是匪夷所思的命案現場,不然至少也會結合旅安排情與當地的神鬼怪談作結合,來鋪陳推理的氣氛與解謎過程。 喜歡吉敷竹史系列小說的讀者,應該都知道吉敷竹史有個前妻加納通子,她在『北方夕鶴2/3殺人』、『飛鳥的玻璃鞋』、『羽衣傳說的回憶』三本書中出現,只是都不是主角,加納通子在『飛鳥的玻璃鞋』與丈夫吉敷疏遠,在『北方夕鶴2/3殺人』一書中已經和吉敷離婚,且牽扯在北海道的一宗殺人事件中,在『羽衣傳說的回憶』的加納通子似乎已經看破紅塵,在天橋立隱居。 在本書還沒出版之前,每次讀到島田莊司描寫通子時,總是會感覺到沒頭沒腦的,只知道主角竹史有個前妻,竹史跟通子的關係還有他們兩個人隱約卻強烈的感情,也只知道他們相遇的過去,也隱約曉得通子心中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但是呢,島田莊司始終不說出來,坦白講,我覺得十分機車,因為實在是歹戲拖棚。 這本《淚\流不止》正是百分之百加納通子的故事,完整的交待了她一生的故事與遭遇,當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我原諒了島田莊司的「機車」。 這本可以稱得上是推理小說中的「大河」巨作,完整地透過通子極為悲情苦命的一生,清楚地帶出許\多時代宿命,更讓人驚艷的是,男性的作者竟然可以將女性的心裡以及深層的恐懼與慾望,描寫的如此絲絲入扣,其細膩程度一點也不輸給女性作家。 禁忌和慾望是貫穿通子一生宿命的兩大原罪,在通子與其他角色的敗德行為中,作者將時代宿命如男尊女卑的偏見、昭和初年的普遍性司法冤獄問題、早年不公不義的社會階層對立……等等,融入女主角通子的一生。 本書的篇幅相當大,中文版還分成上下兩冊,高達八百多頁的內容卻不會讓人讀起來有太大的負擔,前前後後稱得上是高潮迭起,故事的線條分成兩路,一條是陳述加納通子的過去,另外一條,是竹史私自調查一件多年的冤獄真相。兩條事件,最後發現環環相扣然而糾纏在一起。 我認為這本書應該是島田莊司到目前為止最棒的作品,因為本書並沒有異想天開的劇情與驚人的手法,島田的作品中,由於太強調本格,所以會有那種「把火車吹到天空的白色巨人」、「半夜會自動走來走去的鐵甲武士」、「屍體被拆解成五塊分別被放置在不同鐵路的車廂中」或「突然在箱根湖上出現的俄羅斯戰艦」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怪誕情節,或許\有讀者會喜歡這類天馬行空的橋段,但我個人卻極度不喜愛。然而本書島田莊司完全不安排這類怪談,讓整個故事的現實感、大河小說的架構性和時代感十分充分,讀起來行雲流水,不用沈溺在怪異的解謎上頭。 反倒是,《淚\流不止》的文學性相對地提高不少,通子的一生完全合乎了「失落-尋找-救贖」的典型,剪不斷理還亂的禁忌、敗德和不幸遭遇,讀起來相當有衝擊感,一個女子為了贖罪所付出的不堪代價,以及她承擔了家族宿命所遭致的苦難和折磨,找不到出口的那股苦悶怨氣,無一不牽動著讀者的情緒,當然,通子的故事與結局,得留待讀者自己去挖掘與品嚐。只是無須會擔心本書是否會太過於灰暗負面,只要有顆成熟的心,非但不會陷入所謂的悲劇情結,反而可以從通子一步步地去解開自己宿命與原罪的過程,而去思索到救贖的正面價值。 當然,一定有讀者會認為本書過於血淋淋,或怎麼把通子這個女性描寫得如此不堪,也許\也有人會認為劇情與通子身世故事太過於撒狗血,但是,若回歸「小說」的本質,只要好看,何須計較那麼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