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法國至西班牙,直線距離約八百三十公里,不遠不近,可快可慢,全看你想怎麼走。
古時行旅,山高水深,苦行僧一路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一天或能走上二、三十公里,那也花上個把月的工夫;現代的旅人大可以搭乘噴射客機,僅需一個半小時多一點就到達目的地;倘若行李家當太多,選擇自己駕車,一路走高速公路,偶爾停下來上個洗手間,打個盹,吃個三明治,十六個小時或許到得了。
可是在這個夏天眼看就要過去,秋天快到家門外的時節,我和約柏卻花了二十幾天才從巴黎抵達巴塞隆納。請不要誤會,我們並未效法古人一步一腳印,咱倆才沒有那麼堅定的決心,更沒那體力。我們採取「折衷方案」,出發前擬好大致的計畫,但容許甚且歡迎偶然的變化,兩人從都市啟程,先搭火車,繼而租車下鄉,在鄉間居遊,爾後回到城市,就這樣朝著旅程的終點,隨興行去。
我們除非必要,否則不走寬闊方便又相對省時的高速公路,寧可走省道、鄉道,有時還刻意從GPS衛星導航顯示的幾條路線中,選擇那最遠又最曲折的一條。我們不想趕時間,情願慢慢地遊,自在從容,晃晃悠悠,只因為對我們而言,旅行的意義並不單在於「抵達」,總覺得旅行一如人生,一味悶著頭往前奔,怕只會錯過路旁的風景,而這些看似說不出名堂、平凡無奇的風景,在一定程度上卻也是目的地。當我們回到安居的家園,驀然回首,說不定會發現,這些不經意走過的風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其實都已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了記憶,銘刻上我們的心版。
於是我們自巴黎出發,上了路,在南法阿列日省(Ariège)一個名叫聖蘇珊妮(Sainte Suzanne)的小村附近居遊,再穿越庇里牛斯山,先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內陸一個GPS也找不到的僻靜角落,體會農莊生活,最後到達地中海畔的巴塞隆納。
◇ 巴黎的一天
7:30 早晨的棍子麵包
半夢半醒間,聽見金屬刮過石板路面哐噹哐噹的聲音,伸手到床頭櫃上摸索,找到了錶,果如所料,七點半不到,每天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垃圾車便會來到聖潔曼德沛這間小公寓的樓下。這些清潔隊員恐怕是巴黎最守時的公務員吧,我朦朧地想著,翻了個身,又瞇了一會兒,還是起床了,終究捨不得錯過轉眼就過的巴黎居遊時光。
當我反身拉上背後那扇沉重的木頭大門時,已經八點了。陽光仍稀薄,路面殘留著午夜一場雨留下的濕意,積水的青石灰黑發亮。外頭有點涼,我將頸間的薄圍巾拉得更緊一點,抬頭看天,雲影淡淡,氣象報告說,今天天氣將轉晴,是乾爽的好日子。
窄窄的馬路沒有多少車輛,人行道上唯我踽踽獨行,時候還早,通常要到午後,才會見到三五遊客從塞納河畔信步走到不到一百公尺外的這條老街,好奇地張望兩眼,發覺路旁連一間餐廳、咖啡店也沒有,就只有兩排建於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住宅樓房悄然而立,顯然不是個多麼有「名堂」的普通街道。不小心走進小街的遊人於是當機立斷,要嘛快步通過,要不毅然轉身離開,讓老街繼續默然。然而,卻是這個「沒有名堂」,這份沉默與不起眼,讓我們這一回再度租居此處。
我經過一扇扇堂皇的雕花木門,行至小街盡頭,先往左拐,朝南,走幾步便右轉,往西到大馬路,然後朝著聖潔曼大道走去,和大部分人同一個方向,只是別人多半提著公事箱或筆電包,行色匆匆,大概是要趕著搭地鐵上班、辦事去;我呢,斜揹著小布袋,裡頭裝著零錢包和手帕,慢吞吞地走著。我只是個居遊者,既不必上班,也無事待辦,出門,純粹想買條新鮮的麵包而己。只因為,居遊者在巴黎的一天,怎能不以剛出爐的棍子麵包為開始呢?
走進「梅森凱瑟」(La Maison Kayser),門邊櫃台的年輕店員恰與我眼神交會,我向她點點頭,說聲Bon jour便往後走。我們幾次來巴黎居遊都住在這一帶,這家麵包店我幾乎天天上門光顧,都熟門熟路了。甜點、蛋糕在前面的櫃台,各式麵包在後面架上,這會兒已有四、五人在排隊。店裡更往後是烤爐,師傅正烤出新的一批麵包,一室溫暖馥郁的香氣,聞著更教人覺得餓了。
輪到我時,按照法蘭西禮節,和長相俏麗的黑膚女店員互道早安,未待人家開口詢問,便伸手朝她左後方的架子一指,說:「 Une Baguette Monge, s'il vous plaît. 一根棍子麵包,麻煩您。」這家巴黎名店烘製的法式條形麵包不只一種,有粗有細,有長有短,不管是哪種,統統用天然酵母所發酵的麵糰烤成,趁熱掰開來,一股麥香撲鼻,裡頭的氣孔大小不一。我最喜歡兩頭尖尖、以創始店所在地址為名的Monge。
女郎自架上取了根麵包,用一張紙包起來,遞給我。買賣雙方又是行禮為儀,互道Bonne Journée(祝有美好一天),這才結束每天的例行公事。我一手握著外皮烤成金黃亮褐的麵包,掌心感覺到它的溫熱,一邊跨出店門,沿著原路走回在巴黎的家,不時舉起麵包,打量那露在紙外面的尖角,蠢蠢欲動,還來不及轉彎踅進小街,終究忍不住,伸出手,咔嗞一聲掰下最上頭一小截,送入口中,好脆好香啊。
16:30 午后的漫步
小睡一個小時又精神百倍,出門轉悠去。出了小街,向右轉,一路走到連結西堤島和聖路易島的聖路易橋上,駐足聽街頭藝人演奏薩克斯風,吹的是什麼曲目呢?毫不令人意外,皮雅芙的〈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是也,雖是聽到快「爛」的曲目,但這位小夥子吹得還可以。曲畢,給他鼓鼓掌,順便在他跟前的草帽裡擺了兩歐元,算小小的鼓勵。兩人舉步再往前,登上了聖路易島,排隊買兩球Bertillon冰淇淋,記得多年以前第一次來巴黎時,要吃這家的冰淇淋可不容易,得在老店門前大排長龍好一會兒。如今島上到處都有店家代售Bertillon冰淇淋,有些無須久候便可買到,不過我還是習慣到老店排隊,一來那兒口味選擇多,二來懷舊一番。唉,別罵我,我知道我太濫情了。
回程的路上,拐到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雖然這家傳奇性的英文書店創辦人畢區女士(Sylvia Beach)已離世近半個世紀,店面早就不在一九二○年代的原址,昔日在此高談闊論的文人也已成歷史雲煙,書店本身更因盛名之故,多少已是旅遊景點,但是我每回來到巴黎,仍習慣來這兒逛逛,買上幾本書。我支持它堅守以人文書籍為銷售重點的作風,欣賞它依舊在樓上的書架間擺一張床,提供熱愛文學的明日作家住宿的傳統,也喜愛書店外牆黑板上以正楷字母塗寫的幾句話──「在我看來,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比隔壁鄰居更真實,更怪的事情是,在我尚未出生以前,杜斯妥也夫斯基便已在一本叫做《白癡》的書中,寫下我的人生故事。」三言兩語,道出多少書蟲的心聲。
21:30 走至夜深
在巴黎,我們做的最多的事情,除了吃東西、喝咖啡,就是走路了,更精確的講,是漫步──漫無目的地散步。
巴黎的確是個適合走路的城市,不論你已經造訪過多少次,不論你是走在通衢大道、偏街後巷,看到的是深夜還亮著的櫥窗裡最新款的時裝或兩百年前的銀燭台,是尋常人家窗台上的春花,抑或是建築物外牆上促狹幽默的卡通壁畫,巴黎,永遠給人小小的驚喜。當然,還有塞納河,那見證了巴黎千年的滄桑與輝煌、無與倫比的塞納河!旅人來到巴黎,或許可以不爬鐵塔,不參觀羅浮宮,卻該去塞納河邊走走,至少看兩眼河畔風光。只因為,沒有塞納河,就沒有兩千年前那名叫Lutèce的漁村聚落,也就沒有現在的巴黎。
我們一如無數位懷抱著仰慕的心情而來遊客,難以抵擋塞納河的萬種風情。晚飯後,只要天氣不太壞,即便是小雨綿綿,夫妻倆也一定出門,不見得走遠,一定先到河畔走走。
仲夏天黑得晚,九點多了,彩霞餘光猶在天際,在只能徒步通行的「藝術橋」(Pont des Arts)上,年輕男女或躺或坐或憑欄而立,有的輕拂吉他,低聲吟唱;有的指天畫地,高談闊論;也有的儷影雙雙,依偎在一起,耳鬢廝磨,眼中沒有別人,只有你我。
凡此種種,都只能教已步入中年的我感嘆,青春果真無敵。就像海明威那膾炙人口的名言:「如果你有幸在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麼今後不論你到哪裡,巴黎都會一輩子跟著你,因為巴黎是流動的饗宴。」青春正盛時就能來到巴黎,在這美好的夏夜,坐擁塞納河無邊的風情,是多麼幸運的事!
初秋,夜色昏暗,河堤上蒙著薄霜,有人遛著狗經過,耐心地等著狗兒找到某根樹幹,撒泡尿,人和狗再繼續結伴前行。我們一轉身,看到一個孤獨的身影坐在河邊,天涼好個秋,他是在等人嗎?
我們就這樣隨興所至,在巴黎的街道上走著走著,走至夜深,走至人影逐漸稀落,而我們的腳也乏了,再怎麼捨不得巴黎的夜,也不能不暫時與之道別。Bonne nuit, Paris.à demain!晚安,巴黎,明天見!
◇ 南法的一天
7:00 一隻叫噹噹的狗
一下樓,就看到噹噹正背對著屋子,趴坐在落地窗外,頭擱在兩條前腿上。牠大概是聽到我的腳步聲,抬起頭,驀地爬起來,轉過身,拚命搖尾巴,兩隻大眼無辜地看著我,充滿著期盼。我打開落地窗,讓牠進屋來,也不管牠懂不懂,用中文對狗兒說:「乖乖等我梳洗,馬上帶你出門散步去哦。」噹噹想要到山坡頂上去遛達,可是半途有隻兇狗會從樹籬後面惡聲惡氣地吠叫示威,噹噹要人去給牠壯膽呢。
從我們來到聖蘇珊妮村外的拉芭堤小屋的頭一天起,就跟噹噹這隻熱情的犭更犬交上朋友。記得我們剛到不久,來不及卸下行李,牠就來串門子,悶聲不吭,只是搖著尾巴,好像在歡迎這兩個陌生人。
噹噹雖然人來熟,但教養良好,謹守分寸,你不替牠開門,喚牠一聲,牠可不會不告而入。牠儼如公關大使,代表房東帶著我們認識環境,先領我們到草坡,向正在除草的鄰居打聲招呼,又帶我們爬下小山凹,去看汀妮克在菜田澆水、除蟲。噹噹和名叫Scotch的貓咪維持友善但不算熱絡的關係,貓犬相敬如賓,哦,該說是相安無事。
不過牠好像不大喜歡住在自家後院櫟樹下的雞家族。遛狗途中,噹噹原本小跑步走在我的前方,同我保持數公尺距離,不時回頭張望我有沒有跟上。過了一會兒,牠看到前面有公雞、母雞帶著小雞穿越碎石車道,人家明明沒招惹牠,牠卻一個箭步衝上去,狺狺而吠,嚇得雞群落荒而逃,鑽進矮樹叢後避風頭。我樂了,邊笑邊喊噹噹回來,因為,嗯,不好意思,我有恐鳥症,雞雖不會飛,但畢竟也是禽類,我一併畏而遠之。噹噹這下子可替我出了一口氣了,這隻聰明的狗兒說不定感覺到我莫名的懼怕,刻意替我趕雞哩。
遛狗回家,約柏已坐在樓下餐桌旁,正查看著攤在桌上的地圖,瓦斯爐上的摩卡壺散發著咖啡香。我熱了一盅牛奶,在果盤裡挑了幾顆汀妮克自己種的蜜李,從小屋外的棚架上摘了一小串葡萄,又切了幾片昨天在鄰鎮麵包房買來的鄉村麵包。這些加上綿羊乳酪和蜂蜜,還有一壺咖啡,就是健康又天然的早餐。
正在喝第二杯咖啡時,聽見山谷傳來啵啵好幾響,有點悶悶的,平日難得吠上兩聲的噹噹在院子裡跟著叫個不停。我過了半晌才恍然大悟,遠方傳來的是獵槍聲。秋天來了,打獵的季節開始了。
14:00 午后,在拉芭堤
午餐才吃沒兩口,約柏就說覺得越來越不舒服,頭暈,還有點反胃,像是偏頭痛快發作了。我聽了可急了,隨便把盤裡的食物掃進胃裡,餐後附送的咖啡也不要了,催著約柏趕緊回拉芭堤,還好餐廳所在的小鎮離聖蘇珊妮村不遠,約柏只要再撐十分鐘就能好好休息。我慶幸自己提議來小鎮吃午飯,而沒有留在車程較長的密若波瓦用餐,更高興我們要回去的是有住家的感覺的拉芭堤,而不是美則美矣卻始終只是「旅館」的一個房間。人在身心脆弱的時候,往往需要多一點「家」的溫暖。
回到小屋,伺候約柏在樓上臥房躺下,給他倒了一大杯溫水,拿了頭痛藥和胃乳片擱在床頭,還準備了一只水桶放在床邊,他萬一想吐就不必急著喊我。希望他只是前一天在公路上奔馳太久累到了,多躺個一會兒就沒事。
下樓來,午后陽光明媚,照在餐桌上汀妮克昨天送來的那一大盆番茄上,紅豔豔的,好美。我心思一動,決定來做番茄醬汁,不必先試嚐就知道這些番茄肯定可口,我可是親眼見到汀妮克在菜園裡施肥、澆水、除草,這樣悉心種植出來的農產品,怎麼可能不好吃呢?
我用刀在番茄底部劃了十字紋,燒了一鍋熱水燙番茄,以便剝除那煮不爛的皮膜,接著把番茄一切為二,割去蒂,擠去籽,切成塊,一股腦扔進鍋裡,加蒜瓣和月桂葉,淋一點橄欖油,就讓這一鍋在爐上慢慢地熬。等它熬成醬汁,拌上麵條,撒上幾片栽植在大門外花盆裡的羅勒,我們就有簡單美味的晚餐可吃了。
20:00 夜色悠長
居遊期間,不想費太多工夫埋在廚房裡,晚餐只簡單做了兩道菜。前菜是無花果佐風乾火腿和藍紋乳酪,這道菜用不著炊煮,做來不費時間,也花不了多少力氣,無花果摘自樹頭,火腿和乳酪購自農民市集,都是本地土產。主菜的材料也幾乎全是就地取材,切了半小顆洋蔥,炒了一小條也是汀妮克在自家菜園種的茄子,加上下午熬的番茄醬汁和十來顆黑橄欖,拌義式spaghetti。要不是麵條來自義大利,橄欖油和黑橄欖來自庇里牛斯山另一邊,這道家常麵食的「碳里程」簡直趨近於零。
鄉間的暮色來得比較緩慢,也許是因為沒有水泥叢林遮掩夕陽,黃昏顯得格外悠長。我把晚餐開在露台上,一瓶酒,兩道菜,慢慢上,夫婦倆不願打破徐緩的節奏,一頓晚餐從日光璀璨、山風微暖,吃到斜陽西照、彩霞滿天。當我收拾桌子,準備回廚房燒水泡茶時,霞光已逝,天色寶藍,微涼似水,看看錶,才九點半,秋天果然來了。
再過半個多小時,也許一個小時,夜空將佈滿星斗,我要捻熄小屋的燈光,披上薄外套,佇立在星空下,讓約柏指點著天上星辰,告訴我北極星在哪裡,天狼星又是哪一顆。
然後,我們會回到溫暖的小屋,闔上窗簾,打開一盞燈,或許從CD架上取下一片Miles Davis。約柏將在悠揚的樂聲中,伏案寫他的攝影筆記,我呢,繼續看那本一直沒讀完的書。更可能,我們什麼音樂也不放,索性聆聽山風婆娑拂過樹梢,蟲子在草叢中唧唧鳴叫。偶爾傳來三兩聲狗吠,間或有低沉的嗡嗡聲,悶悶的,也許是遠方的火車,又說不定是汽車經過山下的公路。
隱隱約約的聲響,更顯得拉芭堤小屋的寂靜。我們在南法的一天即將結束,夜,漸漸深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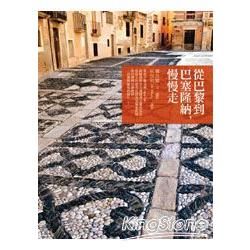 |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 作者:韓良憶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4-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89 |
旅遊 |
$ 299 |
歐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
步調慢一點,美好風景多一點。
巴黎->南法聖蘇珊妮小村->穿越庇里牛斯山->北西班牙->巴塞隆納
從棍子麵包到tapas bar,
從稀薄的日光到鑲著金邊的烏雲,
從莎士比亞書店到高第秘密花園,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一場無與倫比的旅行……
巴黎很美,巴塞隆納很美,
但更美的或許是……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過的風景。
第一站,巴黎,住在聖潔曼德沛區的小公寓,
離左岸很近,離一場流動的饗宴也很近。
散步,逛市集,在盧森堡公園曬太陽,抹茶蛋糕的下午茶時光。
一路向南,陽光漸暖,步調更緩,
在租居的乳黃色小屋,用南法的心情,踏實南法的一天,
跟著狗兒晃到陌生的草坡,用當地摘採的食材做晚餐,直到心滿意足。
翻過庇里牛斯山,就是北西班牙,
永恆的蒙布朗小城,永恆的中世紀風情,
黑米飯、香腸拼白豆、番茄大蒜麵包,則是只屬於這裡的永恆香氣。
終於,來到巴塞隆納,這裡不僅彌漫著想像力,
也彌漫著人們的好心情和好食慾,
巴塞隆納的三餐怎麼吃?
早餐吃兩頓,中餐要澎湃,晚餐的tapas bar一攤吃過一攤……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830公里不遠不近,快一點一個小時,慢一點十幾個小時,或許就能到了。
但良憶和約柏兩個人,卻花了二十多天,邊走邊住,邊住邊玩,邊玩邊吃。
在這本書中,她不僅要分享實用的居遊資訊、獨家的散步路線和道地的美食地圖,還有那些在緩慢的步調之下,不經意遇見的驚喜與感動!
作者簡介:
【生活美食家】韓良憶
喜歡簡單的生活,認為生活中只要有好吃的食物、好聽的音樂、好看的書和電影,平日能在家附近散散步,一年至少去旅行一次,就很好了。尤其吃和音樂是最容易取得的樂趣,一日不能缺。
覺得吃東西時影響自己最多的是心情和食物的本身,再來就是一起吃的人。一看到就想買的CD,有Van Morrison、John Coltrane和Miles Davis。喜歡的作家很多,最喜愛又敬佩的「偶像」是已故的美國飲食文學作家M.F.K.,只要買得到的書,全部都收集了。
覺得幸福就是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但是對人生仍懷有夢想。總覺得,沒有夢的人生,不值得活的。
正因為如此,目前定居荷蘭,雲遊四海,依舊繼續享受著美食和旅遊的生活。
【最佳攝影師】侯約柏Job Honig
生於荷蘭古城豪達(Gouda),從小愛攝影,長大學電腦科學,目前任職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擔任研究員。《我在法國西南,有間小屋》、《我的托斯卡尼度假屋》、《在鬱金香之國小住》和《地址:威尼斯》,是他和妻子韓良憶共同的居遊記憶。
章節試閱
前言
◇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法國至西班牙,直線距離約八百三十公里,不遠不近,可快可慢,全看你想怎麼走。
古時行旅,山高水深,苦行僧一路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一天或能走上二、三十公里,那也花上個把月的工夫;現代的旅人大可以搭乘噴射客機,僅需一個半小時多一點就到達目的地;倘若行李家當太多,選擇自己駕車,一路走高速公路,偶爾停下來上個洗手間,打個盹,吃個三明治,十六個小時或許到得了。
可是在這個夏天眼看就要過去,秋天快到家門外的時節,我和約柏卻花了二十幾天才從巴黎抵達巴塞隆納。請不要誤...
◇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法國至西班牙,直線距離約八百三十公里,不遠不近,可快可慢,全看你想怎麼走。
古時行旅,山高水深,苦行僧一路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一天或能走上二、三十公里,那也花上個把月的工夫;現代的旅人大可以搭乘噴射客機,僅需一個半小時多一點就到達目的地;倘若行李家當太多,選擇自己駕車,一路走高速公路,偶爾停下來上個洗手間,打個盹,吃個三明治,十六個小時或許到得了。
可是在這個夏天眼看就要過去,秋天快到家門外的時節,我和約柏卻花了二十幾天才從巴黎抵達巴塞隆納。請不要誤...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韓良憶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4-02 ISBN/ISSN:978957332891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旅遊> 歐洲
圖書評論 - 評分:
|
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 相關搜尋
出發!去北歐:《【插圖版】芬蘭旅行日常指南》+《曬冰島 UNLOCK ICELAND》星星都美麗.都柏林的A-Z︰大使偕行的愛爾蘭文化慢旅
開始在法國自助旅行(全新第八版)
倫敦旅行家(全新第五版)
羅馬、梵蒂岡深度之旅(最新版)
巴黎啊,你為什麼叫巴黎:法國食尚作家里維帶你漫步巴黎,從塞納河、香榭大道、羅浮宮,到西堤島、蒙馬特、拱廊街、杜勒麗花園,以法式幽默訴說40個你所知道與不知道的巴黎
柏林.法蘭克福.科隆.萊茵河
慕尼黑.新天鵝堡.羅曼蒂克大道.海德堡.斯圖加特
西班牙:馬德里.巴塞隆納.安達魯西亞
驚豔奧地利:歐遊女王洪繡巒帶你品味45處不可錯過的名勝,美饌美酒、古蹟文化、雪景溫泉,領略歐陸四季之美、節慶、工藝與人文氣息【暢銷增訂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