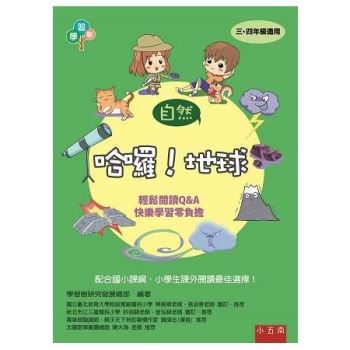哪怕死了六次
我也會六度愛上你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超人氣作家 三田誠 ✿
魔法 × 青春 × 謊言,挑戰腦力極限的推理神作!
✿超人氣繪師 カオミン 繪製封面✿
她以死亡為食,
那是將死者的情感、境遇,化成自身記憶的過程。
在這一刻,兩者的靈魂有如合而為一,
再也分不清你我——
✦✧✦
這是在作夢嗎?
如果是的話,又是誰的夢呢?
作這種惡夢的人是我?還是——
小學時,薊拓海是檻杖久理在班上唯一的朋友。久理總是自稱「魔女」,同學們都視她為異類。某一天,兩人在一所曾經發生虐殺事件的廢棄工廠探險時,拓海親眼目睹久理的「特異功能」──她舔拭現場殘留的鮮血,接著便能產生某種感應,經歷死者生前的情緒,並重現死亡的情景。這讓拓海感到恐懼,他從此不再與久理往來。
上高中後,拓海對轉學生安藝瑤香產生好感,但安藝卻對魔法莫名執著,在試探出拓海與「魔女」的過去後,便成天纏著他獲取更多資訊。招架不住的拓海,只能帶安藝去那座荒廢的工廠來滿足她的好奇心。
沒想到,安藝卻做出與過往久理類似的行為,而後陷入昏迷。更離奇的是,從醫院醒來後的她,個性徹底改變,甚至連過去的記憶都不復存。為了找回那個總是掛著盈盈笑容的女孩,拓海清楚,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於是,他再次找上那個曾經「吞食死亡」的魔女──
✦✧✦
✿每個人的死亡,都因不同的經歷✿
✿而有專屬於自己的味道……✿
失去存在意義的少女,她的死——是芬芳的花蜜味。
在祭典中溺斃的孩子,她的死——是清甜的石榴味。
那被狗群咬殺的男人,他的死——是苦澀的鐵鏽味。
魔女輕輕嗅聞,尋覓著自己的下一餐,
以死亡為食的魔女,只想任由自己的內心,填滿亡者的色彩……
作者簡介:
作者介紹
三田誠 さんだ まこと
作家,現居兵庫縣神戶市。作品以魔術為主題進行創作,類型涵蓋遊戲小說、漫畫等,內容包含奇幻、推理等題材。作品《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於2019年動畫化,並改編成舞臺劇。《魔法人力派遣公司》已連載超過二十冊,於2007年動畫化。由桌上遊戲改編而成的《赤龍戰役》也作為原型,於2015年動畫化。此外還有《艾梅洛閣下II世的冒險》、《魔法使的新娘 詩篇.108 魔術師之青》、《創神與喪神的召喚之戰》、《十字架X王之證》、《加略》(暫譯)、《魔女推理II:一定有天會回想起那是愛情》(暫譯)等多部著作。
譯者介紹
洪于琇
政治大學日文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日文筆譯,平日以書、戲劇、電影餵養心靈。
很喜歡自己的文字能夠幫助到別人的感覺。
近期譯有《究極夢辭典》、《小桌花小瓶花 隨手花藝設計》、《在這樣的雨天》等書。
個人網頁:wishduo.wixsite.com/showscollections
譯者簡介:
洪于琇
政治大學日文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日文筆譯,平日以書、戲劇、電影餵養心靈。
很喜歡自己的文字能夠幫助到別人的感覺。
近期譯有《究極夢辭典》、《小桌花小瓶花 隨手花藝設計》、《在這樣的雨天》等書。
個人網頁:wishduo.wixsite.com/showscollections
章節試閱
三
那一天,我一起床就有不好的預感。
我遠遠望著因為作弊未遂,或是其他什麼事而遭到狠狠責罰的宇治垣,之後每節下課都在學校四處徘徊,唉聲嘆氣。
關鍵發生在午休時間。
我帶著憂鬱的心情前往餐廳時,一名認識的女孩朝我揮手。
「拓海同學——這邊坐。」
對方甚至還指名道姓。
雖然逃走很簡單,但若無視這麼赤裸裸的呼喚不免引人側目,為了避免那種情形,我忍住嘆息,盡可能地散發出「無可奈何」的波長坐到了女孩對面。
「妳該不會還沒放棄問那傢伙的事吧?」
「嗯。」
女孩點點頭,承認得很乾脆。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種態度,溝通高手的人生之於我是未知的世界。
這間餐廳最有名的咖哩飯發出誘人的香氣,女孩露出微笑,一臉幸福無比地發表感想:
「你不覺得這間學生餐廳的咖哩,比外面的爛餐廳還好吃嗎?」
「聽說那個煮飯阿姨以前是開餐廳的,退休後改成來學校的學生餐廳工作。咖哩飯是她以前的招牌,只有這道菜是用她自己帶過來的食譜。」
「原來如此。」
女孩點頭,同時又像是辣到似地一面「哈、哈、哈」地吹著氣一面喝水。
「所以你也點了?」
「沒錯。」
我的餐盤上也是咖哩。
我朝嘴裡塞了一大口飯,想盡可能縮短同桌的時間。
「來,給你。」
女孩從桌邊的調味料中拿起起司粉遞了過來。
這裡的調味料在餐廳阿姨的堅持下,有基本的蕗蕎、福神漬、橄欖、茗荷與醋漬蔬菜,比較特別的甚至還有紫蘇、白蘿蔔和鳳梨丁,種類豐富,應有盡有,而起司粉正中我的喜好。
該說她很機靈嗎?
畢竟我連家人的口味喜好都不太清楚了。
正當我因為在意想不到之處被攻下一城,內心默默沉吟時,安藝又發出一道重擊:
「還有這個。」
「唔。」
我二度悶哼。
安藝高舉的手上,一把我熟悉的銀色工具閃耀著光芒。
「那是……!」
我忍不住抬高音量,接著環顧四周一圈。
雖然有些人瞬間往我們這邊看了一眼,但似乎很快就失去了興趣。我稍微深呼吸,緩緩開口,以免再引起更多注意。
「妳為什麼會……」
「這果然是拓海同學的東西吧?」
安藝放在桌上的,是一把專門用來理髮的剪刀。
「我問妳為什麼會拿著它。」
「原因大概有三個。」
女孩重新拿起湯匙道。
「推理一,你今天早上從朝會前就一臉悶悶不樂對吧?如果是上課後才這樣的話便會有很多種可能,但若是上課前心情不好,那應該就是家裡的事。所以,我猜或許跟你姊姊有關。」
安藝趁著空檔舀了一大匙咖哩飯塞進嘴裡,急急忙忙喝了口水後繼續道:
「不過,從之前在你家剪頭髮時的互動來看,姊姊雖然霸道,卻也有自己的原則,加上你的臉色看起來有些自責,感覺更像是你自己本人搞砸了什麼事而不是姊姊的問題。」
「妳從別人的臉色也看出太多東西了吧?」
「不要因為自己無法辨別別人的情緒,就小看其他人的能力好嗎……人類正是因為有這種社交能力,才得以發展出社會。」
老實說,安藝說得沒錯。
由於人類是藉由群體發揮能力的生物,所以像我這種缺乏社交能力的人就是異端,沒有容身之處。不過,卻產生要過度發展反而才能創造容身之處這樣的矛盾。
就在我越想越遠時,安藝抬起手指。
「推理二,既然如此,就是你在學校掉了什麼東西……這是很有可能的推測,對吧?當然,也有可能只是你單純心情不好而已,但你不是那種會在一件事情上糾結太久的人,如果錯不在己,感覺很快就會看開了。」
「妳真的……很會看人。」
「嗯……因為對象是你啊。」
我已經沒有力氣一一回應她捉弄的話語。
我和這個人是真的合不來。如果我是剪刀,安藝就是石頭,都是她單方面的攻擊。
「最後,推理三。今天早上宇治垣同學因為作弊受到嚴懲對吧?具體來說是被剃了平頭,班上鬧成一團。」
「……?」
不會吧?
「宇治垣同學還真大膽,想從教職員辦公室摸走考卷答案背下來,結果被抓到,老師把他拖到教室裡時,好像剛好看到你的剪刀就拿來用。雖然是古早時代的做法,但這間學校還是經常以剪頭髮做為學生的懲罰對吧?所以,老師也只會覺得,一定是有人撿到了別的老師的剪刀放到了桌上……」
我茫然地抬頭望著滔滔不絕的安藝。
「也就是說,你一臉不開心是因為弄丟了剪刀。之所以會來學生餐廳,也是因為從早上就一直在找剪刀,沒時間做便當。你平常都是自己帶便當對吧?」
「……妳觀察得真仔細。」
我只能勉強擠出這句話。平常我做便當時,會連老姊的中餐一起準備。老姊今天大概是把昨晚的剩菜都丟到鍋子裡做成炒飯吃吧。
「雖然之後就沒必要說了,但我推理到這邊後就去了一趟教職員辦公室,發現被老師放在桌上的剪刀。我跟老師說那應該是你的東西,會負責拿來還給你。最後,我猜你應該會在餐廳就過來了。如何,很簡單吧?」
「妳是什麼名偵探嗎?」
「呵呵呵,怎麼樣啊?你需要這把剪刀嗎?」
女孩晃了晃手中的剪刀,頭髮也開心地左右搖擺。她口中哼著曲調,絲毫沒有要隱藏自己的得意,她的人生一定非常開心吧?
「……需要。」
我嘆了口氣,嚴肅地收下剪刀。
這下欠了安藝一筆人情。
唉,沒辦法。只要還是社會裡的一分子,就必須遵守「有借有還」的原則。學校這種地方是一個幾年內都不會有改變的迷你社會,若是不講道義,很可能馬上就會遭到所有人排擠。
我收下剪刀,盡可能以平靜的口氣問道:
「妳為什麼那麼好奇『那傢伙』的事?」
跟之前一樣的話題,一樣的短暫停頓。
安藝像是想表達咖哩很辣似地緊閉雙眼。
接著,她小聲道:
「……我之前說過,我想當魔女對吧?」
儘管那就像是還沒脫離愛作夢的年紀般說的胡言亂語,不切實際,卻包含了我無法等閒視之的詞彙。
「其實,本來想當魔女的人是我的好朋友。」
女孩繼續:
「她是個對魔女、神祕學這類東西非常了解的女生。雖然我對這些事幾乎一竅不通,她還是每天都跟我聊得興高采烈。而我只要在一旁聽著,看著她天南地北說話的樣子就很開心了。」
人與人之間也有這樣的相處模式吧。
僅僅只是看著對方變化多端的表情或是靜靜坐在一旁便已心滿意足,簡單而靜好。
「後來呢?」
「她在我們國中畢業前死了。」
我的呼吸瞬間一滯。
「是車禍。」
安藝的話語落在桌面上。
餐廳裡越來越吵雜,人聲鼎沸的程度與城市相比毫不遜色。而在這個吵吵嚷嚷的空間中,彷彿只有安藝周圍的空氣凍結起來。
「那時候,我剛好為了小事和她在吵架,所以聽到她車禍的消息時,身上還帶著要跟她和好的信。」
嘶啞的聲音傳了過來。
「搬來這裡後,我想起她跟我說過久城魔女以死亡為食的故事。她說,魔女的後裔檻杖家至今依然存在,持續吞噬人類的死亡,吃下死亡的魔女可以說出那個人死亡時的事。」
那大概類似某種都市傳說吧。
故事長年在某些靈異故事迷之間口耳相傳、不斷變調。久理是活生生的人,加上處於現代這個網路社會,就算安藝的好朋友只是剛好聽到那類的傳聞也不稀奇。
「所以,我試著去了檻杖家幾次……那麼大的一座宅邸,或許要說是檻杖府比較合適……但那裡始終大門深鎖,令人難以接近。」
啊啊,應該也是吧。
久理家那間在山坡上的宅邸簡直像座牢籠,就生人勿近而言,我還沒見過有哪個地方執行得如此徹底。就連我以前也只進去過三次而已。
「妳想讓久理吃下妳朋友的死亡嗎?那傢伙不是潮來巫女耶 。」
「你和她熟到直接叫她的名字嗎?」
安藝的眼神閃閃發亮,彷彿在說「你終於露餡了」。
安藝說的沒錯,所以與其懊悔,我選擇了另一個行動。
「妖怪工廠。」
「什麼?」
啊,沒辦法了,既然都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再往前一步反而比較容易做個了斷。欠了剪刀這筆債,如果不算清楚的話,很難和安藝斷得乾乾淨淨。
「抱歉,我沒辦法讓妳見到久理,因為我回來後也一直沒和她見面。不過……妳一開始的意思,是希望我告訴妳和那傢伙之前發生過的事吧?我和她曾經去過一座在村子外面的妖怪工廠,方便的話,我們週末可以一起過去。」
「耶!」
安藝彈了個響亮的手指,那副笑容對我而言果然太過炫目。
我挪開視線,自暴自棄地將咖哩飯大口大口塞進嘴裡,連同萬千思緒一同咬碎。
四
那座廢墟位於河川分流前的上游沿岸。
那是座只有水泥塗裝、冷冰冰的建築。一方面因為老舊,一方面因為原先的水泥似乎本就粗糙,使得這裡四處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裂痕,彷彿輕輕一戳就會立刻塌陷。
無論是攀附在牆壁四周的金屬管線,抑或是逃生梯都佈滿了鏽斑,特別是後者,感覺連我的體重都承受不了,一副隨時會碎掉的模樣,所以我盡可能地保持距離。
「妖怪工廠這個名字太貼切了。」
安藝發出驚嘆,我也忍不住點頭贊同。
因為,與其說感覺這座工廠會出現妖怪,不如說它本身已經死亡,看起來就像一隻工廠妖怪。
時值黃昏,從巨大裂縫照射進來的光線將工廠內染上一層紅色,更加強化了那種印象……那麼,走在化為妖怪的工廠裡面,我和安藝又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聽說,這裡以前是製藥工廠。」
我確認口袋裡的手電筒後走在前方,回答安藝。
工廠裡似乎還殘留著微微的異臭,但我無法判斷那是事實還是只是心理作用。
這座工廠建設之初相關的法規還非常寬鬆,排放了各式各樣在現代屬於違法的藥物廢水出去。雖然我之前說自己對鄉土史沒興趣,但這件事在課堂上被當做公害問題來討論,就算是我也記得一些概要。
幾年後,在國內社會運動的推波助瀾下,工廠結束了它的任務。據說本來應該要徹底拆除才對,但鄉下的善後工作也很隨便,導致工廠最後成為廢墟留了下來。
那些沾染在牆壁上,看起來既像蝴蝶也像雲朵……偶爾又像人形的汙痕,應該就是那些藥品造成的痕跡吧。
走在佈滿無數碎石的地上,安藝再度開口:
「你和檻杖同學在這裡做了什麼?出事了嗎?」
「嗯嗯,出事了。」
我回答。
此刻,我的表情一定很不耐煩吧。
「有黑道在這裡處理屍體。」
走在我身後的安藝,腳步聲瞬間亂了節奏。
「畢竟,這裡是遭人遺忘的鄉下工廠,於是似乎就成了利用藥劑毀屍滅跡的絕佳地點。不過,對他們也對我們而言不幸的是,久理剛好嗅出了那份死亡。之後,找到證據後警察就出面了。」
當時,黑道還找上門,久理的父親為了保護久理也插手進來,雙方爆發衝突鬧得天翻地覆。但這段往事跟我們現在聊的主題沒有直接關連,只能可惜地略過。
如今,我也已經認不出來倒在地上的哪一個鐵桶實際上曾經融化過人類。
此時,安藝吐出一句極輕的呢喃:
「……久城魔女果然是真的。」
「如果妳信的話吧……」
「可是你信,對吧?」
安藝笑盈盈地反問。
我一時間啞口無言,安藝繼續道:
「拓海同學,你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超能力存在嗎?」
我目不轉睛地望著眼前的女孩。
幾秒後,我在「妳在說什麼蠢話?」與「我很認真聽妳說喔」之間取了中間值,抬了抬下巴示意她說下去。
「久城魔女好像就是被視為那種存在。」
安藝道。
她曲起手指靠在形狀姣好的唇瓣下方,稍微思考了一下後繼續:
「感覺可能跟你剛剛的故事很類似。雖然鄉下人遇事會去神社求神問卜,是很常見的事。但在久城這片土地上,魔女的神諭深受信賴這件事,至今仍保有影響。」
我似乎能夠理解。
也就是說自古以來,日本各地的居民就一直有痛苦時,求神拜佛這個共同的行為吧。當努力與其他累積的一切都不管用時,人們便會想依賴那一類的超自然現象。
「所以,妳想說久城魔女是超能力者嗎?」
「嗯。」
我的反問應該充滿了戲謔的口氣,安藝卻直直點頭。
「雖然我這是聽人家說來的,但比起超能力者,共感人這個詞應該更為貼切。」
「共感人?」
「嗯……」
安藝眼神微微看向半空後繼續道:
「這也是之前聽人家講的。據說,曾經有國家機關之類的機構利用一種叫做ESP卡的工具進行了很正式的超能力實驗。這種卡片的背面繪有特殊符號,實驗便是藉由受試者是否說出正確的符號,來檢定他們的透視能力。」
「喔……」
話題漸漸轉到一個很可疑的方向。
不過,熱衷於脫離日常的神祕學,也算是一種很典型學生會做的事。以前,也有遇見的學者逼我聽一些類似共感體質的話題。
我隨意附和後,安藝接著說:
「據說,在這項實驗中有些受試者的結果自成一格。」
「意思是受試者中有人有超能力?」
「這有點複雜……可能要看你對超能力的定義是什麼。」
出現了「定義」這個詞。
我想起了在髒兮兮的黑板上,寫下歪七扭八公式和數字的年邁數學老師,但為了讓對話繼續下去,我拋出一個空泛的問題:
「什麼意思?」
「實驗中的確有些受試者的成績特別突出,不過,前提是必須滿足某些特定條件。如果他們身邊沒有知道卡片答案的工作人員,準確率就跟隨機猜測差不多。」
「呃……意思是他們造假嗎?」
「應該說,那些受試者的能力跟研究者預估的不同。」
安藝豎起食指說。
「這些人並沒有透視力能看見未知的卡片內容,不過,卻有能力察覺沒有說出口的情報。他們能夠下意識地從那些知道卡片答案的人身上細微的視線游移、口氣差異、臉部表情肌肉,甚至是全身肌肉的緊繃度推測出圖案。」
(……原來如此。)
我懂了。
關鍵在於這些受試者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吧,即使知道卡片內容也不明白自己為何會知道,所以也才沒發現他們是從在場工作人員的身上取得答案。
「有時候電視劇裡,不是會出現那種沒有實際生活感的房子嗎?觀眾會有這種感覺也不是因為有什麼決定性的證據,而是從灰塵堆積的方式、咖啡杯擺放的位置等等,隱隱約約感受到吧?共感人就是這種感覺的延伸。」
「……」
我答不出話。
那種共感能力,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吧?
而那個「多多少少的程度」根據不同人之間的適性,一定有著天壤之別。有的人即使眼前看到身受重傷的患者眉頭也不會動一下,有的人則只是在電話中,聽到對方手指被紙割到發出的呻吟便難以忍受。
世上那些善於看穿他人謊言,或是巧妙利用心理誘導技術控制他人的專家,或許也是應用了這種能力吧。
「有些人認為既然如此,在同一種能力的延伸上,或許也有像久城魔女這樣,能夠聽見死者的聲音的人。如果屋子裡會存在生活感,那麼出現屍體的現場,留下無法抹滅的東西也很正常吧?」
「我覺得這種說法太過牽強也想太多了。」
「哈哈哈,果然嗎?或許吧。」
安藝聽了我的反駁也不計較,爽朗地笑道。
反而是我,雖然否定了她的說法,心裡卻莫名感到不自在。
(……死者的聲音。)
過去,久理沒有說自己見到了亡靈。雖然我只在小學時見過一次,但她是透過一種很特別的行為吃下死亡。
「怎麼了?」
「我們剛好走到附近了,就是牆邊汙痕很深的那裡。」
不知道是因為本來有藥劑槽的關係,還是後來把這裡當做自己地盤的黑道分子幹的好事,那一帶的水泥牆和地面上留下了特別深刻的汙痕。
「久理舔了那塊地方。」
「……這樣啊。」
安藝瞬間瞪大了眼睛後點點頭道。
「如果那裡有藥物殘留的話,很危險呢。」
「她真的差點死了。」
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當時我一個不留神,久理已經伸出舌頭舔起牆壁。緊接著,她便臉色發白、捧著肚子倒了下去。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真的是因為藥物的關係,或許就不只是昏倒那麼簡單了。
三
那一天,我一起床就有不好的預感。
我遠遠望著因為作弊未遂,或是其他什麼事而遭到狠狠責罰的宇治垣,之後每節下課都在學校四處徘徊,唉聲嘆氣。
關鍵發生在午休時間。
我帶著憂鬱的心情前往餐廳時,一名認識的女孩朝我揮手。
「拓海同學——這邊坐。」
對方甚至還指名道姓。
雖然逃走很簡單,但若無視這麼赤裸裸的呼喚不免引人側目,為了避免那種情形,我忍住嘆息,盡可能地散發出「無可奈何」的波長坐到了女孩對面。
「妳該不會還沒放棄問那傢伙的事吧?」
「嗯。」
女孩點點頭,承認得很乾脆。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