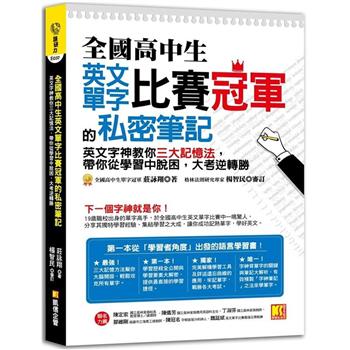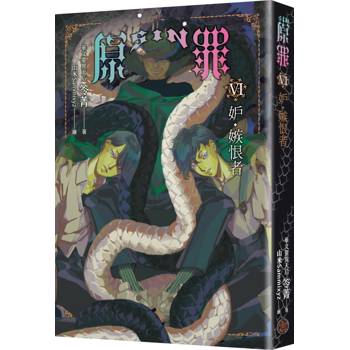新詩30家 李敏勇 (一九四七│) 詩對李敏勇而言,是向歷史告解的自白書,也是面對自我的備忘錄。他的心是熱的,筆是冷的,他的筆是光束集中的雷射小刃、乃至「顫慄的舌尖」,寒光所至,希望能拉朽摧枯、去腐除鏽,深入「意義的黑夜」,盡到文學的社會功用。
歷史與未來是他筆尖經常探觸的主題,前者的陰暗面常化身為不斷啃噬後人的野獸和噩夢,後者是可期待卻又備極艱辛的上坡路。他的詩一直是他一生政治信仰的表徵,他百轉千迴所欲觸及的是亟欲建立名實相符之新國家的熱切與盼望,這至少代表了本土意識強烈的知識分子的心聲與信仰。
此集所選〈春天〉與〈秋天〉兩首小詩同時發表於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報刊上,剛好是總統大選後第二天,三一九兩顆子彈槍擊事件後的第三天,因此特具政治意味。
〈春天〉說的是歷史記憶不可能被美麗的風景所遮掩,「槍聲/擊痛死難者的叫喊」是此詩警句,代表了詩人內心對傷痛永在的不忍、和對血洗歷史者的批判。
〈秋天〉前四句是面對秋風的喜悅,後四句是對秋殺氣息的感嘆,一向上看,一向下看,兩相對比,冷靜寫出面對同一景色的兩種態度,暗示了當下社會的兩極現象。
〈訊息〉藉一封不知名的信,引發一連串的猜測。可能是喜帖、訃聞、情書、警察傳喚單,最有可能的是在報紙刊出的小詩,說的盡是平日生活所觸的再一次回味,以平順和緩的詩文,暗示自身無不可面對的從容處世態度。
〈在世紀之橋的禱詞〉是在新舊世紀之交為台灣祝禱的詩作,語氣正面積極,充滿對台灣未來的憧憬與期盼。寫在一九九八年的〈在葡萄牙歌聲裡的即興筆記〉一詩,則是藉薩拉馬戈得諾具爾獎的訊息,大加宣揚詩人的天職和勇氣是不分古今中外的,尤其在詩末,更點出己身的毅力和不懈,是要「升起詩的天線在風浪中」。他的詩十足展現了知識分子的膽識和勇氣。
李敏勇,屏東恆春人,出生在高雄縣,現居台北。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教師、記者、企劃,現任職企業界。曾主編《笠》詩刊,擔任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著有詩集《暗房》、《鎮魂歌》、《野生思考》、《戒嚴風景》、《傾斜的島》、《心的奏鳴曲》、《青春腐蝕畫》,及散文、小說、文學與社會評論集等約四十冊。
春天 不要以為 窗口的風景 永遠那麼美麗 就在大樹下 槍聲 擊痛死難者的叫喊 一片一片新葉 是一年又一年出現的 記憶 秋天 島嶼在唱歌 呼應著風 樹上的葉子們 在歌聲中起舞 路人束起衣領 帽簷下一雙眼睛 看落葉 在奔跑 訊息 今天 信箱裡 是一張喜帖吧 不知哪個青年的戀情開了花 吐露著芬芳 不 也許是一張訃聞 某個友人悄悄離開人間 從遠方捎來告別信 靜默裡有一聲嘆息 不不 也許是警察的傳喚通知 為了追究某一次示威遊行 伸出了黑手 恐嚇的字句交織著權力的網 不不不 也許是一封情書 是某個陌生女子的寄意 淡淡的哀愁 夾寄在秋天的落葉裡 不不不不 也許只是一首發表在報紙的小詩 在副刊的角落植印著我的心聲 編輯人好意寄來 讓撰稿人回味細讀 在世紀之橋的禱詞 戰火成為歷史 災難成為記憶 傷痕與淚珠形成自然的簾幕 在薄雨中呈顯 一座彩虹像世紀之橋 在時間的盡頭和起點 分隔過去和未來 現在是 世紀末的黃昏 入夜後 星星會指引我們 穿越黑暗 從水平線透露的光照耀日昇之屋 福爾摩沙依然在海的懷抱裡 釀造夢想 地平線上 她的子民共同呼喚 台灣的名字 在葡萄牙歌聲裡的即興筆記
陳大為 (一九六九│) 南洋廣大的水域、土地、太陽、巫師、廟宇、古老神祕的信仰、遙遠的歷史和傳統,構建了陳大為複雜錯綜、理也理不清的心靈和思維系統。那是被搞不清的歷史書寫就的一種符咒,貼在他的腦門上,雜糅入他的命運和血脈,頑固而堅定地挺立於他夢境的中心,他不得不時時運轉他的筆心,起乩似地運轉,冗長而說不完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長篇且大論。那的確需要極度的耐心和細心,才能解開他欲敘述,不,是一種控制不住的力道要他敘述的某些內容,其中似乎隱含著什麼天機。
因此要閱讀陳大為是不容易的,他的作品有龐偉的史詩企圖,意象繁複而深邃,語言遠遠去到古代的、屬於月亮那一面的石階,沒有一些古典的修為和開向南洋的準備,將很容易迷航在藍色詭異的海域。
〈相師〉以算命師為主角,用戲謔口吻敘述相師的形象,也映照出求問的人惶恐不安。「話如游龍先峰迴再路轉/你似盲人騎瞎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此詩描繪二者互動的心理與形象,格外生動。〈守墓人〉詩中的「我」在墓地看盡了人世的生死離別、也體驗到了人情的冷暖。角度特別,題材隱諱,儘管墓地是死亡的象徵,但在這裡卻有了不為人知的「生機」。詩末說「我」是「一團活著的磷火」,想像鬼魅,也反映了現實世界冷暖兼雜的一面。
在〈層出不窮〉一作中,作者藉著食物與味覺兩者的交構形容漢語言辭彙的繁複性。食物是生理需求的產物,它向外延伸出的種種指涉通常脫離不了對故鄉的依戀││母親的手藝、家人的溫暖,和故鄉、傳統的一切連結。而作者在詩作重複提到了家鄉的美食名稱,層出不窮的食物詞語,建構出了一種無可取代的地方感。〈前半輩子〉敘述透過一本影像集讀見了一座城市的古老記憶、隱匿的身世,那是詩人本來不熟悉的。在影像集中土地和人成了一種可以述說的發聲體,它涵容了城市的成長故事,也體現人與土地最直接的情感,此詩也再現了閱讀影像的深刻感受。
〈靠近羅摩衍那〉寫屠妖節在城市中進行的印度節慶,「靠近」的是慶典,靠不近的是信仰,此詩即寫節慶的氣氛和自身的感受。《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約八十萬字。以國王羅摩與王妃悉多悲歡離合的故事為主線,描寫印度古代宮廷內部和列國之間的鬥爭。《西遊記》的孫悟空形象,即與此書神猴哈奴曼有關。
陳大為,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馬來西亞,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詩集《治洪前書》、《再鴻門》、《盡是魅影的城國》、《靠近羅摩衍那》,散文集、人物傳記、論文集多種。
相師 把你沒有信心的心交給我 把你有問題的掌上地理││ 臉是氣象的江山 命運的形下 眉毛是飛起來或飛不起的翅膀 五官預告你未來的興亡 快把八字交給我加減乘除看看: 動用易經的力道 太極的技巧 我的食指把住你赤裸的心跳 話如游龍先峰迴再路轉 你似盲人騎瞎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 任我把螢火說明成太陽 把長長一生像畫符般規畫。 把你失去邏輯的命運交給我 把你腦海裡潛泳的懷疑……
守墓人 我的生平葬滿鬼魅夜景 蠕動的墓誌銘 綠色的怪聲音 我是義山的掌門獨守幡飛的孤寂, 不同的陌生人送來陌生的魂 我開關著陽界和陰間的門 孝子的鹹眼睛 不孝子的酸口氣 清明的熱鬧 一整年的冷冰冰 天和地的日記裡都是:陰有雨。 躺下來的躺入另一座人間 月光防腐住悲情和歲月 反覆地想當年 不外乎那幾件 茅草是他們滔滔交談的舌頭 風把方言從山峰轉到山峰, 守著盜墓的賊子 野狗的爪子 我是大大一團活著的磷火 只在深夜的故事裡出沒。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新詩30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2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詩30家
紀錄了從舊世紀末到新世紀初,跨世代的30位詩人之作品,題材包羅萬象、焦點由近而遠,為台灣30年來的詩壇做了一次全面的定位與整理。
入選菁英詩人:李敏勇/羅青/蘇紹連/馮青/簡政珍/杜十三/白靈/零雨/陳育虹/陳義芝/渡也/楊澤/陳黎/詹澈/向陽/羅智成/焦桐/路寒袖/孫維民/陳克華/瓦歷斯‧諾幹/鴻鴻/紀小樣/許悔之/唐捐/李進文/顏艾琳/陳大為/鯨向海/楊佳嫻
作者簡介:
白靈,本名莊祖煌,福建人,現任臺北工專副教授,從事新詩創作二十年,於藍星詩刊闢有〈新詩隨筆〉專欄。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值年常務理事。著有《後裔》、《大黃河》、《給夢一把梯子》、《一首詩的誕生》、《一首詩的遊戲》、《一首詩的玩法》等多部,主編《新詩二十家》、《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詩卷》。詩作獲銘刻於臺北松江詩園內。曾獲中國時報敘事詩首獎、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創世紀詩獎等多種獎項
章節試閱
新詩30家 李敏勇 (一九四七│) 詩對李敏勇而言,是向歷史告解的自白書,也是面對自我的備忘錄。他的心是熱的,筆是冷的,他的筆是光束集中的雷射小刃、乃至「顫慄的舌尖」,寒光所至,希望能拉朽摧枯、去腐除鏽,深入「意義的黑夜」,盡到文學的社會功用。歷史與未來是他筆尖經常探觸的主題,前者的陰暗面常化身為不斷啃噬後人的野獸和噩夢,後者是可期待卻又備極艱辛的上坡路。他的詩一直是他一生政治信仰的表徵,他百轉千迴所欲觸及的是亟欲建立名實相符之新國家的熱切與盼望,這至少代表了本土意識強烈的知識分子的心聲與信仰。 此集...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白靈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4-10 ISBN/ISSN:9789574444915
- 頁數:3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