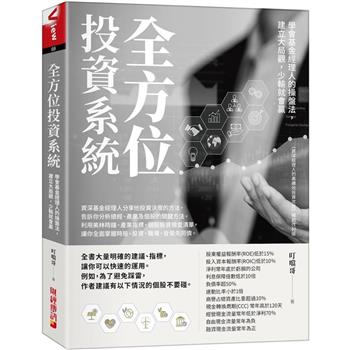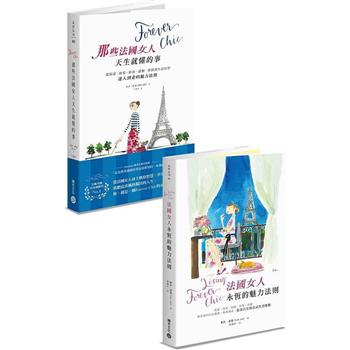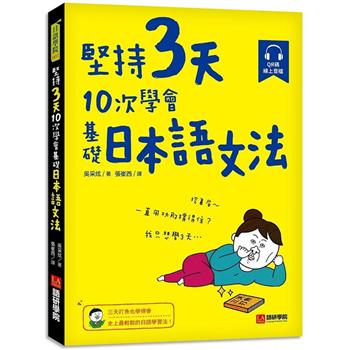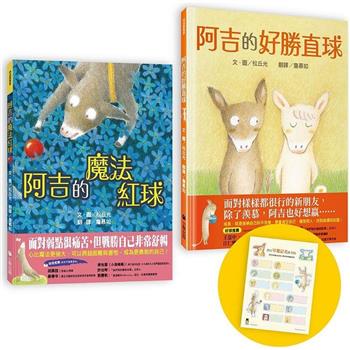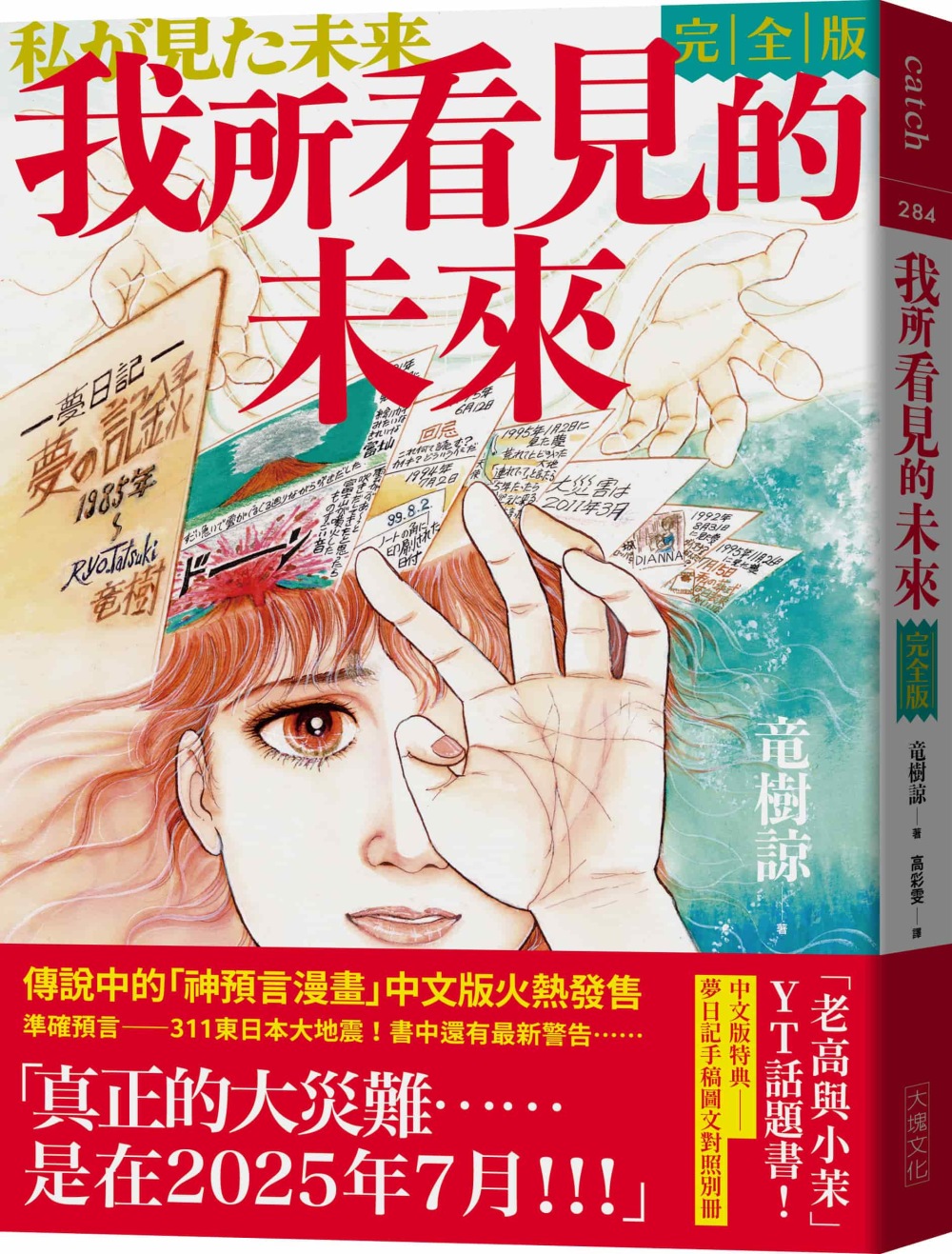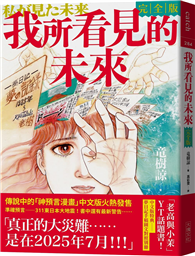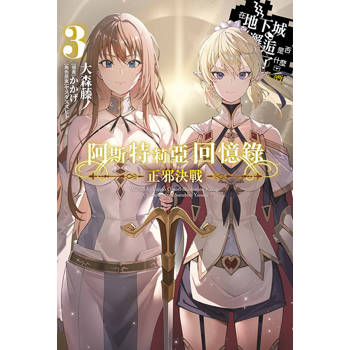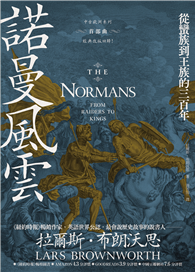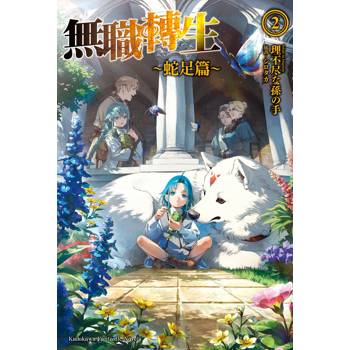歸園自然
榮哥是竹山當地人,少小離家,目前是假日農夫,有一塊四分地的茶園。
他會認識我,是因為這小地方沒什麼祕密,他總聽說有個肖年仔(年輕人)不認真除草,懶惰不愛照起工,沒有認真施肥打藥,茶產量跟別人比總是很低,但這些年茶樹長得還不錯,如果再噴藥一定會更好更漂亮……
從他的口述中,我才知道「鄰人心中的我」是什麼形象,也大概知道兄臺來找我這個肖年仔所為何事。幾輪茶起茶落後,他開始吐出心中的糾結。
自然農法的迷思
「我回來接手這片茶園,其實是想從事自然農法,當初也有很多人給我不同的意見,最困擾我的是,到底要怎麼達到自然農法、不用農藥。」他雙手交纏托著頭,一臉苦惱。
「帶我進入自然農法的前輩,告訴我的轉作方法非常簡單,不要除草、不要施肥、也不要噴水,偶爾去拉拉茶樹上的藤蔓就好。這樣的方法讓我很不安,除了旁邊的鄰居一直告訴我,草會競爭茶樹的肥分外,雜草到底要留多長也困擾著我,常常我從臺北回來,面對的就是滿園與茶同高的雜草,除也除不盡,叢頭雜草拔除又費時費力。天氣濕熱,雜草長得又快又猛,我的體力只夠工作到太陽冒出頭,每次工作都有種無力感。難道從事自然農法,我的農園不能像公園的草皮一般美觀嗎?」他問。
果然又是「著相」的老症頭,我心底琢磨著該怎麼回答他。
「榮哥,你覺得什麼是有機農法?什麼是自然農法?你覺得你屬於哪一種農法?」我問。
「有機農法就是不用農藥、不用化肥,經過專門的驗證機構驗證核可,就是有機農業;而自然農法就是要師法自然,以我的茶園來說,就是自然農法。」
「那什麼是自然呢?」我問。
「自然……自然是很自然的狀態?」榮哥突然楞住,不知如何回答。
「那我換個方式問,你覺得一塊自然的田地裡,要有什麼?」我看著榮哥問。
依靠自然力量的農法
習慣從負面表列來描述有機農法或自然農法,我們似乎很少想過,一片自然的田園,應該要存在什麼。自然農法,是因為在這環境下,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緣起,彼此相互依存而成為這個整體,本自具足,故為自然。
實行自然農法時,為何僅在田地播種,少用功力,就能長成肥美作物,不需要靠農人勤力多勞?是因為這方田地早已具足成熟作物的種種條件。例如,作物生長所需要的陽光能量、水分、礦物質養分與空氣,不需要靠農人勉力,在這片田地都可以自然不間斷地供應,我們便稱這樣的農法為「自然」農法,依靠自然的力量的緣故。
那麼,何謂自然的力量呢?最直觀的理解,近似於生命求生存的力量。試觀察一片葉子掉落到田地化成虛無的過程:枯葉落在田地,一時半晌看不出變化,三五日後,枯葉便出現不規則與凹凸崎嶇的坑洞;有時翻開枯葉,便看到不知名的節肢昆蟲逃竄。
兩週後,只剩下脈骨與脈痕,能證明兩週前枯葉曾經存在,還有那曾被稱為枯葉的物件旁的土面,有一堆堆蚓糞顆粒堆聚。一個月後,若非刻意追想,否則曾經存在枯葉的土面,只剩青草茵茵,或許還有野芳綻放,以及不遠處又一片片的落葉枯草,重複這樣的過程。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中國詩人龔自珍看花開花落有感,英國爵士把眼光放至那方春泥,有機農業的鼻祖艾伯特.霍華(Sir Albert Howard)在一九四○年出版書籍《農業聖典》(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寫了這樣一段話:「生命之輪由兩個部分所構建:生長與分解,並互為彼此的另一面。」
是的,生命無非就是為了求生存而努力,落在土壤的葉子能成為繼起的生命,節肢昆蟲、蚯蚓、真菌、細菌、原生動物、線蟲、哺乳類、爬蟲類等,依序繁榮的因緣,這片葉子的落下,便與這個環境無法分割。相對地,當這些生物為求生存、繁衍所做的種種努力,最後死亡回歸大地,這方春泥便具足植物萌吐新芽繁榮成長的所有條件,因為如此,才能是本自具足。
有機,就是有生機
如果農人沒有認知到這一層,何能稱所做為自然?如果已經體會到這一層,不管是有機農法也好,自然農法也好,友善農法也好,什麼名相都好,他都已經走在與環境共處、共存、共榮的這條路上。
有機,就是有生機:土壤有生命,環境有生氣,如此才有孕育健康作物的條件,農人一切農業作為──除草、不除草、噴水、不噴水、施肥、不施肥、噴藥、不噴藥等,都必須圍繞著這個中心理念而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自然就心平氣和,不會為眼前一片雜草蔓生而慌亂,也不會心生妄想把自己的田園打造成公園了。
「所以,如果拔下來的草可以幫助豐富土壤生命,那我就拔;如果天氣太熱,除草會讓土壤太乾,傷害土壤生態系,那我就不拔。如果像公園一樣的草皮不能豐富生命,那種草皮就沒意義;如果雜亂的草有助於田地健康,那何必一定要它整齊乾淨。」榮哥喃喃總結。
「這席茶沒有白喝,你得到它了。」我笑著再為這位菩薩斟上一杯茶,同行路上多此一友,想來也是彼此的福分了。
種地瓜葉種出四攝法
家園前,種有一畦地瓜葉,供應平日吃食菜蔬,因為家人工作忙碌,這種懶人蔬菜就成為耕作首選,飯前只消至園中摘取新鮮地瓜嫩葉,洗淨後汆燙淋上薑油、蠔油,或者大火快炒些許佐味,就是飯桌菜食良伴,營養又美味。
冬末瓜葉收根,要讓地瓜葉重新恢復生機,必須在冬末清園,將田中地瓜藤曬至略為凋萎後,剪段重新插入土壤中,這對農家來說,是稀鬆平常的工作,妻躍躍欲試,加上朋友一家來訪,於是把種地瓜葉的工作交給妻與朋友一家人。
妻子的提醒
幾日後,在菜圃中澆水時,才發現地瓜藤只覆上淺淺的一層土,雙指夾住瓜藤輕抽,就把整段瓜藤抽離土壤,此時心中略有不快,心想:這麼簡單的工作,做之前也示範種了一小段,怎麼實際做起來和示範區差這麼多。妻喚我吃早餐時,只見我不斷地將瓜藤抽離土壤、重新挖洞、埋回土中,理都不理,知我心中不快,於是表明希望早餐後,能同她一起把地瓜葉種好。
餐後,我與妻再仔細地核對種植流程:先挖出深約十公分的溝,擺上剪好的瓜藤,然後把土覆上,澆水點根完成。如此簡單的流程,實際操作時就發現有些出入:妻一直把重點擺在瓜藤擺放的方向與角度,回饋我一開始教時提到用四十五度角擺放,而且我種的瓜藤明顯較挺些。然扦插地瓜藤能不能長成,關鍵是瓜藤有沒有與土壤充分接觸,能不能順利發根汲取土壤養分,和扦插角度的關係不大。
我本想將地瓜葉種植的方法傳授完,就著手田區內的工作,觀察到不諳田事的妻,還是沒領會種植方法,索性陪著妻把整畦地瓜葉重新植完,也讓妻意會種植作物存活的關鍵──接地氣。感謝妻成熟賢慧,沒有棄嫌我性急臉臭,傳道過於簡化,並未仔細說明原則,還陪笑著一起重新植完整一畦地瓜葉。
菩薩在行利他道時,遵循的原則可歸為四面向:布施、愛語、利行、同事,首先菩薩必須用種種的方式,透過身、語、意傳遞對其他有情的關心,想辦法給他好處,攝受其他有情成為眷屬,願意聽菩薩的教悔,然後用種種柔軟語傳遞善美的教理,教導正確行持的作法,並且同他一起造善。在種地瓜葉的過程,我根本就忘失四攝法,若不是妻的微笑,才驀然想起:「啊!顥嚴菩薩,你不是說要學佛嗎?怎麼種個地瓜葉就忘記要學佛了。」
四攝法的有機農法
誠然,推動有機農業扎根的具體作法,就是四攝法。在返鄉種有機茶六年多來,第三年覺得自己的理論與技術都摸到邊,想著要怎麼擴大種植面積,於是到庄內租了一塊荒廢多年的茶園耕作。位在路邊的茶園,最不缺的是往來的關心與玩笑,關心是這個年輕小夥子有沒有辦法堅持做下去,玩笑是看到這塊土地草如此長,是不是主人都日曬屁股才下田管理。
茶園與紅龍果園比鄰,主人是個樸實的斜槓莊稼漢,平常幫人燒焊鐵件,兼業自己的果園,為了節省勞力,多用合成肥料搭配除草劑管理,也因為無法與隔壁田區畫設隔離帶的緣故,即使自己租的田區不噴任何農藥、不使用化肥,也無法申請有機驗證管理,儘管如此,我還是堅持用有機的方式管理茶園。
過了半年多,一日,我在租用田區噴灑發酵葉面肥,隔壁紅龍果田的大哥走過來寒暄,當時我半開玩笑說他最近田區雜草也長了,是不是旁邊有個不良示範,讓他也開始發懶,大哥看了一會兒,說:「其實我都有在觀察你怎麼作業,我覺得你的方法有道理,土壤會因為有雜草的關係愈來愈肥沃,沒有浪費肥力,又幫助排水,連農藥錢都省下來了。」
在那之後的半年,我觀察鄰居紅龍果田大哥開始不用除草劑,有雜草也是等草長到兩臺尺高時才用機器割除,施肥時甚至就學我直接施用在雜草上,因為沒有病害,不用噴灑農藥,只套了網袋防昆蟲、蝸牛咬食,以及鳥類啄食。
我向他訂了一籃紅龍果分贈親友,大部分的親友都回饋味道乾淨、不死甜,吃起來相當舒服,於是我又主動分享了大哥的聯絡方式,希望幫他們架起更多的橋樑。因為大哥的田區不用農藥、不用除草劑,等於我租的茶園旁多一大塊隔離田區,免除了農藥汙染的風險,往有機耕作發展又更進一步。
佛法的理論很美,真正碰上境界,能用上佛法改變緣起,更是美不勝收!我抬頭望妻揮汗,真覺得她才是個菩薩,她用笑容告訴我:「哎呀,要耕作有機,沒用上四攝法,沒有同我一起做事,你又怎麼當得成菩薩呢?」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茶園裡遇見佛陀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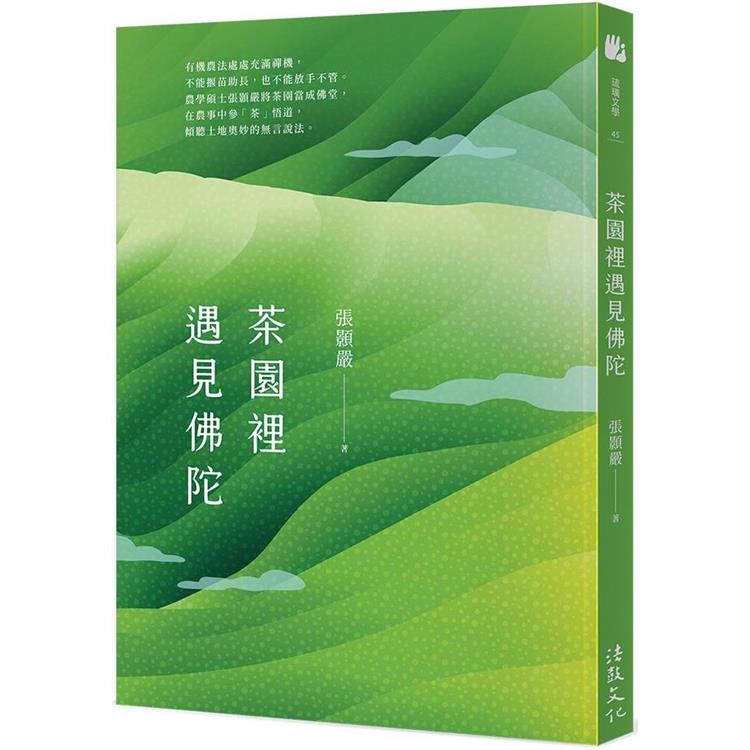 |
茶園裡遇見佛陀【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張顥嚴 出版社: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 出版日期:2022-12-12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生活佛法 |
$ 252 |
中文書 |
$ 252 |
佛教 |
$ 252 |
科學‧科普 |
$ 252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茶園裡遇見佛陀
人本來就該吃有能量的食物!
讓世界更美好的「心農法」耕作奮鬥史。
無防治、不殺生,頂多用手摘摘避債蛾,
鄰居看他三不五時才去撒點肥料,
更過分的是居然都撒在雜草上,簡直邪門外道。
然而茶葉拿去參加有機茶分級比賽,全得了獎。
作者擁有臺大農化專業,返鄉從事有機茶園,
從自信滿滿到挫折不斷,
他傾聽土地的聲音,以緣起智慧突破慣性思維,
印證了佛法用在農業生產的可能。
本書為充滿禪機的「心農法」耕作奮鬥史。
作者簡介:
張顥嚴
一九八七年生,成長於南投縣竹山鎮西南角的山村。自小看著父親苦讀醫書長大,雖然無緣走向濟世之路,卻種下喜好閱讀研究的基礎。
臺大農業化學系學士、碩士畢業,短暫從事環境顧問工作後,決心返鄉扛起茶園農事。曾獲農委會第三屆百大青農輔導,並擔任外交部第一屆南向青農大使。
目前從事有機茶業工作,擁有約三公頃的認證有機農地,皆以「無防治」、「不殺生」,活化土壤生態系的方式做茶園栽培管理,參加國內舉辦的有機茶分級賽屢屢獲獎。因理論與實務兼備,經常應邀擔任學校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講師,並於各大專院校相關課程授課,推廣慈心農法不遺餘力。
章節試閱
歸園自然
榮哥是竹山當地人,少小離家,目前是假日農夫,有一塊四分地的茶園。
他會認識我,是因為這小地方沒什麼祕密,他總聽說有個肖年仔(年輕人)不認真除草,懶惰不愛照起工,沒有認真施肥打藥,茶產量跟別人比總是很低,但這些年茶樹長得還不錯,如果再噴藥一定會更好更漂亮……
從他的口述中,我才知道「鄰人心中的我」是什麼形象,也大概知道兄臺來找我這個肖年仔所為何事。幾輪茶起茶落後,他開始吐出心中的糾結。
自然農法的迷思
「我回來接手這片茶園,其實是想從事自然農法,當初也有很多人給我不同的意見,最...
榮哥是竹山當地人,少小離家,目前是假日農夫,有一塊四分地的茶園。
他會認識我,是因為這小地方沒什麼祕密,他總聽說有個肖年仔(年輕人)不認真除草,懶惰不愛照起工,沒有認真施肥打藥,茶產量跟別人比總是很低,但這些年茶樹長得還不錯,如果再噴藥一定會更好更漂亮……
從他的口述中,我才知道「鄰人心中的我」是什麼形象,也大概知道兄臺來找我這個肖年仔所為何事。幾輪茶起茶落後,他開始吐出心中的糾結。
自然農法的迷思
「我回來接手這片茶園,其實是想從事自然農法,當初也有很多人給我不同的意見,最...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讓世界更美好的心農法
我不是一個喜歡作農的人,卻好像願力注使業風吹送般「必然地」進入農業這個領域。
從小母親用身教告訴我,作農是一件很苦的事,做有機更苦,千萬不要像你老爸一樣,頭殼壞去做有機。所以從小我就在一種莫名的恐懼與自卑中長大,恐懼自己會像母親描述的那樣陷在社會的底層,而自卑感,自然是來自原生於這個苦的階級裡。
當父親中風後,我再三抉擇考量,決定放下已有的學歷與準備開展的職涯,返鄉從農,那時我心中充滿著幽暗與陰影,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味道在,完全不敢把這決定告訴...
我不是一個喜歡作農的人,卻好像願力注使業風吹送般「必然地」進入農業這個領域。
從小母親用身教告訴我,作農是一件很苦的事,做有機更苦,千萬不要像你老爸一樣,頭殼壞去做有機。所以從小我就在一種莫名的恐懼與自卑中長大,恐懼自己會像母親描述的那樣陷在社會的底層,而自卑感,自然是來自原生於這個苦的階級裡。
當父親中風後,我再三抉擇考量,決定放下已有的學歷與準備開展的職涯,返鄉從農,那時我心中充滿著幽暗與陰影,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味道在,完全不敢把這決定告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讓世界更美好的心農法
一、重新學習心農業
歸園自然
除雜草?除心草?
靜觀省力處
當頭「樑」喝
土地的滋味
所思與所為的相互印證
與福岡正信的對話
農學與佛法的交會
二、以農法實踐佛法
種地瓜葉種出四攝法
茶園窺緣起
福報最重要
農事斷捨離
有機農法也有戒律?
由心塑根性
心的力量
佛菩薩的心語
八風吹得動
三、尊重大自然生機
救蝌蚪記
哈達的故事
螞蟻的路
讓愛傳出去
菩薩的茶
誠意吃水甜
有機的初心
誰給了肥?
幫土壤鬆筋
四、護生的慈心農法
菩薩的農法
耕耘出十善的社會
農耕...
一、重新學習心農業
歸園自然
除雜草?除心草?
靜觀省力處
當頭「樑」喝
土地的滋味
所思與所為的相互印證
與福岡正信的對話
農學與佛法的交會
二、以農法實踐佛法
種地瓜葉種出四攝法
茶園窺緣起
福報最重要
農事斷捨離
有機農法也有戒律?
由心塑根性
心的力量
佛菩薩的心語
八風吹得動
三、尊重大自然生機
救蝌蚪記
哈達的故事
螞蟻的路
讓愛傳出去
菩薩的茶
誠意吃水甜
有機的初心
誰給了肥?
幫土壤鬆筋
四、護生的慈心農法
菩薩的農法
耕耘出十善的社會
農耕...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