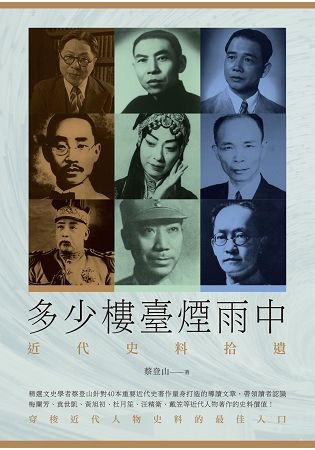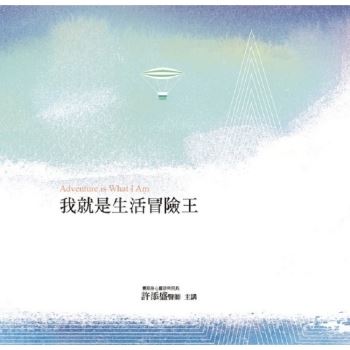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大時代的見證:黃旭初和他的五冊回憶錄】
黃旭初(一八九二~一九七五),廣西容縣人。係廣西省政府主席,主政廣西近廿年。黃旭初年十六入容縣師範,二十歲肄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與李宗仁有同學之誼。一九一四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中國陸軍大學學習。一九一七年,任廣西陸軍模範營連長,保定軍校畢業的黃紹竑、白崇禧任副連長。一九一九年由湘歸任廣西陸軍第一師步二團團附。一九二一年六月,調任廣西督軍署中校參謀。一九二三年擔任李宗仁的「廣西定桂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六年北伐軍興,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白崇禧任參謀長,黃旭初任第四旅旅長,後升任第七軍第六師師長,屢建奇功。一九二八年升任第十五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一九三○年任護黨救國軍第十五軍軍長。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黃旭初在南寧就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一當就是十九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止。與山西的閻錫山同以模範省著稱中外,有聲於時。黃旭初積極配合李宗仁、白崇禧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大建設」,在幾年的時間裏,桂系一躍成為中國西南的一大地方實力派。李宗仁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黃君(指黃旭初)老成練達,與我有同窗之雅,並曾入陸軍大學深造,謹小慎微,應對如流,全軍賴其輔導,上下歸心。嗣後我軍竟能戡平八桂,問鼎中原,渠早年主持戎幕,為本軍打下良好基礎之功,實不可沒。黃君其後主持廣西省政達十九年,澤被桑梓,亦非幸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黃旭初離開南寧,因為軍事情勢上南寧已不可守。十二月三日他和白崇禧同時飛抵海南島的海口,他們在海南十九天。白崇禧乘艦出海指揮作戰曾小別一週,其餘每天都有會議或晤談,商討的都屬當前軍國要事,全不及私。又因由桂入越的敗殘部隊,為數尚不少,白崇禧乃囑黃旭初赴越南籌謀部隊生活的照顧和善後安排。法國駐邕龍領事田友仁那時也遷到海口,黃旭初請他辦理入越護照,但他轉報法方得不到答覆,無法辦通赴越南手續。十二月二十一日黃旭初和白氏握手分袂,飛往香港,白氏南飛榆林視察。不料此別竟成永訣!自此,黃旭初寓居香港,後來國府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但他一直沒有到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因心臟病發作,病逝香港九龍浸會醫院,享年八十四歲。
黃旭初在五○年代末在香港雜誌上開始寫回憶的文章,前後有十來年,據香港傳記作家胡志偉先生估計,有二百一十五篇,共一百卅萬言。其中成書出版的只有《我的母親》一書,另外還有《八桂憶往錄》(後名為《廣西懷鄉記》)、《廣西與中央廿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這兩部書稿篇幅頗大的,史料價值尤高。胡志偉的評價是「從地域來講,他寫了自一八九八年李立廷領導會黨起義至國軍由桂南退入越南期間的廣西內政、邊防、外交、建設、金融、民族、約法、議員、自治、鐵路、糧產、通志、民意機關、粵桂關係以及外界對廣西的評價,儼然一部廿世紀五十年代前的廣西省斷代史;從政事來看,他從同盟會滲入廣西、辛亥柳州獨立、陸榮廷討袁、廣西護法、桂軍參加北伐、粵桂之戰、龍潭大戰、粵桂合力敉平南昌暴動、西征唐生智、逐奉軍出關、用兵武漢、黃張攻粵、滇軍攻南寧、中原大戰、粵桂反蔣、寧桂復合、桂南會戰、大別山戰鬥、衡陽保衛戰、崑崙關血戰、常德會戰、南寧兩次陷日、反攻桂柳、廣西光復,一直寫到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李白求和失敗、李宗仁飛美、監察院彈劾李宗仁、李宗仁回歸大陸,活生生是一部桂系政治軍事活動史。」。此外還有〈辛亥革命廣西援鄂北伐軍〉、〈辛亥革命造成廣西陸榮廷握政〉、〈辛亥革命時廣西省議會與臨時約法〉、〈抗戰前夕寧桂間的微妙關係〉、〈遷省史話〉、〈廣西回應雲南護國討袁始末〉、〈劉古香柳州獨居〉等近代史料的文章,但可惜的是並沒有單獨結集出版。
胡志偉還特別指出黃旭初寫近代史,資料主要取自他自己的日記,部份依據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盧玉衡的口述和第五軍司令部編印處李誠毅等人的手記;敵方的行動,則依據日本人鈴木醇美的《廣西會戰紀事》等書。這也是他回憶錄史料之價值較高的所在。一般我們看到的回憶錄都是作者晚年的回憶之作,由於是數十年的往事,即使有驚人的記憶力,許多細節還是無法回溯的。而黃旭初寫這些戰役,有時間,有路線,何日何地被攻陷,戰役的整個路線圖,一清二楚。苟非靠當時的日記所載,是難以做到的。
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巫惠民說他幾經周折後,在自治區文化廳、區黨委統戰部和廣西海外聯誼會的多方努力和協調下,終於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將黃旭初的日記和信札徵集到,成為國家二級珍貴文物收藏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日記是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間所寫的,除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兩年共用一本外,其餘每年一本,共四十四本。徵集時,除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年這六年日記因外借未還而沒有徵集外,其餘三十八本全部徵集入藏。而信札部分黃旭初將之集成七冊,共二○八封,一○七九頁。有李宗仁給蔣介石、黃旭初和臺北張群(岳軍)的信,有白崇禧致黃旭初的信,也有黃旭初給李宗仁以及黃旭初與夏威、程思遠、徐梗生聯名給李宗仁的信等。
鑑於黃旭初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我聯絡上在香港的黃旭初的次子黃武良同意出版。我找齊了黃旭初在香港《春秋》(半月刊)連載的《廣西與中央廿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四十四章節,他在書稿最後記了「一九六三、八、四初稿」,這書稿前後,寫了近兩年的時間。文章刊出後,李宗仁從美國來函,對第一篇的章節作了若干更正與補充。於是黃旭初又寫了補正之一〈李宗仁由美來函話當年〉、補正之二〈廣西人在浙皖兩省的地方政權〉、補正之三〈桂人主皖政─由李宗仁到夏威〉、補正之四〈國軍戰敗避入越南經過詳情〉,對原書稿做了更詳盡的補充,可見其精益求精的態度。
此書稿談及李宗仁、白崇禧和蔣介石的恩怨離合甚多,為此我又找到黃旭初所寫的四篇文章,分別是:〈白崇禧兩度任副總參謀長之憶〉、〈蔣李初次會晤經過詳情〉、〈蔣李第二次會晤經過詳情〉、〈我記憶中的早年李宗仁〉,當作此書稿的附錄,如此對李宗仁、白崇禧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當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書名也改為《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
鑑於《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一書之重要性,我進一步蒐集黃旭初發表過的文章,詳加閱讀,發現其集中寫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謂「廣西三傑」的文章,有數十篇之多。(案:後來由於黃紹竑離開廣西到中央,因此「廣西三傑」的稱謂改指: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只是這些文章發表時是東一篇、西一篇,雜亂而沒有順序的,它沒有依照時間先後次序,也沒有依人物事件排序,前前後後大約寫了幾年,它完全不同於《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中,除附錄四篇是我補進去的外,其他完全是作者自訂的章節。因之如何將這些文章串連在一起,就成了我的難題。
我於是先區分為三部分,分別為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再依他們的生平去排定文章的次序(無法根據文章發表的先後),但有同時寫兩個人的如〈李宗仁頭白,黃紹竑骨寒!──當年兩封公開信,如今一夢隔人天!〉一文,只得擺在李宗仁部分。至於有關李宗仁思想突變,原因何在?黃旭初曾兩三次提及,內容大同小異,但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七○年六月所寫的〈李宗仁晚年思想轉變的由來──為了留存史實特刊露我與李氏往覆兩函〉一文,其中並將甘介侯與溫金華兩氏所言,併附篇末,藉供參考,該文應該是最完整者。前面兩文雖有引用但並不提及甘、溫兩人之姓名,或許怕造成當事人之困擾,作者之宅心仁厚,由此可見。這本書編成後就名為《黃旭初回憶錄─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名作家白先勇教授特為此書寫了推薦序〈新桂系信史―《黃旭初回憶錄》的重要性〉,而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則為此書寫了〈黃旭初與「廣西三傑」〉的導讀文章。
《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是以「史」為主,依時間次序,講述廣西與中央廿餘年來悲歡離合。《黃旭初回憶錄─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是以「傳」為主,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謂「廣西三傑」的生平事蹟,種種軼事秘聞為其寫作的重點。由於作者與他們之間甚為熟稔,甚至有時朝夕與共,因此有近身之觀察,這是其他寫傳者所做不到的。《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與《黃旭初回憶錄─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兩書,可說是互為表裡,合而觀之,則有「史」有「傳」,如同干將莫邪,雙劍合一,更足以明瞭此段歷史之軌跡與人事之興替!
至於《黃旭初回憶錄─從辛亥到抗戰》,內容收錄諸多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的珍貴史料,包含辛亥革命時期廣西北伐軍的行動,孫中山訪日面臨的諸多阻礙,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造訪廣西的記錄彙集,蔣中正與黃埔軍校的深切淵源,切關北伐成敗的龍潭大戰等等。以黃旭初的日記加上歷史文獻,重揭辛亥到抗戰時期的歷史真相。
黃旭初回憶錄中,他生前親自訂定章節的《八桂憶往錄》(又名《廣西還鄉記》),篇幅較大。為便於閱讀今將其分為兩部,分別是:《黃旭初回憶錄─孫中山與陸榮廷的護法暗鬥》及《黃旭初回憶錄─抗戰前、中、後的廣西變革》。另他原先唯一結集出版過的《我的母親》薄薄一小冊,此次亦予收錄,附之於《黃旭初回憶錄─抗戰前、中、後的廣西變革》之後。如此他的回憶錄一共五本,有一百三十萬字,可謂齊備矣。黃旭初晚年在香江一隅,用了十餘年的時光,來寫回憶錄,不為名也不為利,但卻為歷史做了見證,其精神無疑地是令人敬佩的。
我看過為數頗多的回憶錄,有太多都是自我標榜,揚善隱惡,或道人是非,揭人短長,甚者淪為八卦及道聽塗說之作。但黃旭初的回憶錄不同於此,他寫回憶錄根據他四十年的日記及種種史料,包括數十年前作戰的路線圖,時間都記得一清二楚。而且他寫回憶錄不寫自己,苟或有之,也一筆帶過,絕無渲染。他寫回憶錄完全在寫別人,在寫整個歷史,這在所有回憶錄中確實是僅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我不識黃旭初,但我讀了他的著作,油然生起一股敬佩之心,在此引用他姪女黃華東的話說:「不過他寫史實雖多,卻很少自我標榜。他的筆下也不輕易褒貶人,所以別人也甚少議論他的長短。不像與他同時代的那些政客軍閥之流,往往留有被人談不完的傳奇或話柄。這與伯父謙虛沉著的性格有關。伯父善守中庸之道,在他二十年掌政期間,向不好大喜功,只是盡其在我的埋頭實幹,雖說不上政績輝煌,卻能在萬方多難中不隨波逐流,固守自己的崗位,二十年如一日,不見異思遷。再後更能在國事蜩螗,混亂不堪的政局中,急流勇退,淡薄自甘,始終沒有落得什麼禍國殃民的罵名,這是我們作他後輩的深深為他老人家引以為傲的!」
而黃旭初有〈八十一歲初度述懷〉詩兩首,可見其晚年生活之一斑:
其一
人生八十已尋常,屢病今來漸復康。
藥似有緣猶未斷,筆非無債暫停償。
書刊堆案翻披減,親友同城訪候荒。
且喜聯吟詩興在,聊將瓦缶引笙簧。
其二
三遷舉世總相依,頤養營生互得宜。
兒趁郊墟孫入市,我司灑掃婦為炊。
思親念切懸弧日,感舊情殷聞笛時。
世態繽紛看未足,蟾宮可許去探奇。
詩以言志,由此兩首詩中可見黃旭初的淡泊生涯,晚景堪稱悠閒。雖然一向「吶吶向人鋒斂芒」,靠著他的筆墨也能消歲月長,也寫出不少文章能永流人世間!
黃旭初的著作雖然在他完稿後的半個世紀後才出版,但是也愈更加珍貴。這證明「好書」永不寂寞的,雖然一時之間沒被發現,但終究有「識珠」者。好友江蘇南通欽鴻兄在得知《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出版的消息,來信索書,並告知他手上有黃旭初的日記手稿影印本,分別是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三年的,還有一些散頁。我原本要借為校稿之用,蒙他無私的餽贈,在此記上一筆,衷心感謝。新書發表會當天除了黃武良先生遠從香港來到臺北外,正巧從美國回臺的白先勇教授也受邀出席這場盛會,黃旭初、白崇禧兩位先生的哲嗣能在廣西同鄉會共此盛舉,真是意義非凡。其他還有美國的史學者林博文先生、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不斷地鼓勵與提攜,都是銘感五內的。而最該感謝的是黃武良先生他無私而且信任我,才是我在整理出版這五冊《黃旭初回憶錄》的最大動力,雖然前路漫漫,但不寂寞!
最後引用白先勇教授在推薦序開頭的一小段,云:「新桂系在國民黨軍隊中,並不屬於中央嫡系,在官方國軍史上,記載並不翔實,有時刻意疏漏,甚致扭曲。因此,廣西省前省主席黃旭初的回憶錄,便更加彌足珍貴,補償了國府官方歷史的不足。……黃旭初有記日記的習慣,敘述多有根據,下筆井井有條,其為人謹慎,行事篤實,三○年代,建設廣西,父親總管其事,黃旭初便為其最得力的執行者,父親託以重任,因其誠信可靠。黃旭初的回憶錄,可以說是一部新桂系信史,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袁世凱女婿薛觀瀾及其著作─《我親見的梅蘭芳》、《北洋政壇見聞錄》、《薛觀瀾談京劇》】
薛觀瀾(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原名學海,字匯東,觀瀾是他的筆名。江蘇無錫人。其祖父薛福成先後師事曾國藩、李鴻章,歷任寧紹臺道、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欽差大臣等職,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和早期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父親薛南溟是清光緒朝舉人,曾入李鴻章幕下。此後棄官轉事實業,一八八一年開始辦繭行,一八九六年與人合夥創辦繅絲廠,後又組建永泰絲業集團,成為近代著名實業家。薛觀瀾早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留學美國,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他喜愛體育運動,曾任該校田徑隊隊長,還是短跑健將。回國後,在北京匯文大學任體育教練。後曾任北洋政府監務署檢事、駐英使館三等秘書、直隸省公署顧問、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員等職。
薛觀瀾在京期間結識了袁世凱的次女袁仲楨,一九一九年十一日二日兩人結為秦晉之好,在無錫成婚時,因袁世凱已死,乃尤其子袁克定主婚。關於薛觀瀾和袁世凱的次女袁仲楨的結褵,有段小插曲。當時黎元洪總統欲將長女黎紹芬(周恩來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許配給薛觀瀾,薛觀瀾說:「黎大小姐為父母最得寵者,我見黎大小姐革履西裝,口如懸河,漸漬於泰西之風甚矣。與予性格不合,婚事不諧。」而袁世凱生前曾經做主,準備將女兒袁仲楨許配給兩江總督端方的侄子。然而袁世凱死後,這位性格剛強的「公主」逃婚,自願嫁給了她挑中的「白馬王子」薛觀瀾。因為薛觀瀾和袁仲禎在校讀書時便結識,兩人最初便是很好的朋友,以至後來雙雙排除「萬難」執著牽手。當日薛府張燈結綵,而新房設在無錫西溪下的花園洋房內。這是一座具有巴洛克風格的花園洋房,建成於一九一七年,在無錫也是屈指可數的。當時年僅十二歲的京劇名伶孟小冬,亦獻藝婚禮,無疑為婚禮錦上添花。據《錫報》載:「十一月三日晚,屋頂花園小京班及已輟演之髦兒戲班,同至西溪下薛宅合演堂會,孟小冬演《武家坡》、《捉放曹》二齣,最是精彩。小京班童伶王福英之武戲,亦甚出色」。堂戲演至凌晨一時尚未終場,為此薛南溟電話通知耀明電燈廠(薛南溟為該廠創辦人之一),要其再延長二小時用電,待戲畢再熄燈。
一九二五年春,徐樹錚受命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率考察團十五人,先後考察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德國、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等十二國。到倫敦時,薛觀瀾時任駐英使署的秘書,徐樹錚知道英國的「皇家學院」是國際聞名的,經過一番得力的宣傳,「皇家學院」始知徐樹錚是中國國學專家,果然請他公開演講兩小時,徐樹錚以〈中國音樂的沿革〉為題,叫薛觀瀾代他趕速翻譯成英文。翌日《泰晤士報》載稱,徐專使作為中國軍人有此文學成就,不勝欽佩云云。徐樹錚甚得意,遂聘薛觀瀾為秘書,待遇甚優。接著又訪問蘇聯,當時徐樹錚之隨員只有褚其祥、朱佛定與薛觀瀾三人。薛觀瀾在回憶文章說:「我當時面對史氏(史達林),印象特深,此公眉有煞氣,雙目狡獪,八字鬚如亂柴。惟他右眉之上有紅痣一粒,此殆註貴之徵,與我國黎元洪一般。」而徐樹錚與俄外長齊翟林在外交官舍為了共黨問題,通宵舌戰,均由薛觀瀾躬任翻譯,雙方各逞辭鋒,循至面紅耳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徐樹錚考察結束回到上海,十九日即動身赴京。復命後,於二十九日晚乘專車離開北京南下,途經京津間廊坊車站,被馮玉祥部下張之江劫持,當時薛觀瀾亦隨侍在側,他記下最後一幕:「行約百米,瞥見徐專使在前,由官兵數人推挽而行,月明如晝,寒氣逼人,步點甚疾,塵土飛揚,徐失一履,踒其足,回顧觀瀾者三四次。於是徐公在前,我跋其後,相距不遠,又疾行一里,前面橫一小丘,附近皆係田隴,此即預定之殺人場也。在此呼吸存亡之際,有一軍官,突如其來,問我姓甚?我說姓薛,又問:『是薛學海薛秘書麼?』我曰:『然。』軍官勃然大怒,推開挾我之二卒,以鞮踢其小腹,二卒仆地,軍官乃親自扶持觀瀾,折回原來地點,行逾百武,即聞槍聲兩響,乃徐氏被害於小丘之磡。時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一點半鐘,吾聞槍聲,潛然淚下,深感一代儒將,已隨此數響而長逝矣!」。
薛觀瀾國學底子很好,他說是得力於母教。他的外祖父是桐城吳汝綸(摯甫),當他幼年時外祖父住在他家,教他作文。而母親嗜京劇,教過他一齣《鎖五龍》。母親又准許老僕揹了他到惠泉山廟內觀劇,這是光緒三十年左右的事。那時他的家鄉無錫縣還沒有戲園設備,看戲不必花錢,懂戲的人可說絕無僅有。他家絲廠都設在上海,因此他常隨父親赴滬小住,天天去看「新舞臺」的新戲,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新茶花》、《黑籍冤魂》、《查潘鬥勝》之類,實係變相的文明戲。
宣統初年,他到北京,大過戲癮。開始學習譚派鬚生戲,連唱帶做一齊學,先由郭春元說戲,郭是楊瑞亭的開蒙老師,此時北京戲園林立,名角如雲,這是譚鑫培的全盛時期。在那幾年中(清末至民初)薛觀瀾所愛看的對象,第一是譚鑫培,第二是崔靈芝,第三是李鑫甫。而考取出洋考試之後,毋須再上課,每日看戲吃館子(致美齋),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日子。
留美歸國後,薛觀瀾說他學戲的機會比任何人都好。因為「自從一九一八年余叔岩重振舊業起,至一九二八年余叔岩突然輟演為止,我和余叔岩契深款洽,幾乎形影不離,只有這段時間,余叔岩天天吊嗓,由李佩卿操琴,這是學戲的好機會。且在一九二二年以前,都是他自動地揀戲教我,如《宮門帶》、《馬鞍山》、《焚棉山》之類,這些戲,余叔岩在臺上都沒有唱過。」薛觀瀾喜歡京劇,是知名票友,著名的劇評人,他和余叔岩亦師亦友,余叔岩曾向他請教學習中州音韻,他和孫養農等都是研究余叔岩的專家級人物。
但那時他為了稻粱謀,不能安心學戲,至今追悔莫及。一九二五年,徐樹錚被刺殺,而他死裡逃生,悻悻回到家鄉,心灰意懶,更談不到學戲的興趣了。薛觀瀾說:「回到無錫之後,我父為我提一別號,就是『觀瀾』二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教我袖手旁觀,不要再被捲入政治旋渦之中。我字匯東,這兩個字就隱在『觀瀾』二字裡面。所以我今用我的別號為筆名,乃是紀念我嚴明的父親,他老人家教訓我,言道:『今日政界黑幕重重,我不希望你做官,我更不願意你登臺唱戲,尤其你在外交界,現當簡任職,串戲更不相宜。』我當然遵命。」儘管如此,他仍未放棄京劇,他特延請孫老元(佐臣)操琴,又邀名票魏馥孫共同整理譚派各劇的詞句,其時他還記得七十餘齣,其中有的全部唱念係採余叔岩的詞句,有的僅屬大路玩藝,與余叔岩無關。他仍舊天天吊嗓子,可見他對京劇的癡迷程度。
薛觀瀾和梅蘭芳是同輩人,他僅小梅蘭芳三歲。薛觀瀾說宣統年間,在北京「文明園」第一次看到梅蘭芳,那時梅才十六歲,但已有五年舞臺經驗,他竟在開鑼第三齣為奎派鬚生德建堂配演《硃砂痣》,他飾吳大哥的妻子,青衣打扮,是日粉紅色的小戲單上竟沒有梅蘭芳的名字。但是,他一出臺,好像電燈一亮,臺下寂靜無聲,全園觀眾的靈魂被他迷住了。此因春雲出岫的梅蘭芳,的確美而艷,又端麗大方,一顰一笑,宛然巾幗。膚色白嫩,齒如編貝,手如柔荑,他雖患高度近視,然其雙瞳爆出,反若增添它的嫵媚,梅蘭芳是以「色」瘋魔了全國!所以譚鑫培生前說過:「男的唱不過梅蘭芳,女的唱不過劉喜奎,叫我怎樣混!」。
寫梅蘭芳的書籍在坊間不少,但大多數的作者都沒見過梅蘭芳本人,甚至也沒見過他演的戲,只是根據書面的資料去鋪成他一生的傳奇。而薛觀瀾則不同,他和梅蘭芳、孟小冬、余叔岩等名伶都熟悉,他又是一個著名的劇評家,他寫出的《我親見的梅蘭芳》自然與眾不同,他甚至是最早寫到梅、孟之戀的人,因為當時在中國這是犯忌的,沒人敢寫。作者當時已移居香港自可秉筆直書,直言無諱。
又如他寫梅蘭芳和余叔岩後來有了心結,更非行家所能知悉究竟的。薛觀瀾說有一天,梅蘭芳和余叔岩合演《武家坡》,這是難得一見的好戲,二人爭奇鬥勝,各不相讓,到了「誥封」一場,當余叔岩唸完「哦:他見不得我!有朝一日,我身登大寶,他與我牽馬墜鐙還嫌他老呢。」以下旦角應該接唸「薛郎:你要醒來說話。」誰知道梅蘭芳突然之間把這句忘了,在臺上僵了一些時間,余叔岩雖為掩蓋過去,他乃接唸:「句句實言:自古龍行有寶。」事後梅蘭芳大不願意,他認為余叔岩故意不提醒他,使他少唸兩句。其實余叔岩並非故意,他在臺上向抱一絲不茍的作風,與其師譚鑫培完全不同。當是時,余叔岩已有脫離梅所主持的「喜群社」的計畫,常常臨時回戲,使梅更不滿意。後來捧余的團體與捧梅的團體形成對立的狀態,捧余的決不去看梅蘭芳,這齣《武家坡》確是導火線之一。
類似的事還有不少,由於作者熟悉梨園掌故,許多事更是親見親聞,因此此書有許多道人所未道之事,其珍貴處就在此。例如他提到他所親眼目擊的上海幾位大亨,他們都是戲迷,而且喜歡登臺亮相,結果當然鬧了不少笑話。如王曉籟飾《空城計》劇中的司馬懿,居然揮軍殺進西城。張嘯林常唱《盜御馬》的竇爾墩,竟將詞句抄在大扇子上當臺照唸。杜月笙在無錫榮家堂會唱《劈三關》,屢次忘詞,只得不了了之。但他們是道地的戲迷,戲癮極大,亦肯很用心的學戲。
又作者是著名的劇評家,所觀京崑等劇包羅萬象,而且獨具慧眼。書中對所看過的戲,都有中肯之評論。薛觀瀾的曾祖父薛湘為道光朝進士,歷任湖南安福、新寧知縣、廣西潯州知府,著有《說文段氏翼》、《未雨齋詩文集》等書。稱得上是晚清嘉道年間音韻學專家。因此薛觀瀾在京劇與崑曲的研究中,特別注重音韻。他乃專治沈苑賓(乘.)所著的《韻學驪珠》一書,認為該書補弊救偏,能集大成,尤其反切最準,清濁最明。薛觀瀾說:「欲考皮黃崑曲之音韻,殆莫善於是書矣。京劇固奠枕於中州韻,然能變化無窮,有典有柯,鮮以腔害字,亦不以字害腔,比較崑曲與其他地方戲劇,自更易引人入勝。申而論之,四聲五音乃皮黃之體,鍊氣運嗓乃皮黃之用。體用兼賅,方成名角。歷代名伶如程長庚、余三勝、譚鑫培、余叔岩之儔,其畢生精力大都耗費於字音之中,精益求精,日慎一日,遂成大器,名留千古。次如梅蘭芳、程硯秋之輩,則皆心有餘而認識不足,故其唱唸夫能登峰造極。餘子更不足道矣。是音韻者,乃京劇廢興絕續之樞紐,而演員成敗利鈍之契機。」洵為知言。
薛觀瀾說他所寫的事蹟,什九是曾身歷其境的,他說蓋聞作者之條件有三,曰:「信、達、雅。」讀者諸君之於拙著,只能取一個「信」字而已。《我親見的梅蘭芳》為作者晚年的一本精彩的著作,圍繞梅蘭芳,談論當時的伶人往事和精彩的戲碼,是京劇史上的重要史料。書稿完成後不久,作者便病逝於香江,著作未及出版,歷經半世紀後,重新出版,除告慰作者外,又為京劇研究增添重要的資料。
薛觀瀾一九四九年南下香港,直至一九六四年病逝。晚年在香港《天文臺》報紙闢有「觀瀾隨筆」專欄,而在香港《春秋》雜誌亦寫有諸多回憶文章。因其身為袁世凱的女婿,對當時北洋軍閥的重要將領,如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楊宇霆等人都有深入接觸,而他和徐樹錚更是朝夕相處甚久,知之甚詳,因此多篇記載徐樹錚之事,尤其是徐樹錚廊房遇害,更是他親身所見,他前後寫有兩篇長文分別發表在《天文臺》及《春秋》雜誌,雖詳略有別,而皆作者身歷其境,可補正史之不足。
薛觀瀾在序言中云:「自留美歸國,奔走四方,於茲三十六年,駸駸日老,逐逐仍勞,所感所見,可歌可泣,興之所至,率筆及之。」雖是如此,但他對於這些憶往的文章,特別強調是「事存真相,不加渲染」,因此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當為治史者所重視。薛觀瀾又云:「體裁廣泛,隨筆所之,要以風俗掌故為經,戲劇奕棋體育音韻為緯,凡此國粹攸關,非小道也。」這是就其內容而言,它包括政治歷史以及戲劇圍棋等等,今為讀者閱讀之方便,特分為《北洋政壇見聞錄》及《薛觀瀾談京劇》二書,此在其生前均未曾出版過,有幾篇文章還是他去世後以「遺著」而發表者。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歷史人物 |
$ 306 |
中國歷史 |
$ 306 |
社會人文 |
$ 306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
☆穿梭近代人物史料的最佳入口:精選文史學者蔡登山針對四十本重要近代史著作量身打造的導讀文章,並附上四十本重要近代史著作的全彩書影,帶領讀者認識梅蘭芳、袁世凱、黃旭初、杜月笙、汪精衛、戴笠等近代人物著作的史料價值!
☆近代史是朦朧的,如真似幻,我們需要更多的史料,更多的歷史碎片,才能拼出一幅幅的圖景。──蔡登山
【40本珍貴近代人物史料的完整導讀,考證生平資料、詳述歷史貢獻】
北洋軍閥袁世凱
上海大亨杜月笙
新桂系大管家黃旭初
在蔣介石與汪精衛身邊的要員臧卓
汪精衛姪兒汪希文 宣傳部長趙叔雍
孫中山的左右手朱執信與胡漢民
戴笠與十三太保
戲曲大師梅蘭芳
話劇先驅歐陽予倩
京劇老生首席余叔岩
民初報壇變色龍薛大可
京劇評論家薛觀瀾
吳國楨事件解密
民初大記者徐彬彬
著名報人張慧劍、陳定山
詞學大家況周頤 民初詞人汪東
慈善教育家毛彥文
詩壇才子王揖唐
史料翻譯家王光祈
作者簡介:
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與《楊翠喜‧聲色晚清》等十數本著作。
章節試閱
【大時代的見證:黃旭初和他的五冊回憶錄】
黃旭初(一八九二~一九七五),廣西容縣人。係廣西省政府主席,主政廣西近廿年。黃旭初年十六入容縣師範,二十歲肄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與李宗仁有同學之誼。一九一四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中國陸軍大學學習。一九一七年,任廣西陸軍模範營連長,保定軍校畢業的黃紹竑、白崇禧任副連長。一九一九年由湘歸任廣西陸軍第一師步二團團附。一九二一年六月,調任廣西督軍署中校參謀。一九二三年擔任李宗仁的「廣西定桂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六年北伐軍興,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黃旭初(一八九二~一九七五),廣西容縣人。係廣西省政府主席,主政廣西近廿年。黃旭初年十六入容縣師範,二十歲肄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與李宗仁有同學之誼。一九一四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中國陸軍大學學習。一九一七年,任廣西陸軍模範營連長,保定軍校畢業的黃紹竑、白崇禧任副連長。一九一九年由湘歸任廣西陸軍第一師步二團團附。一九二一年六月,調任廣西督軍署中校參謀。一九二三年擔任李宗仁的「廣西定桂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六年北伐軍興,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代序
蔡登山
在近代史中,晚清以降至民初,雖然最接近我們的,但其實那只是時間上的距離,而事實上這段歷史是最為朦朧不清,可謂「雖近實遠」。究其原因,除了時代的動亂外,還有許多人為的扭曲、竄改、隱諱等等因素,再加上許多政治的因素,諸多檔案無法開放,也導致研究人員無法深入事件其中做進一步的研究。
我也常常陷於這種不得其門的窘境,於是數年間在幾個大型的圖書館尋搜,希望能找到一些線索。翻遍許多昏黃的老雜誌及報紙,先從香港的《春秋》、《大人》、《大華》、《掌故》到香港的《天文臺》...
蔡登山
在近代史中,晚清以降至民初,雖然最接近我們的,但其實那只是時間上的距離,而事實上這段歷史是最為朦朧不清,可謂「雖近實遠」。究其原因,除了時代的動亂外,還有許多人為的扭曲、竄改、隱諱等等因素,再加上許多政治的因素,諸多檔案無法開放,也導致研究人員無法深入事件其中做進一步的研究。
我也常常陷於這種不得其門的窘境,於是數年間在幾個大型的圖書館尋搜,希望能找到一些線索。翻遍許多昏黃的老雜誌及報紙,先從香港的《春秋》、《大人》、《大華》、《掌故》到香港的《天文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多少樓臺煙雨中:近代史料拾遺代序
大時代的見證:黃旭初和他的五冊回憶錄
袁世凱女婿薛觀瀾及其著作─《我親見的梅蘭芳》、《北洋政壇見聞錄》、《薛觀瀾談京劇》
薛大可和他的《憶往錄》
商界奇人李晉(組紳)和其《政壇見聞錄》
掌故大家徐彬彬和《凌霄漢閣筆記》
給您一個真實的杜月笙─《上海大亨杜月笙》、《上海大亨杜月笙續集》編後記
杜月笙秘書─胡敘五其人其書
汪精衛姪兒汪希文回憶錄:《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
《孫中山的左右手:朱執信與胡漢民》及其作者
《戴笠與十三太保》編後記
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
趙...
大時代的見證:黃旭初和他的五冊回憶錄
袁世凱女婿薛觀瀾及其著作─《我親見的梅蘭芳》、《北洋政壇見聞錄》、《薛觀瀾談京劇》
薛大可和他的《憶往錄》
商界奇人李晉(組紳)和其《政壇見聞錄》
掌故大家徐彬彬和《凌霄漢閣筆記》
給您一個真實的杜月笙─《上海大亨杜月笙》、《上海大亨杜月笙續集》編後記
杜月笙秘書─胡敘五其人其書
汪精衛姪兒汪希文回憶錄:《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
《孫中山的左右手:朱執信與胡漢民》及其作者
《戴笠與十三太保》編後記
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
趙...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