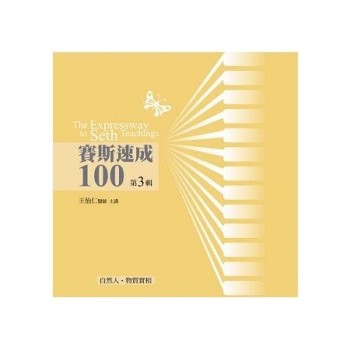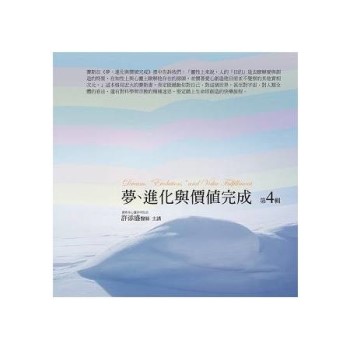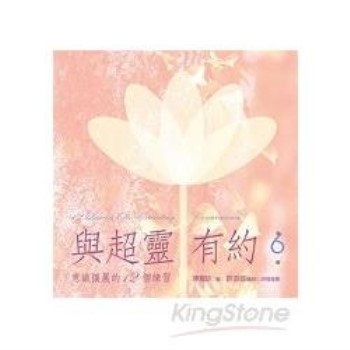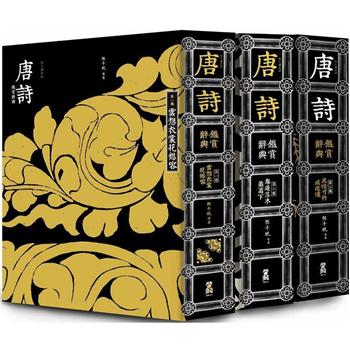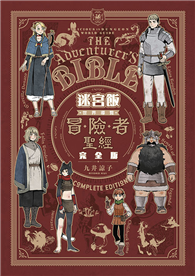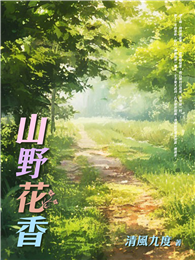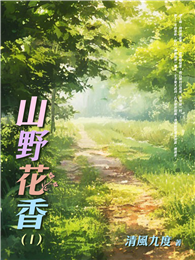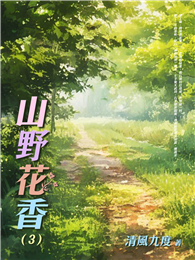中國人的生活變化,應了鄧小平的名言,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從小貨車到寶馬、從膠袋到LV,外國名牌俘虜了國民的心,支撐着他們對「中產」這個新階級的身份認同;以往封閉的門戶開通了,他們能周遊世界揮金如土,更能告別故里移民他鄉,一切看來都像一個新世界。但是,改變未必都是美好的。奇怪的食物添加劑威脅健康,因資源爭奪而致的育兒壓力折磨父母,文明進步的背後總是會發生問題。於是有人主張告別繁忙與壓力,重新過種花喝茶的懶人生活;也有人鍾情於網絡世界的罵戰,發洩滿腔積怨,或者只是圖個過癮。
這是一場「小」革命,一場生活的革命。
「他們既沒有西方貴族的族,徽甚至都沒有像樣的家譜──在這個消費時代,Logo的力量幾乎等同於身份證同。」
「住在城裡還是郊區,買精裝修的房子還是自己動手,現在,決定這些事情的已經不再單純的是你能兜裡掏多少錢,而在於你想選擇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系列:
《三聯生活周刊》創刊至今逾十五年,而近十五年,恰好是中國發生最大變化的時期。我們從這十五年的封面故事中精選具代表性的文章,分門別類出版,讓讀者回顧中國的變化。
繼《邵氏光映系列》、《號外三十》、Modern China系列(《周末畫報》、《生活》和《新視綫》精選文章結集)後,三聯書店又一次出版當代中國具影響力的刊物叢書。
作者簡介:
《三聯生活周刊》創刊於1995年。這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讀書》月刊後出品的又一份重量級雜誌。從構思、試刊,到正式創刊,直至今天它成為中國內地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之一,眾多當代中國文化界、傳媒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曾與這份雜誌有過或淺或深的交集——董秀玉,錢剛,楊浪,朱學勤,胡舒立……真正在十五年時間裡決定了這份雜誌核心價值與外在氣質的人,是主事者朱偉和潘振平,以及一眾不可多得的主筆:方向明,胡泳,苗煒,舒可文,李鴻谷,王小峰,以及更多年輕、獨立、富有才華的記者。
《三聯生活周刊》:
《三聯生活周刊》的前身為鄒韜奮先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創辦的《生活周刊》,1995年由三聯書店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於北京復刊,其定位是做新時代發展進程中的忠實記錄者:力爭以最快速度追蹤熱點新聞的前提下,更多關注新時代中的新生活觀,「以敏銳姿態回饋新時代、新觀念、新潮流,以鮮明個性評論新熱點、新人類、新生活」。
章節試閱
從「打折年」到「倒閉年」到「批發年」消費平淡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末中國經濟的「一塊心病」。
從生產不足到流通「瓶頸」,再到消費「掉鏈子」(編按:跟不上),我們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消費時代。面對陌生的難題,面對陌生的時代,舉國上下殫精竭慮地刺激消費,提前消費,但為什麼始終啟動不起來?
有人說,只有當真正的中產階層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佔紡錘形的多數時,
我國的市場經濟信用消費才能建立起來,消費和市場才會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但我們能否容忍忙於購買和還債的日子?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可能出現佔人口多數的中產階層嗎?對消費的重新認識使我們正試圖仿效美國式的消費經濟模式,可消費必然以消耗資源為代價。中國的發展靠的是徹頭徹尾的自我資源資本化,為了追求注定沒有盡頭的物慾生活,我們是否真要陷未來於貧困之中?
在激情的消費時代,喜劇離我們很近很近,悲劇卻離得很遠很遠,遠得可能我們一輩子都看不見。但它確實在那兒。
消費「掉鏈子」
清晨8 : 35,一名中年女店員從地鐵站上來,拚命地朝達處張燈結綵的北京翠微大廈跑去,大廈前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上千號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人群,她要在忙碌中度過這1999年的第一天了。9 : 00,翠微大廈開門營業。人群也開始騷動,但卻沒有一個邁進富麗堂皇的商場大廈,而是潮水般向門前那一排福利彩票發售窗口湧去,在大廈裡,店員們高興地等待著,他們相信,那些乘興而來的摸獎者一無所獲後,終將會進來把兜裡剩下的百元大鈔花費掉。
他們後來不得不承認自己想錯了。翠微大廈業務部的敖鐵林告訴記者,元旦那天商場裡的客流量確實增加了一倍多,營業額卻只有 359 萬元(人民幣,下同) ,只相當於平時雙休日的水平。敖鐵林很懷念一年前商廈剛開業時的火爆場面,他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老百姓寧可拿幾百塊錢摸回一個劣質鋼精鍋,卻不捨得到商場裡一分錢一分貨地買東西呢?」
日子不好過的並不僅僅是一個翠微大廈,1月19日,北京市商委公佈了1998年全市109家大中型零售商場的經營狀況:
30家虧損,19家不賠不賺,其餘60家共計盈利6.86億元,利潤率也僅是2.93%比1997年還少了0.57個百分點.市商委新聞發言人張秋白說,連鎖超市和一些歷史較為悠久的中檔商場尚能微利經營,近幾年新閒業的豪華商廈則「基本上都是虧損」。慘淡的愁雲將那些光裝修就花去上億元的大商場壓得欲哭無淚。
以至於朱鎔基總理在1998年10月「5,000人吹風會」上半開玩笑地拜託與會代表們到京城的商場裡多買點東西帶回去,在如此的大環境下,似乎已經沒有誰能得以幸免了。1998年8月15日,自八十年代以來風光無限的鄭州亞細亞商場被債主封門,10月9日,以引領現代家居新時尚為鮮明特色的北京海藍雲天商城開業不足一年便敗走北京朝外大街。僅過了一個月,北京又一大型貴族商廈「萬通新世界」在苦撐三年後也不得不黯然凋謝。來自內貿系統的消息說,全國二百多家大型零售商場1998年1至11月的利潤總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4 %,平均利潤率不足3%,據在各地擁有37家成員單位的華聯商廈集團統計,銷售總額少了9.6%,利潤也下降了1/2。
曾立志要建成全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帝國的「亞細亞」更慘,從天津到廣州、從河南到北京,幾乎是轉眼間就呼喇喇全線崩潰。國家內貿局商業信息中心總工程師王耀透露,1998年全國國有商業企業「有1/3虧損」。
1/3虧損,對中國商業來說,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紀綠。自建國初期開始, 四十多年的輝煌,創造了一個行業「只賺不賠」的世界級神話。八十年代舉國上下的百貨商場裡更是一片「人流如織,購物如潮」的喜人景象。售貨員的月收入比大學教授還要高出好幾倍,即使是九十年代經濟疲軟時期,中國商業也取得了高速度成長,事實上,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大批比著上規模、上檔次、上豪華的大商場開始簇擁追逐著在各地拔地而起。
「當時真正疲軟的是工廠,產品積壓賣不出去;而商業網點卻還很少,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可以大搖大擺地賒賬銷售,所以商場是開一家賺一家,」商業信息中心預測處處長郭守中分析道,八十年代以前,生產是經濟鏈條中最重要的環節,進入九十年代,流通和銷售成了最稀缺的「瓶頸」資源。「現在終於該輪到消費了」,郭守中說。
為了讓消費者掏錢,商家一再忍痛「祭起」降價法寶。整個1998年,北京各大小商場從節日降價到店慶降價, 直至沒有任何理由地「大派送 」、「大甩賣」, 在武漢,由於競相殺價已到了血本無歸的地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但就在1999 年1月17 日降價狂潮被亮「紅牌」的第一天,武漢幾家知名大商場仍然打出了 「買什麼送什麼」「買多少送多少」的顯眼條幅。
然而實踐已經證明,降價並非吸引顱客的「至尊法門」,有分析者認為是消費者「買漲不買落」的心理作用,但不管怎樣「跳樓大甩賣」 已沒了早年一呼百應的號召力。眼看著批發市場還算紅火,商場倒閉浪潮又演化成了批發大戰。 1 月 15 日,擁有豪華裝修、中央空調和18部滾動電梯的萬通新世界商品批發交易市場開業頭一天,一位花11萬元押金租了兩個化妝品攤位的小貨主就告訢記者,他已準備私下裡轉租出去一個攤位,且「條件優惠」;月租 3,200 元,不要一分錢押金。
不光是大小商家老闖在著急上火, 1998 年 12 月 22 日召開的全國電子工業經濟工作會讓上,信息產業部責怪彩電和 VCD的價格戰使行業全年「 至少減少利潤 100 億元」,其中彩電降價約減少利潤 52億元。轉過年來,國家機械總局自豪地宣佈,1998年國內轎車產量超過65萬輛,平均每小時有 74輛國產轎車開出生產線。 但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買主,每小時生產 74 輛轎車又有什慶用呢?
機械總局汽車行業管理處處長李萬里承認,轎車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差額有擴大的跡象,1998年國內車市需求55萬輛,過剩至少10萬輛;1999年預計產能達到75萬輛,需求估計在63萬輛左右。
「即使這銷出去的 55 萬輛轎車已經很出人意料了。」北京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的經理戴建說,他們市場 1998 年原預計銷售量在 25 , 000 輛,實際已突破40, 000輛,是建市以來生意最火爆的一年,究其原因有二:從年初非 2000 型「桑塔納」單車價格降至11.2 萬元開始,國產轎車全部加入降價戰團,降價5,000 至 20,000 元不等;到年頭,由於非電噴轎車即將停止上牌,搶購化油器車的熱潮驟起,亞運村市場日銷量達到創紀錄的四百多輛,但轉過年來,短暫的繁榮一落千丈,素有北京車市晴雨表之稱的亞運村市場又創下了日銷 1 輛車的最低紀錄,據戴建介紹,1999年1月1至 12日,「亞運村」共售出轎車282輛,而1998年同期的銷量是1,000輛。交易市場已將1999年的銷售目標定為 25 , 000 輛至 30,000 輛左右,比 1998 年下調了 20 %,僅次於「亞運村」的北方汽車交易市場境況更為不佳,1 月的銷量只有去年同期的 1 / 10 ,因此他們也更為悲觀, 預計 1999年全北京汽車銷量將下降五成以上。北京車市的銷售量可以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左右。
1998 年 12 月 30 日,國家統計局宣佈了當年的宏觀經濟主要指標:工業增加值漲8.8 %,社會商品零色總額漲 6.8%,商品零售價格跌 2.6 %,居民消費價格跌 0.8%,另一個被廣泛引用的宏觀數字是,全國物價總水平從 1997年10 月至 1998年12月,已經連續 15個月低於上年同期。 供應充足,價格低迷,消費不振,是經濟界對當前國內經濟的共識 ,也是每一個消費者都能感受到的事實:商場上的貨架塞得滿滿的,人民幣也變得很值錢,可錢包就是揣得緊緊的。
滿大街地尋找消費
國家內貿總局商業信息中心每半年都要對市場上主要商品的供求情況進行一次排隊,這是這家機構從計劃經濟時代沿襲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傳統之一。1997 年底的排隊結果是,供過於求的商品佔 31.8 %,供求平衡的佔 66.6 %,供不應求的有 10 種,佔 1.6 %。
一年之後再次排隊,供不應求的只剩下 1 種,主要依賴從印尼進口的棕櫚油。記者問這棕櫚油是幹什麼用的,信息中心的郭守中處長笑著說:「是炸方便麵用的。」
形形色色的商品生產出來賣不出去,內貿總局感覺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 1998 年 10月,原內貿部部長陳邦柱在部份省市商品流通工作座談會上一再給老部下打氣,強調要發展新的消貧熱點,積極研究「擴大消費、刺激消費、鼓勵消費」 的政策措施。1998 年 12 月 9 日,辭舊迎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擴大內需、以消費拉動國民經濟增長被寫入了新華社會議通稿,這是近十多年來中央第一次把消費提升到如此戰略性高度。八十年代中期,消費問題曾在中國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鼓勵消費」的提法被指責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消費經濟思潮」,消費被認為是不創造價值的「生活的需要,生產的末節」。不料於不經意之間,消費最終又成了社會再生產的目的與歸宿,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 1998 年底完成的一份形勢分析報告以雄辯的材料證明,「 20 年來,經濟政策與居民最終消費結合最緊密的時候,也就是經濟實現高速健康增長最快的時候」。宏觀經濟學家們指出,目前(1998年)我國最終消費裡居民消費佔81%左右,過去 20年中,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又一直在 60 %上下,居民消費每增長 1 % ,可帶動 GDP 增長約 0.5 % ,所以,「消費這『 頭駕馬車』能否跑得歡,於民眾關係到自身的就業機會與收入增長,於企業意味著擴大再生產能否順利進行,於國則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和 GDP 的穩步增長」。
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證是住房,根據世界銀行和深圳市的抽樣調查,每銷售 1 億元的商品房,可誘發 1.3 至 1.5 億元的住宅商品銷售,而住房建設每投入 1 億元,可創造建材、冶金、機電等相關上萬種產品 1.7 至 2.2 億元的需求,另外,住房建設每吸納 100 人就業,又可帶動相關行業提供 200 個就業機會。此一時,彼一時,經濟界話語的朝秦暮楚不過是中國經濟從短缺到過剩這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但僅有個說法顯然還是不夠的,啟動消費談何容易。
第一個出場的是降息,這是國際通行的法寶。從 1996 年 5 月到 1998 年 12 月 7 日,中國人民銀行 31 個月內連續 6 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 9.18 %一路降至 3.78 % 。如此密度和力度建國以來前所未有,但結果有目共睹。銀行裡的儲蓄存款反而從 3 萬億元一路飄升到 5.3萬億元。 1998 年 7 月 1 日銀行第 5 次降息的時候,工商銀行天津和平支行的蔡之良發現,整個 7 月份的居民存款淨增額相當於前 6 個月的總和,這位愛好寫作的銀行職員在天津人行的內部刊物上發表的處女作題目就是 《 利率跌半,存款狂增 ─ 儲蓄依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 4 個月後,人行宣佈第 6 次降息,當天滬深股市即縮量下跌。運用利率槓桿刺激消費的第一板斧以失敗告終。政府隨即走出雙管齊下的第二步棋 ─ 一方面擴大財政赤字,由國家投錢帶動民間游資,另一方面集中改革一批抑制消費的政策規章。 1999 年 1 月 14 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透露, 1998 年度國家赤字近 960 個億,共發行國債 5,900 億元,成為建國以來發行國債最多的一年; 1999 年計劃再發國債 3,165 億元,預計赤字 1 ,053 億元。與此同時,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向國務院送呈 《 國家行政機關收費管理條例 》,據計委價格司收費管理處許昆林處長介紹說,這次改革建議取消 48 種不合理收費,另有近三百種改為服務價格。儘管許昆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沒有透露一些民怨沸騰的收費是否屬被取消之列,但國家技術監督局已經證實,剛剛劃歸他們管理的電話計費辦法將改「按分計費」為「按秒收費」。建設部房地產司司長謝家瑾也告訴媒體,有關方面希望 1999 年將上海試行的購房減稅政策推向全國。各種不大不小的好消息還在不斷傳來:國家稅務總局已透出口風,證券交易稅、遺產稅和新的消費稅近期估計都不會出台; 1 月 8 日,廣東省物價局和公安廳宣佈將原來的 46 項車輛交通管理收費減為 5 項。「國家正在盡力做所有它能在較短時間內做到的事情。」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楊聖明研究員認為,通過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連鎖拉起內需,這是一種大膽而積極的做法,而為個人消費清除行政障礙、創造寬鬆環境更是題中應有之義,「私人買車要交 2 萬元牌照費、2,000 元佔地費、1萬元城市增容費這種短缺時期 『劫富不濟貧』 的限制早就應該取消了」,楊聖明說。
但楊聖明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樂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是長久之計,中央財政赤字也不能年年增加。錢花出去了還不見效果怎麼辦?再出現通脹危機怎麼辦?」他反問道。
而且消費不消費是老百姓的事,把存款利息壓低 2 / 3 撼不動。「我以為,研究刺激消費必須研究消費者心理。」楊聖明說,「老百姓是有錢不敢花,在滿是變量的轉軌期,每個人都想為將來留一手,你再引誘也是枉然。」
楊聖明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國家信息中心的贊同。該中心消費需求課題組在一份專題報告中將居民的消費行為與心理歸納出三大特徵。第一,由於近年來收入增幅連續下降和巨大的失業壓力,居民未來預期收入下降;第二,醫療、養老、住房和教育體制齊頭並進的改革,使未來預期支出大幅上升;第三,對未來強烈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引起消費行為的過度反應。這家副部級的經濟諮詢機構在報告中認為,由於歸根結底是「轉型期問題」,所以根本上解決「有待於經濟景氣的好轉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健全」。
這是國內可以聽到的最為無奈因此也最為悲觀的分析預測。比這讓人放心的也有。一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正處在兩次消費高峰之間的平緩斷代區,悲觀點兒講就是沒有消費熱點,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幾乎是商品空白, 86 %的居民在購齊了千元級耐用消費品以後,只能把月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存入銀行,所以當務之急是發掘出萬元以上新的熱點。著名經濟學家薰輔扔教授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認為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增加收入,因此建議盡快將現存的一些實物型待遇貨幣化,盡快形成一批中產階層。「這些不同意見我都同意。」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范劍平研究員創造性地用一個詞把它們統一了起來 ─ 時間不對稱。「萬元以下的耐用消費品普及以後,應該說還是有新的需求的,尤其是住房和汽車。但它們都是價值十幾萬、幾十萬,大部份人想購買只能花一輩子時間去儲蓄,消費行為必然後仰,可是數以百億計的生產貸款又使供給前傾,等消費者攢夠錢了,汽車廠和房地產商早就餓死了。」
范劍平寄望於國家盡快使出「第三板斧」。記者問他心中的「第三板斧」是什麼,范劍平毫不猶豫地說是全面推行信用消費。「簡單地講就是鼓勵消費者 『 寅吃卯糧 』 提前享受消費。」范劍平稱,近一年來 ( 1998 年 )國家的政策傾向可以明顯看出對透支性消費正從寬容到縱容,「但僅此還不夠,我們必須打破短缺時代的落後消費觀念和對消費的偏見。」他說,信用消費可以輕易解決制約消費購買的時間差問題,「理應大張旗鼓地鼓勵和宣傳」
從「打折年」到「倒閉年」到「批發年」消費平淡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末中國經濟的「一塊心病」。從生產不足到流通「瓶頸」,再到消費「掉鏈子」(編按:跟不上),我們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消費時代。面對陌生的難題,面對陌生的時代,舉國上下殫精竭慮地刺激消費,提前消費,但為什麼始終啟動不起來?有人說,只有當真正的中產階層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佔紡錘形的多數時,我國的市場經濟信用消費才能建立起來,消費和市場才會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但我們能否容忍忙於購買和還債的日子?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可能出現佔人口多數的中產階層嗎?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