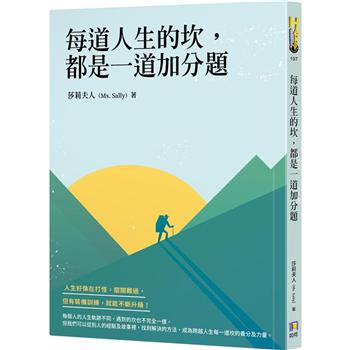序
研究者的冷靜與崇拜者的熱情/羅展鳳
每次指導同學做學術論文寫作,我多著他們從兩個方向出發:選擇當下感興趣的題材,或選擇多年來喜愛的題材。通常選擇前者的同學較多,後者較少,本書作者吳子瑜則屬於後者。
幾年前,子瑜充滿喜悅地告訴我想做有關楊千嬅的研究,原因是楊千嬅是他多年來的偶像,當得知有「明星研究」理論,他便二話不說,想借用來分析楊千嬅如何在其歌影作品呈現多變又統一的矛盾形象。我看見他雀躍欣喜的研究熱誠,就大力度鼓勵,來個順水推舟;畢竟,同學能夠有著這種從心而發的喜樂去開始研究,並不常見。最後,看他在研究中洋洋灑灑地把楊千嬅拉到方麗娟、說到余春嬌,談本色形象,又聊到倔強單純少女如何落入凡間變成世故港女剩女,就相當好玩。
記得有次閒聊,聽到子瑜說起他當年認識楊千嬅的小故事──某個農曆新年,小學生的他拿著利是錢到地鐵站的地利店購買楊千嬅的第一張細碟,傻呼呼地就是被唱片封面吸引過來,我的腦海立時想像當年小男孩的子瑜如何從一次偶然─從此對楊千嬅展開「萬劫不復」的欣賞─爾後,他從不錯過楊千嬅的每張唱片、每部電影乃至每場演唱會,更收藏有關她的報道,回頭一想,有什麼比從小喜歡的偶像一天成為自己研究的對象來得快慰?當理性的研究遇上感性的情懷,建立屬於研究者冷靜與崇拜者熱情的距離,過程中大抵也有夾雜著雙重的刺激與欣喜,這點,想子瑜最明白。
全書分兩部份:楊千嬅的歌與影。延續「明星研究」理論在楊千嬅的電影形象探討,子瑜在修讀碩士過程中繼續他在楊千嬅的流行歌曲上的研究,以楊千嬅為作者中心,從其早年的流行曲開始著手,到不同時期的演變,試圖接連歌手與作品之間千絲萬縷的「自我對話」關係,勾勒出這位自1990年代中出道的女歌手如何在有意無意間被建構或主導有關其作品的創作,甚至製造一種「自我調適」的明星特質,當中夾雜著不少社會文化與性別意識;明顯,多年來子瑜集中以「明星研究」來細讀楊千嬅的電影與音樂之發展脈絡,箇中自有趣味獨特之處,對「明星研究」亦備參考作用,加上當中不乏側寫楊千嬅作為演員與歌手的創作與生命成長之路,又是另一層次有趣的微觀閱讀,粉絲自然看得入心。
至於我,今天實實在在捧著子瑜的這本書,是真的為他滿心歡喜。
羅展鳳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