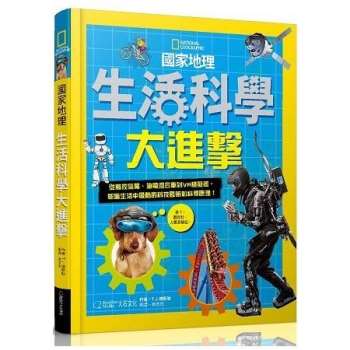經濟高度成長的年代,科學至上的時代精神,理性進步的歷史觀,舊時代的迷信一掃而空。曾經,人們活在被狐狸戲弄的精神世界,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之下,那個世界成為一段幽微不可見的歷史。過去我們與自然一體共存,現在它成為我們功利衡量的客觀存在。生活在我們身邊、那些曾經欺騙過先人的動物,我們必須重新確認與牠們的關係,以此認識自身的存在:自然觀、生死觀、人觀。
日本地方創生的重要思想源頭,哲學家內山節邀您一起探索時代的現象與精神世界。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日本人為什麼不再被狐狸騙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中文書 |
$ 253 |
東方哲學 |
$ 288 |
當代思潮 |
$ 288 |
社會人文 |
$ 288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日本人為什麼不再被狐狸騙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內山節(UCHIYAMA Takashi)
一九五○年生於東京,東京都立新宿高校畢業。
哲學家。在群馬縣上野村與東京兩地生活,同時在立教大學、東京大學等校執教。
著有《通往森林的路》、《貨幣思想史》、《「里」之思想》(以上由新潮社出版)、《戰爭這種工作》(信濃每日新聞社)、《哲學的冒險》(平凡社)、《共同體的基礎理論》等(農山漁村文化協會,中譯書名皆暫譯)。
著述豐富,二○一六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內山節著作集》共十五卷。
譯者簡介
秦健五
Uber司機,兼職文字工。
內山節(UCHIYAMA Takashi)
一九五○年生於東京,東京都立新宿高校畢業。
哲學家。在群馬縣上野村與東京兩地生活,同時在立教大學、東京大學等校執教。
著有《通往森林的路》、《貨幣思想史》、《「里」之思想》(以上由新潮社出版)、《戰爭這種工作》(信濃每日新聞社)、《哲學的冒險》(平凡社)、《共同體的基礎理論》等(農山漁村文化協會,中譯書名皆暫譯)。
著述豐富,二○一六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內山節著作集》共十五卷。
譯者簡介
秦健五
Uber司機,兼職文字工。
序
前言
過去我不論走到哪裡,身上總是帶著釣竿。就算旅行的目的並非釣魚,我的包包裡還是會放著釣竿,等辦完正事之後,再就近探尋山女魚或岩魚棲息的河流。
我曾在許多村落投宿,也寫過一本名為《山里釣魚紀行》(一九八○年)的書,那已經是超過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與其說是熱衷於釣魚,不如說我喜愛在溪流流經人們所聚居之處,也就是「里」這樣的地方,朝溪流伸出釣竿,一邊欣賞田園與人家交織的景色,一邊釣著魚。我釣魚可以說是在「山里的釣魚」,而非在「溪流的釣魚」。傍晚時分,我便就近尋找投宿地點,有時在溪邊認識的村民會邀請我到他們家裡作客,有時會聽聽坐在田邊的村民閒聊。最近我比較少把魚竿放在包包裡了,這是因為我住到群馬縣一個叫做上野村的山村裡,待在那裡的天數差不多和我待在東京的天數是一樣的。上野村也是我在一九七○年代之初,因為釣魚而造訪的一個村子。
住在山上,經常可以聽到以前的人被狐狸戲弄的事,因為太常發生,可以說是稀鬆平常的事。不只是狐狸,包括狸貓、狗獾甚至是鼬鼠,都會戲弄人,而且是時常發生的事情。
然而進一步詢問,會發現那些都是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以前的事,到了一九六五年之後,曾經多不勝數的狐狸戲弄人的事,在日本社會中就不再發生了,而且幾乎是全國一致。
這究竟是為什麼?這本書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為什麼自一九六五年起,狐狸戲弄人的故事就不再發生了?日本社會在一九六五年時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呢?我希望能嘗試解答這些疑惑。
本書作為我個人的企畫,有著「歷史哲學序說」這樣的子題。這是因為在反覆探問為何人們不再被狐狸戲弄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一些課題,那就是一直被狐狸戲弄的自然與人的歷史、村里的歷史、生活在與自然的交流當中的民眾精神史等等。透過這些課題,我面對著一種必要性,那就是重新認識在一般的歷史學之下「看不見的歷史」。歷史是什麼?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考察這個歷史哲學的課題。
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寫成的。曾經,被狐狸戲弄的故事不斷發生的歷史,為何不再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活在什麼樣的歷史世界呢?
希望本書可以為「我們的現在」提供一些思考。
過去我不論走到哪裡,身上總是帶著釣竿。就算旅行的目的並非釣魚,我的包包裡還是會放著釣竿,等辦完正事之後,再就近探尋山女魚或岩魚棲息的河流。
我曾在許多村落投宿,也寫過一本名為《山里釣魚紀行》(一九八○年)的書,那已經是超過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與其說是熱衷於釣魚,不如說我喜愛在溪流流經人們所聚居之處,也就是「里」這樣的地方,朝溪流伸出釣竿,一邊欣賞田園與人家交織的景色,一邊釣著魚。我釣魚可以說是在「山里的釣魚」,而非在「溪流的釣魚」。傍晚時分,我便就近尋找投宿地點,有時在溪邊認識的村民會邀請我到他們家裡作客,有時會聽聽坐在田邊的村民閒聊。最近我比較少把魚竿放在包包裡了,這是因為我住到群馬縣一個叫做上野村的山村裡,待在那裡的天數差不多和我待在東京的天數是一樣的。上野村也是我在一九七○年代之初,因為釣魚而造訪的一個村子。
住在山上,經常可以聽到以前的人被狐狸戲弄的事,因為太常發生,可以說是稀鬆平常的事。不只是狐狸,包括狸貓、狗獾甚至是鼬鼠,都會戲弄人,而且是時常發生的事情。
然而進一步詢問,會發現那些都是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以前的事,到了一九六五年之後,曾經多不勝數的狐狸戲弄人的事,在日本社會中就不再發生了,而且幾乎是全國一致。
這究竟是為什麼?這本書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為什麼自一九六五年起,狐狸戲弄人的故事就不再發生了?日本社會在一九六五年時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呢?我希望能嘗試解答這些疑惑。
本書作為我個人的企畫,有著「歷史哲學序說」這樣的子題。這是因為在反覆探問為何人們不再被狐狸戲弄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一些課題,那就是一直被狐狸戲弄的自然與人的歷史、村里的歷史、生活在與自然的交流當中的民眾精神史等等。透過這些課題,我面對著一種必要性,那就是重新認識在一般的歷史學之下「看不見的歷史」。歷史是什麼?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考察這個歷史哲學的課題。
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寫成的。曾經,被狐狸戲弄的故事不斷發生的歷史,為何不再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活在什麼樣的歷史世界呢?
希望本書可以為「我們的現在」提供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