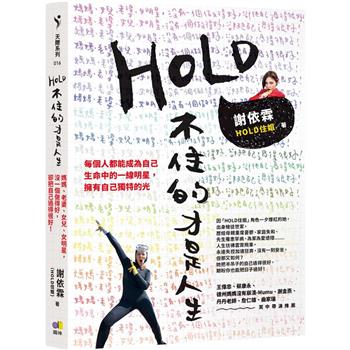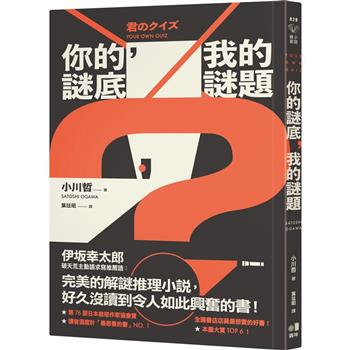導讀╱你從阿富汗來?──二十世紀末福爾摩斯再訪台灣
文/ 唐 諾
「你從阿富汗來?」——這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一八八六年四月誕生於英國所說的第一句話,物件當然就是日後負責記敘他一生行跡並充當他探案助手的約翰•華生醫生。
彼時華生醫生方由阿富汗戰場負傷被遣送歸國,想找一處分租的廉價居所,經由朋友介紹,有名怪人亦因房租太高無人分攤而煩惱,兩人遂因此在大學的化學實驗室初次碰了面。這段經過寫在福爾摩斯探案的處女作《暗紅色研究》中;那處分攤的租屋則是攝政公園旁、往後偵探小說世界最重要的一個住址:倫敦市貝克街二二一號B座。而「你從阿富汗來?」這石破天驚的典型福爾摩斯首次推理,也成為一百五十年推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定場辭。
以上有關福爾摩斯出生所說的第一句話,是國內推理小說傳教士詹宏志介紹福爾摩斯時的習慣開頭方式,由於此番臉譜出版公司重譯重製福爾摩斯全集的原始構想始於詹宏志,因此,這篇介紹文字亦沿用詹先生的典型說法以為開始。
我從海上來,帶回來航海的二十二顆星。
你問我航海的事兒,我仰天笑了──
然而,我們此番重看這部《暗紅色研究》很容易發現,彼時正為著成功找到新化學試劑而雀躍不已的這名神探,他的首度發言其實並沒有如此深沉睿思的況味,而是有點神經兮兮地從實驗桌前跳起,不僅沖過來,手中還抓著一支試管。「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發現了一種試劑,只能用血蛋白來沉澱,別的都不行。」──感覺上比較像被卡通化的愛因斯坦式的瘋子科學家。
但仔細想想,如此較不偉大的出場方式也很好不是?起碼更接近一般人生真相不是?畢竟,彼時的年輕福爾摩斯即使再有自信,應該還是不至於知道在未來的四部長篇加五十六個結集短篇探案之後會成為歷史上神探的代名詞;而同樣也還年輕的亞瑟•柯南•道爾(時年二十七而已)亦不會知道他筆下正創造一個超越愛倫•坡的杜賓和威基•柯林斯的霍夫警官的偉大神探,正如同人們尋到巴顏喀喇山源頭的小小滴水之處,會很難想像這居然孕育出長達五千公里的壯闊長江黃河一般,人類歷史的先驅一般總是這樣子沒錯;而且想想看,一個從小就知道自己未來會是個偉人,也因此分分秒秒都緊端著偉人架式的人有多虛偽多可怕不是嗎?
不管怎樣,福爾摩斯開始了。
一個已停止供應的人種
有關福爾摩斯(或寫他的柯南.道爾)有多重要、多偉大,這已是常識了,不待多言。這裡我們只說,他在人類歷史裡歸屬於一個古老、人數不多、而且今日世界已然停止供應的職位或說人種,名單大致是:巴哈、米開朗琪羅、愛因斯坦、亞當•史密斯、達爾文和邁克爾•喬丹(他極可能搶下了最後一個名額)云云。
我們很難簡單為這樣一群奇怪的人命名:他們通常代表著自己的那一行業,即使不是原始的開創者,也必定是最重要的奠基者,但事情不只是這樣,相對于其他較平凡的行業奠基者,這一小群人常常莫名其妙地「嚴重」擴張開當時歷史條件所允許的規格,超越了既有的歷史條件限制,而使他們的成功有著某種匪夷所思、甚至「不像人」的神采,像一種奇跡──我們就以愛因斯坦為例,前蘇俄一位重要的物理學者曾把物理史上的偉大人物分為四個等級,級數越低,其成就和重要性便越驚人,其中愛因斯坦被單獨列為〇等,理由便在於,像量子論的發現,有客觀的物理學進展為基礎,即使沒有當年普朗克那臨門一腳,短則數年,長則十年,也一定有其他物理學家會提出來;相對論不同,這是由「一個偉大的天才不可思議地想出來的。」
這一小群人,你不見得會最喜歡他,因為喜歡不喜歡有著因緣,有歷史的隨機性,比方說不少人喜歡雷蒙•錢德勒和他筆下的菲力普•馬羅遠勝於柯南•道爾和他筆下的福爾摩斯,正如不少人毋寧更喜歡壯烈深沉而且音符常帶感情的柴可夫斯基而不是巴哈,但你仍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是這個行業中的真正天下第一的人,你甚至可以討厭他恨他,但你絕對不能無視於他巨大而且無所不在的存在。
而由於這一小群人的存在和成就距離我們今日往往有相當一段時日了(邁克爾•喬丹仍是唯一的例外)。在江山代有才人、後代傑出人物有機會站在他們肩上看世界的狀況之下,這一小群人亦難免有過時甚至被取代的危機出現。像亞當•史密斯或達爾文,社會主義思潮的蔚然成風和凱恩斯一般理論的出現,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演化論的誤解和誤用,一度曾令這兩個偉大的名字黯然乃至於成為某種程度的髒名詞。然而,真正厲害的也正在於此,當二十世紀後半葉人們逐步發現凱恩斯的理論無法解釋並對付不了經濟實況,市場機能遠比人們所想像的精微奧妙;當人們進一步探入基因這個攜帶遺傳密碼的小小世界,重新思索生物傳種演化的秘密,我們才又一再地驚喜發現,史密斯和達爾文的洞察力、穿透力、理論延展力和他們可怕的預言的啟示能力。
時間,對這一小群人而言,仿佛並不構成威脅,而且,仿佛還真需要一點時間,我們才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真正價值和邊界。
討厭福爾摩斯的人
如同正面攻打一座堅固如金湯的城一般,要從頭一件一件交代福爾摩斯的「功勳」,無疑是太浩瀚不切實際的工程,這裡,請容我們倒行逆施一下,借用科學主義者卡爾.巴柏著名的「否認」概念,來看看歷史上真正討厭福爾摩斯的人及其理由。
老實說這不多,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美國的推理評論家海克拉夫(Howard Haycraft),他說福爾摩斯小說「全都有太鬆散、太明顯、太不原創、太平庸,而且詭計和主題一再重複等等毛病」。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可以先把答案給擺這兒:海克拉夫的嚴厲指控,熟讀福爾摩斯小說的人都清楚他的矛頭指向哪篇小說或哪個段落,也可以同意並非無的放矢,但絕大部分仍不是真的。
事實上,海克拉夫並不能算歷史上最討厭福爾摩斯的人,他頂多排第二,真正的冠軍不是別人,正是福爾摩斯的創造者且因他而功成名就甚至封爵的柯南.道爾本人。柯南•道爾從一八八六年《暗紅色研究》以來,並沒把這位老鷹一樣長相的聰明神探當回事,而且隨著福爾摩斯的越來越成功,越發想擺脫他甚至謀殺掉他,最終得手之後柯南•道爾快樂得不得了,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慶功般寫下「殺死了福爾摩斯」,而且怎樣都不讓他復活。
這樁令全球福爾摩斯迷駭然的公然謀殺發生在一八九三年,長期以來一直心懷殺意的柯南•道爾終於在《最後一案》中,讓福爾摩斯和他的死敵莫里亞蒂教授雙雙跌落瑞士山區的萊辛巴赫瀑布的深淵之中──當然,除了快樂的柯南.道爾本人之外,每個人都極其傷心,包括那些平日不苟言笑的倫敦金融界人士在絲帽上加了黑帶致哀;包括可以想見的讀者抗議信函如雪片湧入雜誌社甚至破口大駡作者「殘忍冷血」;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人更誇張,他們開始集結串聯,成立所謂的「福爾摩斯不死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從芝加哥、三藩市、波士頓等地冒出來,跟真的一樣。
一直抗戰了足足八年之久,也就是一九○一年,柯南.道爾才「看在錢的份上」肯讓福爾摩斯在《空屋》中化妝成老流浪漢回來,這也是後來題名《福爾摩斯歸來記》的第一篇及其得名的理由──已然死過一次的福爾摩斯從此成為一個不死之人,他最後的下場是緩緩退休,不知所終。
柯南.道爾之所以這麼討厭福爾摩斯,用最簡單、其實也是他自己所說的話是,「他妨礙了我做更有意義的事。」──很多人曉得,柯南.道爾是那種超級典型的維多利亞式大英國佬,一生以大不列顛帝國和女皇陛下之榮辱興亡為己任,他的人生有太多「有意義」的事想要做,包括南非的波爾戰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包括國會選舉和國家政策,包括英美兩國未來再結合為世界超級強權,甚至包括英國運動員如何在奧運會拿到好成績云云;而他最想寫的作品,除了晚年傳教式的唯靈論文章之外,出身沒落貴族,從小被他母親灌輸紋章學和歷史故事的柯南•道爾,自認最有動力也寫得最好的一直是騎士型的歷史俠義小說。這些林林總總,我們從這回和「福爾摩斯全集」一起出版的《柯南.道爾的一生》一書皆能清楚讀到。
得稍加說明的是,這本柯南.道爾的一生傳記,寫的人不僅大有來頭,而且是真正的「內行人」。此人叫約翰.狄克生.卡爾,是推理史上大師級的人物,他有個更響亮的名號,叫「密室之王」,理由是他一生數十部推理小說皆至少存在著一個以上的密室殺人概念──當然,這本《柯南.道爾的一生》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儘管這本傳記係以小說的形式表達,而且也包含著死亡,但不是待破的謀殺案,更沒有密室,不知道卡爾寫此書時會不會覺得非常不過癮。
燦若滿天繁星
在福爾摩斯四個長篇和五十六個短篇探案所構成的堅硬盔甲中,若有所謂的裂縫,大概集中在長篇上頭──我想應該不會有錯,以海克拉夫為代表的質疑福爾摩斯的聲音,便集中在這上頭。
真正讓福爾摩斯「偉大」起來的,不是四大長篇,而是那燦若滿天繁星的五十六個短篇,正如古典推理小說大師而且也極可能是推理史和推理評論第一把交椅的朱利安•西蒙斯所說的,即使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我們來挑選推理史上最好的二十個短篇,福爾摩斯應該至少可排得半打吧──朱利安.西蒙斯更進一步銳利指出,在長篇推理並未找到「舒適」表達格式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福爾摩斯的四個長篇,不論就詭計、就情節和結構,毋寧更像是字數寫得太長的短篇,只除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是「提前出現」的長篇瑰寶。
福爾摩斯的短篇如何好法?我個人曾有個可能並不恰當的說法:古典推理的短篇接近推理小說的「原型」,所謂的原型,指的不只是推理演化史的順序由短篇而長篇這一點,而是指短篇通常直接體現著詭計和死法,是古典推理長河所賴以發展的一個個源頭,這樣的原型,我們可以簡單通過短篇小說的「概念化」予以提煉結晶出來,比方說,福爾摩斯的某個短篇(對不起,基於職業道德我們不能提是哪篇作品)是「如何讓凶手裝扮成被害人」,或「死亡或重傷無力之後如何讓凶器消失」等等,當這樣的概念結晶出來,後代的寫作者便有再複製的可能,就像研發出一部原型飛機可以增添修改成為多種形態功能不同的機種一樣。
如果這樣的想法不算太離譜的話,那我們可以說,柯南.道爾的五十六個短篇,除了少數不免自我重複之外(海克拉夫便是逮住這少數特例開火的),他一口氣獨力為後來的?理創作世界至少貢獻了四五十個詭計或說死亡的原型,這是個極其驚人的數字,你要不要打個電話問問美國的麥道或洛克希德公司,四五十架成功的不同原型飛機值多少錢?
所以說,推理小說始自於愛倫.坡,但真正讓推理小說大成大行的關鍵人物卻是柯南•道爾及其筆下的福爾摩斯,當然,我們也別忘了,他另外還貢獻了華生醫生,這個神探助手的概念人物,被全世界眾多推理作家狠狠使用了一百年,至今仍用來順手無比,絕不過時。(其實哪裡只是推理小說,你以為蝙蝠俠身旁忠心耿耿的羅賓,概念從哪裡來?)
尋常「一次性使用」、只關心最終凶手是誰的讀者比較不容易發現福爾摩斯閱讀玩賞底下的巨大意義,但寫小說的推理作家對這點可是知之甚詳,福爾摩斯的短篇像一個巨大的羅網,一百年來的古典推理作家放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想像馳騁,定下神來才發現自己依然在福爾摩斯的掌控範圍之中,你會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慨歎,當然,你也可能會很生氣。
這也使得福爾摩斯的短篇值得並吸引真正的推理迷一再閱讀,而不是知道答案就毫無樂趣了──我個人的經驗是,除了順手翻翻、看看其中某篇這種不算之外,大約每隔個兩三年便很自然會從頭看一遍,總次數大約在五到八次之間,我記得每個結局,每個關鍵,每個出場人物,每個情節甚至對白,但仍趣味盎然。
三隻黑羊
至於,那三隻黑羊呢?──我指的是《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之外的三大長篇。
其實沒那麼糟糕啦,海克拉夫顯然是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誇張傢伙,我這麼說並非懾於福爾摩斯的威名,或考慮到事隔一百年難免應該降低標準,我是真的有認為不壞或頗有意思的真心理由。
這麼說好了,我個人喜歡的字是魏碑,魏碑是從漢隸走入真書(即今日的正楷)一個有趣而燦爛的階段,為什麼有趣而燦爛呢?我的想法是,彼時真書的形態還沒完全定型,某個字該怎麼寫才叫好看,沒形成有限的定則(比方說王羲之或顏真卿怎麼寫它),提筆寫字的人千奇百樣,充滿了嘗試性和想像力,同一個字,石門銘有石門銘的寫法,靈廟碑陰有靈廟碑陰的寫法,溫泉頌有溫泉頌的寫法,天下不定於一尊,美學沒有強大難以撼動的唯一主流,字的呈現當然多樣而且充滿驚喜,不像後代,天下不宗顏即宗柳之後,美則美矣,但看來看去就那少數幾種字,久而久之不免以為這個字只能這樣寫才對。中國後代的書法家亦發現了這點,所以才有「顏真卿出,天下之字大好也大壞」的說法,大好,是因為有規則可摹可循,較容易有個款式;大壞,則是因為顏真卿的磅礴懾人,後代學書者容易膽怯而不敢落拓瀟灑地走自己的路。
柯南.道爾便正好是處於這樣「一體兩面」環節之人。之前固然有愛倫.坡、威基.柯林斯等先驅,但古典推理的「寫法」並未真正定型,和其他小說的邊界亦非常模糊,柯南•道爾一方面以他的推理寫作才智為後代推理小說鑄成發展之路,但另一方面,他個人的寫作則充滿著嘗試意味,鑿痕累累。像《恐懼之谷》,在結構上便完全不符合我們所習見的長篇推理,它幾乎是一截為二,前半是一篇稍長的純短篇推理,後半則是另一篇黑幫火拼的歷險小說;更怪的是被今日古典推理視為不可違犯的最終解答,居然就在這小說進行一半的臨界點就「提前」出現,這當然令今人讀之駭異。
但正如小說名家張大春的用詞:這樣的書寫有某種「野趣」,我們感受到某種樸直的自由。
如此的野趣或說自由,表現在柯南•道爾較圓熟的短篇探案上便有著相當醒目的光芒,在福爾摩斯的五十六個探案中,我們會讀到,其中有來不及破案的,有無須破案的,亦有說不出來福爾摩斯到底算成功或失敗的,甚至還有連構成不構成犯罪都難以說清的,它們不像後代推理小說那麼「整齊」,於是也就沒有後代推理小說那樣削足適履式的矯揉造作──總而言之,它們和人生現實有更稠密更結實的聯接,沒那麼封閉。
真的福爾摩斯
這直接間接令福爾摩斯獨立於所有虛構的古典推理神探之上──他像是真的,有真人的肌理和質感。
這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令很多人上當。
這裡,我引述一篇《讀者文摘》的文章前段:
倫敦貝克街上,一個肩掛照相機的遊客抬頭找尋門牌。商業大廈管理員白拉斯見了便說:「又來了一個。」果然那遊客在門外止步,略一猶豫,然後推門而入,走到擺在大堂的辦公桌前,面帶困惑的神情向白拉斯問路:「我想找二百二十一號B座福爾摩斯的住宅。」
這已是當天的第十二次,白拉斯重複解釋一一九號到二二三號歷來是阿比國民房屋協會的會址,並非福爾摩斯和華生住宅。那遊客若有所失,問道:「請告訴我,福爾摩斯這位偵探是不是確有其人?」
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也同樣相信這件事,每星期都有大堆信件寄到二百二十一號B座福爾摩斯收。郵局總是負責地把這些信件交給阿比國民房屋協會,由協會客氣地答覆:「收信人已遷,現址不詳。」
我個人便也曾經扮演過這樣找尋貝克街二二一號B座的異鄉客,只除了,過去太多人的上當經驗,令我知道那裡並沒有抽著板煙等著幫我解答謎題的福爾摩斯和華生醫生在。我下了貝克街地鐵站,牆上瓷磚滿滿是福爾摩斯口銜煙斗的著名剪影。很清楚地知道已來到他的勢力範圍了,然後我循地圖找到住址,沒有管理員白拉斯,也無需問白拉斯,如今它是一間小小的福爾摩斯紀念館,底下是販賣部,我買了兩根印有同樣剪影的金屬咖啡小匙,以為紀念。
在那樣一個秋天黃葉嘩啦刮過老英倫路面的瑟瑟街頭,我「自我感覺良好」,仿佛走到了人生現實和想像世界的曖昧交界之處,有一種遑恐的幸福之感。
我想,福爾摩斯的宛若真有其人,不只因為柯南.道爾對這名神探長相栩栩如生的描述,哪個推理神探的長相(如布朗神父如白羅)我們不知道呢?也不只因為柯南•道爾運用一些書寫小技巧如書信、記錄、日記和檔案資料等,努力想讓假事成真,這從十八世紀的現代寫實小說家笛福、李察生和費爾丁以來我們也看慣了;更不只因為柯南•道爾還為福爾摩斯留下了明確無二的地址問題(這一點我們今天還真的很感激他這麼做)──而是因為福爾摩斯就像是真的。
對一個百年之後故地重返的福爾摩斯尋旅者來說,便不會只逗留在貝克街附近尋找或說感受福爾摩斯,他與倫敦市甚至整個大英帝國同在,你看著路上的街車,到查令十字路或維多利亞車站,步行過滑鐵盧橋,坐在泰晤士河邊喝咖啡或發呆,或甚至只是沒事看看那些緩緩行走的很「英國長相」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要你讀福爾摩斯讀得夠熟夠仔細而且夠多遍,你自然會想得起每個名字、每件案子,以及每個情節起伏和對話,你可能還會不自主地跟著學「聰明」──前面那個中年男子才從美國回來,他是會計師,而且最近老婆剛過世,留下一個還念小學的獨生女兒;旁邊公園椅子上坐著的年輕小姐則最近才換了眼鏡,她有個不和善的雇主而她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辭職回愛丁堡去;至於剛剛走過她前面的老頭子則是退休的騎兵,他在二次世界大戰北非戰場受過傷,他喜歡戴安娜王妃遠勝過查理斯王子,如今他最大的願望是到西藏一趟,找尋吉蔔齡小說中所描述的世界……
福爾摩斯,當然是真的。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福爾摩斯全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99 |
二手中文書 |
$ 1019 |
歐美推理小說 |
$ 1019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福爾摩斯全集
歷久不衰的推理經典
「你從阿富汗來?」
這是夏洛克.福爾摩斯1886年誕生於英國時所說的第一句話,也是一百五十年推理史最重要的一句定場辭。事實上,這一句問語,就涵蓋了一場推理過程。這般精準而獨到的觀察與推理,不但讓助手華生醫生驚嘆不已,也從此讓全世界的讀者們死心地跟隨著福爾摩斯經歷一場場瑰麗且刺激的冒險探案。
福爾摩斯與華生住在倫敦市貝格街221號B座,後因華生結婚而恢復獨居生活,但華生偶爾會在下班之後或結伴探案時繞過去貝格街坐坐。除了華生以外,小說中還出現幾位固定配角,包括蘇格蘭場的警探李士崔和葛里格森、兄長麥考夫、犯罪集團首領莫拉提教授,以及由貝格街上的孩童組成的「雜牌警探隊」等等。
有關福爾摩斯(或寫他的柯南.道爾)有多重要、多偉大,這已是常識了,不待多言。這裡我們只說,他在人類歷史裡歸屬於一個古老、人數不多、而且今日世界已然停止供應的職位或說人種,名單大致是:巴哈、米開朗琪羅、愛因斯坦、亞當.史密斯、達爾文和邁克爾.喬丹(他極可能搶下了最後一個名額)云云。
本輯套書收錄有柯南.道爾所著的五十六部短篇、四部長篇探案故事外,還有驚喜的《柯南.道爾的一生》,撰寫的人不僅大有來頭,而且是真正的「內行人」。此人叫約翰.狄克生.卡爾,是推理史上大師級的人物,他有個更響亮的名號,叫「密室之王」,理由是他一生數十部推理小說皆至少存在著一個以上的密室殺人概念──當然,這本《柯南.道爾的一生》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經典重讀的五大理由】
1.用朝聖之心讀它:推理小說雖始於愛倫.坡,但真正的流水源頭卻是從福爾摩斯開始。
2.用歷史的追尋之心讀它:由此建構出自己的推理歷史。
3.用考古學者之心讀它: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現存的推理小說在這裡皆能找到出處。
4.用後代推理小說家之心讀它:就像百年來的推理小說家一樣,學習技藝並偷點東西。
5.用單純之心讀它:即使到今日,福爾摩斯仍是最頂尖的作品。
【福爾摩斯探案事件簿】
◎五十六部短篇、四部長篇探案故事完整收錄!
◎獨家收錄推理小說大師約翰.狄克森.卡爾編寫《柯南.道爾的一生》!
1.暗紅色研究
2.四個人的簽名
3.福爾摩斯辦案記
4.福爾摩斯回憶記
5.巴斯克村獵犬
6.福爾摩斯歸來記
7.恐懼之谷
8.福爾摩斯退場記
9.福爾摩斯檔案簿
10.柯南.道爾的一生
作者簡介:
亞瑟.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
亞瑟.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1859年5月22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是家中第二個小孩。1876年進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就讀,花了五年時間取得學位,後定居倫敦。為了醫治酒精中毒的父親,家庭支出龐大,道爾遂行醫扛起家計重擔。但由於並不熱中醫務,使他有多餘空閒時間,從那時起著手寫福爾摩斯探案集。
道爾以真實生活中,他的老師約瑟夫.貝爾醫生作為原型,將其高度的觀察力與推理能力鎔鑄在小說角色中,創造出福爾摩斯這位偵探。第一篇成名作品《暗紅色研究》於1886年完成,1887年出版;1890年《四個人的簽名》出版後,他放棄了醫務而 專心於寫作。雖然也寫過不少冒險及文藝小說,但卻是以福爾摩斯偵探小說聞名於世。事實上,當道爾寫膩了這個角色,在1893年出版的《福爾摩斯回憶記》將他賜死,後來卻由於讀者大眾的要求,被迫技巧性的使他起死回生。
柯南.道爾一生經歷多采多姿而且曲折離奇。他是個歷史學家、捕鯨者、運動員、戰地通訊記者及唯心論者。他曾參與兩件審判不公的案子,並運用偵探技巧使真相大白。1902年時,他曾參與波爾戰爭,在南非的野戰醫院表現優異,因而受封為爵士,卒於1930年7月7日。
譯者簡介:
王知一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曾譯有《辦公室求生術》、《廣告媒體與運用手冊》、《面對工作之怒》、《育兒寶典》、《山旅書札》。
TOP
推薦序
導讀╱你從阿富汗來?──二十世紀末福爾摩斯再訪台灣
文/ 唐 諾
「你從阿富汗來?」——這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一八八六年四月誕生於英國所說的第一句話,物件當然就是日後負責記敘他一生行跡並充當他探案助手的約翰•華生醫生。
彼時華生醫生方由阿富汗戰場負傷被遣送歸國,想找一處分租的廉價居所,經由朋友介紹,有名怪人亦因房租太高無人分攤而煩惱,兩人遂因此在大學的化學實驗室初次碰了面。這段經過寫在福爾摩斯探案的處女作《暗紅色研究》中;那處分攤的租屋則是攝政公園旁、往後偵探小說世界最重要的一個住址:倫敦市貝克...
文/ 唐 諾
「你從阿富汗來?」——這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一八八六年四月誕生於英國所說的第一句話,物件當然就是日後負責記敘他一生行跡並充當他探案助手的約翰•華生醫生。
彼時華生醫生方由阿富汗戰場負傷被遣送歸國,想找一處分租的廉價居所,經由朋友介紹,有名怪人亦因房租太高無人分攤而煩惱,兩人遂因此在大學的化學實驗室初次碰了面。這段經過寫在福爾摩斯探案的處女作《暗紅色研究》中;那處分攤的租屋則是攝政公園旁、往後偵探小說世界最重要的一個住址:倫敦市貝克...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亞瑟.柯南.道爾 譯者: 王知一
- 出版社: 臉譜 出版日期:2011-12-02 ISBN/ISSN:978986120994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00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