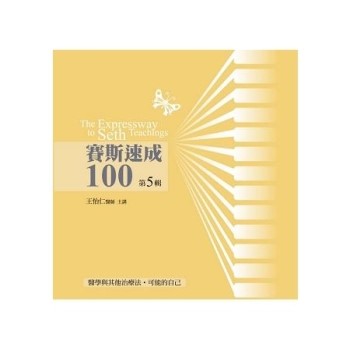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0 |
二手中文書 |
$ 510 |
社會人文 |
$ 600 |
大眾傳播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
過去幾十年來,「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意味著記者運用其如椽之筆,英勇地揭露不公不義、惡行劣跡,以及最重要的──濫用權力。《別對我撒謊》收錄了歷來調查報導的扛鼎之作,表彰幾位最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時值今日,新聞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攻擊,本書的問世意義格外重大。
本書選錄篇章依寫作年代編排,類型涵蓋新聞報導與專論、電視節目底稿與專書節錄,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緘默之牆的後方,披露令人坐立難安的重大真相。編者約翰.皮爾格也藉本書向他最欽佩的新聞工作者致敬,包括名噪一時的揭密記者(挖掘越南美萊大屠殺的西摩.赫許、直探洛克比空難真相的保羅.福特)、勇氣十足的親身見證者(廣島原爆之後第一位趕到當地的西方記者韋佛瑞德.柏契特、一九九○年代定居加薩走廊進行報導的阿米拉.哈絲),以及另闢蹊徑的新聞工作者(德國變身臥底記者根特.華萊夫、戳穿美國殯葬業真面目的潔西卡.密特佛)。
《別對我撒謊》涵蓋過去五十年來意義重大的事件、醜聞與抗爭。從瑪莎.葛爾紅筆下在一九四五年解放後的納粹死亡集中營達豪,到二○○三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之後的血腥殺戮。一路走來,讀者將深入理解不公不義如何蹂躪越南、柬埔寨、東帝汶與巴勒斯坦等地的人民。
皮爾格為每一篇報導做了詳盡的導讀,針對作者提出個人的獨到見解。同時皮爾格也為全書寫了一篇緒論,他大聲疾呼:本書全力表彰的調查報導,正面臨諸般惡勢力從新聞界發動的顛覆威脅,這些惡勢力正是調查報導要口誅筆伐的敵人。
綜而觀之,本書藉由當代最頂尖記者的精彩報導,鋪陳出一部跨越世紀的「祕史」,號召全球各地的新聞工作者:此時再不奮起,更待何時!
商品資料
- 作者: 約翰.皮爾格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7-01-02 ISBN/ISSN:9789861247960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608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大眾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