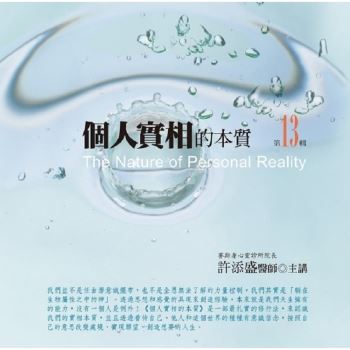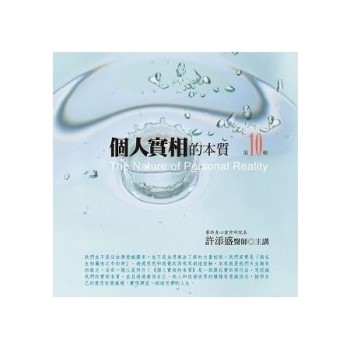這是一部讓有目標的人更熱血,
讓沒有目標的人變得想把它尋找出來,
讓有煩惱的人產生勇氣,
能夠成為猶如每個人的能量飲料般的魅力故事。
★世界第一熱血的哈佛留學記
「我留學於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他們的暑假很長,有四個月之久。通常哈佛MBA的學生都會去參加名為『INTERNSHIP』的企業實習,賺取百萬圓以上的薪資;而我,則是花了這四個月的時間做了不同的事。」
◆一場價值百萬圓的挑戰,竟是……
有一種食物名叫水牛城辣雞翅,當時正在舉辦全美料理王比賽;
為了挑戰這個比賽,我賭上了一整個暑假。
◆水牛城辣雞翅!?
菜單上通常稱作雞翅,用醋跟tabasco調味,有種非常奇妙的味道,
有些人會覺得這道料理超級辣,但我絲毫不在意,就給它一口咬下去。
◆用哈佛的暑假挑戰全美第一!
料理選手權剛好在暑假接近尾聲的時候舉行,所以,
我就以「吃遍全美一周的辣雞翅狂熱粉絲」的稱號直接和他們談判讓我出賽。
這個男人能拿下優勝嗎?
優勝究竟有什麼「好處」?
「我在心裡發誓,我死也要完成與我引以為傲的父親所訂下的約定。」
雖然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會選擇辣雞翅,但是如果要我為自己竟會遵從這個不自量力的心願行動找個理由,我可以說,那都是哈佛商學院的教育惹的禍。
「不要一心想著要在大企業晉升這種輕鬆的事」,學校這麼教我們。
「如果每天早上看著鏡子時老是覺得提不起勁,如果覺得鏡中的自己不見期待、興奮的神情,你就要重新去思考出路,去做可以鼓舞自己的事」,學校也這麼教我們。
「不要等到年老以後才後悔,不冒險挑戰的生活才是背負最大風險的人生」,學校還這麼教我們。
所以,我想靠著享有娛樂王國美譽的美利堅合眾國的重量級垃圾美食--水牛城辣雞翅--來帶給人們感動。
我要靠著我最熱愛的水牛城辣雞翅拿下第一名,登上「王」的寶座大聲吶喊。
我要感動美國人。事情就這麼簡單。
我終於擺脫長年的約定和所有的束縛,
當回原原本本的自己。
〔摘自內文〕
『脫下褲子吧!』
這是被全世界認可的勇氣與激情喔。
作者簡介
兒玉教仁 NORIHITO KODAMA
一九七二年出生,日本靜岡縣人。清水東高校畢業後,花一年時間拚死打工賺取學費,一九九二年首次赴美留學,畢業於美國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一九九七年進入日本三菱商事有限公司。二○○四年進入哈佛商學院就讀,二○○六年取得MBA學位後,於三菱商事復職。二○一一年離職,以培育國際社會人材為職志,成立新公司「Global Astrolines」。
譯者簡介
張富玲
台大日文系畢,曾於翻譯公司、出版社任職,現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