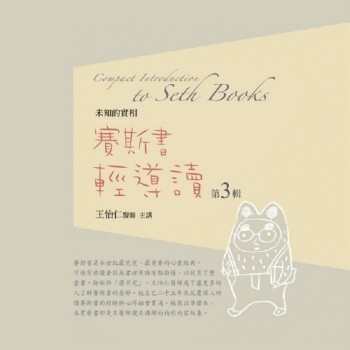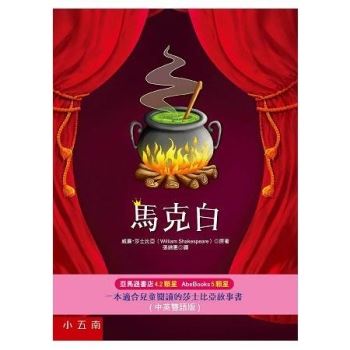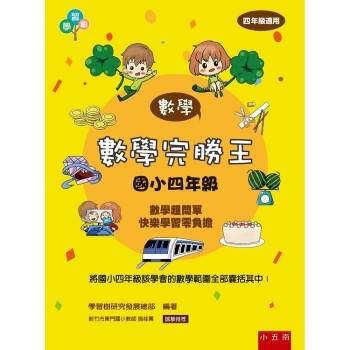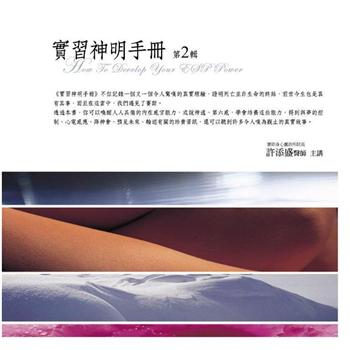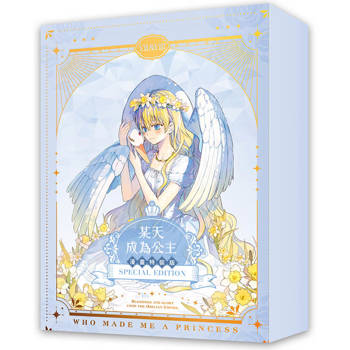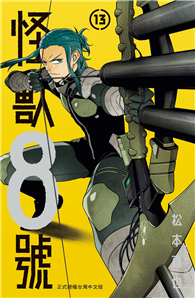明朝不只那些事
從皇室權貴到文人武將,一窺大人物們掌握的權利、欲望和真實面貌……
朱元璋沒有什麼文化,卻喜歡寫點東西。
李善長為開國功臣,卻慘遭滅門之禍。
一介文人方孝儒,氣節高尚而遭殺身之禍。
胡惟庸明列奸臣,後世史家卻對其案持懷疑態度。
錦衣衛、奪門之變、西廠橫行的各式權利鬥爭,譜寫出四十六篇情節緊湊的精采歷史。
‧劉伯溫致仕後選擇「朝入青山暮泛湖」,為何仍難逃一死?
‧明朝開國謀臣的朱升為朱元璋成就宏圖大業,為何選擇歸隱?
‧創造「永樂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是用了哪些令人髮指的手段對待舊臣?
‧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有何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崇禛末年的袁崇煥、毛文龍到底有何功過是非?
明朝(1368-1644年)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檢,共歷經十六位皇帝,長達二百七十六年。明初,由於朱元璋的洪武之治、明成祖的永樂盛世,到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歷經百年榮華,成就了繼漢唐盛世後又一個興盛的王朝,也曾是當時手工業、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然而,到了末期,皇帝昏庸不理政事,又遇氣候突變、戰事頻仍帶來的飢荒,終於引起人心不滿而民變,最後滿清入關而滅亡。
現今看來,將近三百年的歷史裡,「小人物」早已湮滅,留下「大人物」任人評說——本書中的每一個主角,無論九五之尊的帝王、權傾一時的大臣、不可一世的佞幸,都是所謂名留千古的「大人物」,但主宰他人命運的同時,他們卻無從把握自己的起落浮沉。
《明朝大人物》娓娓道來的,即是一個更接近真實的明朝故事。由致力於明史研究數十年的樊樹志教授,透過各種史料的比對、研究之後,以當代人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而成。本書共46個故事,每篇的選題、立論、敍述,都極具新意,讓人耳目一新。
作者簡介:
樊樹志
一九三七年生於浙江。一九五七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一九六二年留校任教。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代表作有《萬曆傳》、《崇禎傳》、《國史概要》、《晚明史》、《國史十六講》。其中《晚明史》榮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
章節試閱
二、朱元璋的文筆
朱元璋民間畫像
「朱元璋的文筆」,題目似乎有點突兀,為什麼偏偏要談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筆呢?
朱元璋出生在貧苦的農家,只在幼年短暫上過私塾,識得幾個字。然而,從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經歷來看,又不像一個文盲,一生勤奮好學,廣泛涉獵經史、兵法,頗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筆,仍然有點困難。
話說回來,儘管此人沒有什麼文化,卻喜歡寫點東西,膽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現在還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跡,是給部下的信函或便箋,文筆自然,不加修飾,如同當面講話一般,毛筆字寫得也還可以。此外可以考證斷定,出於他手筆的文章還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皇陵碑》。
十七歲那年,淮北大旱,繼以瘟疫,父母兄長相繼過世,他到於皇寺當小和尚。於皇寺後來改名為皇覺寺,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改名為龍興寺,位於鳳陽城北。民間饑荒,廟裡和尚也無以為生,朱元璋有兩年時間一直四處遊方,美其名曰「化緣」,實際上是叫花,也就是乞討。
二十一歲的朱元璋回到皇覺寺後,當地的紅巾軍起義已經熱火朝天。小時候的放牛夥伴湯和,從紅巾軍那裡寫信勸他參軍。朱元璋猶豫不決之際,有人告訴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風聲。何去何從,朱元璋束手無策,只得向菩薩卜卦求籤,籤文示意他:逃跑與留守都有危險,不妨「就凶」(投奔紅巾軍),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後,當了皇帝的他,親筆書寫了《皇陵碑》的碑文,回憶這段往事,如此寫道:
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旁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我者為我畫計,且默禱以陰陽。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鬱鬱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
爾後寫到他招兵買馬,擴大隊伍,「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筆鋒一轉,寫了一段思念親人的話語,似乎是把親人的狀況告訴地下的父母:
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綱。群雄並驅,飲食不遑。
最後寫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於是整修皇陵,「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這是一篇頗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顧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後,無以為生,鄰居汪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爾後投奔紅巾軍,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稱帝的全過程。詞語鄙俚粗俗,不加粉飾,氣勢不凡,絕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勞。自學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講學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滿意。他在碑文的引言中說:「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夏燮《明通鑑》洪武十一年四月條,引用前述朱元璋的話,特地加了一句:「乃自製碑文,命良督工刻之。」明確指出碑文是朱元璋親筆撰寫的。他還在「考異」中徵引郎氏《七修類稿》、徐氏《典匯》的相關記載,來證明「自製碑文」這一論點。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把危素與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較,說:「對讀起來,廷臣們的代述,卻是如何粉飾得不自然!他們要代他粉飾,卻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說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筆的話,肯定要粉飾的是,朱元璋是走投無路,用求籤的方式向神靈請示之後,才決定走上造反之路,顯得覺悟不高。
他的其他詩文,名聲雖不及《皇陵碑》,也很有特色,不妨略舉一二。
二十五歲的朱元璋投奔郭子興,從九夫長升為小軍官回到家鄉招兵買馬,同鄉徐達、周德興、費聚、陸仲亨等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後又來了謀士李善長,他的勢力愈來愈大,在群雄紛爭中脫穎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個名叫田興的謀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二人私交情同手足。田興是一個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見朱元璋步步勝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別,浪跡江湖。朱元璋當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這位朋友,寫了一封真情摯性的信,勸他出山。信中這樣寫道:
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遊何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為之喜不可抑。兩次招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昔者龍鳳之僭,兄長勸我自為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跡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固以為戲言,不意真絕跡也……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信,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事,而平生交誼,不為時勢變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做皇帝,並非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做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敘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腳色。
這封信並非御用文人或祕書代筆,而是朱元璋自己親筆所寫,確證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說明的:「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做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沒有虛偽的客套,也沒有「禮賢下士」的陳詞濫調,這種「盡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實意,捉刀代筆者是寫不出來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絕無膽量如此直白地寫出這樣的句子:「元璋不過偶然做皇帝,並非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龍顏大怒,是要掉腦袋的。信的末尾兩句「再不過江,不是腳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氣,與前面的口氣──「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判然兩人,畢竟「做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馬倥傯之中,朱元璋親筆書寫了不少公文、手令,風格獨特,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口語體。他的部下看到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當面聽他用鳳陽口音講話一樣。
請看他給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的手令:「即日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裡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來廝殺。你料著不妨,便撥將來。」
請看他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
再看他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絡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謂文如其人,一個活脫脫的朱元璋已經躍然紙上了。
在不經意間,朱元璋開創了一種口語體的「聖旨」。洪武三年(一三七○)他為了建立「戶帖」制度,親筆寫了一道聖旨,一看便知,這道聖旨出於朱元璋的手筆: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軍。欽此。
這實在是極為少見的聖旨,仿佛在聽朱元璋訓話,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語,比如:把你們說成「你每」,戶部說成「戶部家」,充軍說成「拿來做軍」,依律判罪說成「依律要了罪過」。如今的人們看起來有點費力,在當時卻是民間日常語言,只要看一看元代雜劇裡面的對白,就一清二楚了。這樣的聖旨只有朱元璋才寫得出來,如果由祕書代筆的話,肯定不是這個樣子。明白曉暢的口語,到了史官的筆下,就變成了乾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國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核實,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文字固然簡潔,意思也和朱元璋並無差異,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經消失殆盡了。
像這樣很有意思的口語聖旨,他的「御製文集」裡面還有,一篇寫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諭西番罕東畢裡等詔」,看來日後收入文集時並未修改潤飾,依然是原來面貌。大概因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對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詔書,親自動筆,以示重視。詔書這樣寫道:
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裡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裡坐地有,為這般頭,諸處裡人都來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裡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裡巴一撒,他每這夥人,為甚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開與西番每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著人馬往那裡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與布施麼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禍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著,不著軍馬往你地面裡來,你眾西番每知道者。
與前面的戶帖諭旨相比,顯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氣,宛如元雜劇裡面那些引車賣漿者流講話的樣子,一口一個「俺」字,一口一個「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著」,而且通篇充滿威脅的字句:「你西番每怕也不怕」,哪裡有一絲一毫「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文縐縐口氣?
朱元璋身體力行宣導的口語聖旨,對他的子孫後代影響巨大,此後皇帝親筆寫的聖旨(祕書代筆的除外),夾雜口語,半文半白,已經司空見慣。
《御製文集補》收錄了朱元璋寫的一百多首詩,讀來頗感疑慮:不見得都出於他的手筆吧?不過有兩首可以肯定是他寫的,儘管有點流於「打油」,那種難以掩飾的霸氣流露得淋漓盡致。一首題名《野臥》:
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當初造反時,隨軍露宿野外時寫的,大家擠在一起,「夜間不敢長伸腳」,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將士,他偏偏說「恐踏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氣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當口寫的,題名《詠菊花》: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這是對唐末黃巢《詠菊》的應和。黃巢的詩寫道: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兩首詩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懷,就詩論詩,朱詩略顯遜色。畢竟黃巢是「家有資財,好騎射,略通詩書」的人。不過,黃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長安,最終還是失敗了;朱元璋造反成功,當上了開國皇帝,霸氣更勝一籌。「我花發時都嚇殺」,是抑制不住的內心流露,登極以後果然如此。吳晗《朱元璋傳》(一九四九年版)說:「桀驁不馴的元勳、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歸順的地方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無人敢出一口大氣。」當時的人真的「都嚇殺」了!
如果研究文學史的人,根據朱元璋的詩文集,或者根據《全明文》,送給他一頂作家和詩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卻並不以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標的經學老師宋濂說:「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為文或不喜書,召臣濂坐榻下,終日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誠所謂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壇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言語來讚揚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難脫諂媚奉承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縉,原本敢於講真話,一旦談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筆時,也和宋濂一樣,讚不絕口:「臣縉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紙以俟。聖情尤喜為詩歌,睿思英發,雷轟電觸,玉音沛然,數十百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說不是阿諛奉承,沒有幾個人會相信。
明朝的遺老錢謙益是相信的,他編撰的《列朝詩集小傳》,開篇第一個詩人就是「太祖高皇帝」,並且說明把他「冠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時的博學鴻儒朱彝尊,已經是清朝的順民了,沒有必要再拍前朝開國皇帝的馬屁,竟然和宋濂、解縉、錢謙益一般見解。他編撰的《靜志居詩話》,卷首第一人還是「明太祖」,說道:「孝陵不以『馬上治天下』,雲雨賢才,天地大文,形諸篇翰,七年而御製成集,八年而正韻成書,題詩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閣,賞心胡閏蒼龍之詠,擊節王佐黃馬之謠。」甚至認為明朝詩人輩出,「三百年詩教之盛」,全歸功於明太祖在詩歌方面的「開創之功」。
宋濂、解縉、錢謙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為什麼要說這些言不由衷的假話呢?
一三、「瓜蔓抄」及其他:建文舊臣景清與鐵鉉
今山東濟南鐵公祠鐵鉉像
燕王朱棣以軍事政變手段奪取帝位以後,對於支持建文帝「削藩」,反對「靖難之役」的官員,趕盡殺絕,其手段之殘忍,可與乃父太祖高皇帝相媲美。齊泰、黃子澄的慘死,固不待言──齊泰被「族誅」,黃子澄先砍去雙手、雙腿,再處死。禮部尚書陳迪和兒子同一天處死,朱棣下令把兒子的耳鼻割下讓陳迪吃下,還要問他:味道如何?
其他官員們的死,個個令人毛骨悚然。且以景清、鐵鉉為例,略見一斑。
景清,本姓耿,訛為景,北直隸鎮寧人,年少時在國子監求學,以聰明機警而著稱。和他住一間宿舍的同學有一本祕不示人的書籍,景清想一睹為快,對方不肯,再三請求,並且答應明日一早就歸還。第二天,那位同學向他索書,景清竟然謊稱我不知道什麼書,也從未向你借書。那位同學憤憤然向祭酒(校長)控告。景清拿了那本書前往,對祭酒說:這是我窗前燈下反覆攻讀的書,隨即一口氣把它背了出來。祭酒要那位同學背誦,居然一句也說不出,被祭酒訓斥了一頓。從祭酒那裡出來,景清就把書還給了他,笑著說:我不滿你把書看得太珍祕,故意和你開個玩笑而已。
景清是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進士,會試時列為第三名,廷試時皇帝賜予第二名,看來是才華橫溢的佼佼者,卻並非書呆子,崇尚大節。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身分,改任北平參議,顯然負有察看朱棣動靜的使命。風流倜儻的景清,與朱棣相處非常融洽,言論明晰,大受朱棣稱賞。
首都南京被朱棣攻陷,建文帝舊臣大批死亡。景清當年曾經參與「削藩」密謀,自然在劫難逃,他與方孝孺等相約,以身殉國。令人不解的是,當許多舊臣紛紛殉國之時,他來到紫禁城,向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朱棣投誠歸附。朱棣為了表示豁達大度,命他仍舊擔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建文朝舊臣搖身一變成了永樂朝新貴,景清遭到遺老遺少的非議,說他「言不顧行,貪生怕死」。
其實,他是虛與委蛇,等待時機,為舊主報仇。
某一天上朝時,景清身穿紅衣,暗藏利器,準備行刺。說來也巧,日前主管天象的官員報告皇帝:「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生性多疑的朱棣本來就對景清有所懷疑,上朝時特別注意。但見景清身穿紅衣,且神色異常,命令衛士對他搜身,果然查獲暗藏的兇器。景清奮然喊道:要為故主報仇!不斷辱罵朱棣。衛士拔掉他的牙齒,他仍罵聲不停,口中鮮血吐向朱棣的龍袍。朱棣一聲令下,當場活活打死,並且把他的皮囊剝下來,塞進稻草,懸掛於長安門示眾。
正是無巧不成書,朱棣乘坐轎子經過長安門,繩索忽然斷裂,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轎子前面,狀如撲擊。朱棣大驚失色,下令燒毀。
有一天朱棣午睡,夢見景清手持利劍追殺過來,嚇出一身冷汗。驚醒之後感嘆道:想不到景清死了還這麼厲害!下旨株連九族,連他的鄉親也不放過,「轉相攀染」而死的有幾百人之多,老家的一個村莊頓時化為廢墟。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瓜蔓抄」!
這樣的「瓜蔓抄」還不止一處。建文時期的大理寺少卿胡閏,是江西饒州府人,朱棣發兵南下,他與兵部尚書齊泰籌畫抵抗事宜。南京陷落後,不屈而死,朱棣不僅抄了他的家,而且株連他的家族,殺死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他們聚居的地方──府城西面的碩輔坊,化作一片廢墟。呂毖《明朝小史》寫道:
一路無人煙,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嘗有一猿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污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
為了懲治幾個政敵,株連九族還不消氣,居然摧毀整個村莊和社區。不獨在明朝,即令其他朝代,也聞所未聞。
另一個政敵鐵鉉的下場,更加令人哀嘆。
建文初年,鐵鉉出任山東參政。李景隆奉命北伐,征討朱棣,他負責督運糧餉,從不間斷。李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走德州,他感奮涕泣,退守濟南。朱棣率軍攻打三個月,濟南巋然不動,無奈之下,決定掘開黃河大堤,水淹濟南。鐵鉉反其道而行之,使用詐降計,派使者到燕王大營請降,請退兵十里,燕王單騎進城,軍民恭迎大駕。不戰而屈人之兵,朱棣大喜過望,騎著高頭大馬越過護城河,進城受降。說時遲那時快,城上的鐵閘門急速落下,砸中馬頭,如果稍慢幾秒,朱棣必將砸成肉餅。遭受此番羞辱,朱棣下令猛攻,濟南依然牢不可破,只得退兵而去。鐵鉉乘勝追擊,收復德州等地。建文帝隨即晉升鐵鉉為山東布政使,不久又晉升為兵部尚書。
南京陷落,鐵鉉被俘,押解到朱棣面前。他不願面對亂臣賊子,始終背身而立,口中罵聲不絕。朱棣想看他一面而不可得,命令衛士割去他的耳朵、鼻子,鐵鉉依然不屈。衛士奉命割他身上的肉,塞到他嘴裡,問他:甜不甜?鐵鉉厲聲回答:忠臣孝子的肉,當然是甜的!
面對如此寧死不屈的硬漢,朱棣束手無策,下旨寸磔處死,也就是俗話所說千刀萬剮,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來,而不讓他立即死去。整個行刑過程中,鐵鉉口中罵聲不絕。惱羞成怒的朱棣命衛士扛來一口大鍋爐,鍋內是沸騰的油。鐵鉉的軀體投入鍋中,頃刻焦黑。衛士們把他的軀體撈出,讓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辦不到。朱棣大怒,命太監們用鐵棒挾持,使他面向北。坐北朝南的朱棣朗聲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見朕了。話音未落,鐵鉉身上的沸油突然飛濺,太監四散而逃,屍體仍然反背如故。
鐵鉉死時年僅三十七歲。兒子福安、康安被處死。妻楊氏和兩個女兒,發配教坊司為娼。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賦詩明志。姐詩云: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妹詩云:
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而歸娼,
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
孟森《明史講義》寫到「靖難後殺戮之慘」,大為不解,感慨系之:「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為太祖之子,攘奪乃帝王家事,未必於建文遜位之後,定欲為建文報仇,非討而誅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後,即廓然大赦,許諸忠為能報國,悉不與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殺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實則杜諸忠之或有號召,猶之可也;誅其族屬,並及童幼,已難言矣;又辱其妻女,給配教坊、浣衣局、象奴及習匠、功臣家,此於彼之帝位有何損益?」分析得合情合理,又入木三分。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以篡得位」的明成祖朱棣的心態,絕非謙謙君子所能洞悉。這或許是「靖難殺戮之慘」給予讀史者最有價值的啟示。
二、朱元璋的文筆
朱元璋民間畫像
「朱元璋的文筆」,題目似乎有點突兀,為什麼偏偏要談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筆呢?
朱元璋出生在貧苦的農家,只在幼年短暫上過私塾,識得幾個字。然而,從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經歷來看,又不像一個文盲,一生勤奮好學,廣泛涉獵經史、兵法,頗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筆,仍然有點困難。
話說回來,儘管此人沒有什麼文化,卻喜歡寫點東西,膽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現在還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跡,是給部下的信函或便箋,文筆自然,不加修飾,如同當面講話一般,毛筆字寫得也還...
目錄
1. 鳳陽的朱元璋情結
2. 朱元璋的文筆
3. 劉基的悲劇
4.「積疑成獄」的胡惟庸黨案
5. 李善長的滅門之禍
6. 大將軍藍玉的冤案
7. 朱升為何歸隱
8.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鐵券」
9. 酷似乃父的朱棣
10. 建文帝下落之謎
11. 朱棣的智囊——道衍和尚
12. 「讀書種子」方孝孺的氣節
13. 「瓜蔓抄」及其他: 建文舊臣景清與鐵鉉
14. 打著「錦衣衛」的幌子
15. 才子解縉的政治生涯
16. 「弄沖主於股掌」的王振
17. 英宗被俘與獲釋
18. 貪位的景帝
19. 「奪門之變」的台前幕後
20. 復辟功臣的下場:徐有貞、石亨、曹吉祥
21. 憲宗與方術佞幸
22. 憲宗擅寵的萬貴妃
23. 汪直與西廠
24. 明君孝宗和他的諍臣們
25. 「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劉瑾弄權
26. 且看劉瑾的垮台
27. 告密者焦芳
28. 「甘心頤指」的李東陽
29. 武宗與豹房政治
30. 楊廷和撥亂反正
31. 「大禮議」與張璁的浮沉
32. 夏言:「棄市」的首輔
33. 錦衣衛頭目陸炳
34. 癡迷於玄修的「中材之主」:自比為堯舜的嘉靖皇帝
35. 嚴嵩、嚴世蕃父子
36. 徐階:「名相」還是「甘草閣老」?
37. 海瑞的為官風格
38. 張居正的另一面
39.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張居正的悲劇
40. 魏忠賢與奉聖夫人客氏
41. 魏忠賢與閹黨專政
42. 魏忠賢個人崇拜運動
43. 毛文龍的功過是非
44. 袁崇煥之死
45. 錢謙益的政治挫折
46. 鼎革之際的陳洪綬
後記
1. 鳳陽的朱元璋情結
2. 朱元璋的文筆
3. 劉基的悲劇
4.「積疑成獄」的胡惟庸黨案
5. 李善長的滅門之禍
6. 大將軍藍玉的冤案
7. 朱升為何歸隱
8. 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鐵券」
9. 酷似乃父的朱棣
10. 建文帝下落之謎
11. 朱棣的智囊——道衍和尚
12. 「讀書種子」方孝孺的氣節
13. 「瓜蔓抄」及其他: 建文舊臣景清與鐵鉉
14. 打著「錦衣衛」的幌子
15. 才子解縉的政治生涯
16. 「弄沖主於股掌」的王振
17. 英宗被俘與獲釋
18. 貪位的景帝
19. 「奪門之變」的台前幕後
20. 復辟功臣的下場:徐有貞、石亨、曹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