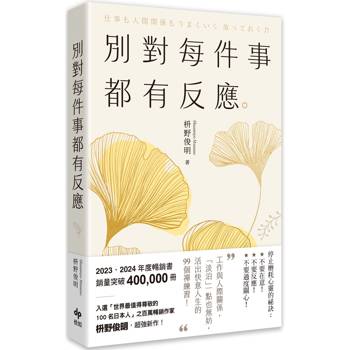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孔孟的觀點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孟子‧盡心上》
《論語‧述而篇》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不語」的態度正代表孔子對於死亡與鬼神這兩個問題的基本立場,而這兩個問題與孔子有關生命意義的觀點息息相關。孔子為何對死亡與鬼神的問題抱持「不語」的態度?從孔子回答季路的話中大略可以知道其中的原由: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
很明顯,孔子把「事人」置於「事鬼」之上,亦把「生」列於「死」之上,即以人為本,以生為重。孔子並非否認鬼神與死亡的存在,孔子之所以「不語」,在其有所側重,以人生為主要的關懷,是以對鬼神之事與死亡情狀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雖然如此,孔子還是相當重視死亡與祭祀的,這突顯出孔子的別具用心,其所關心的乃是死亡的社會道德意含。
孔子當然也知道人生而必死,所謂「死生有命」(《論語‧顏淵篇》),但孔子更強調:「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篇》)宋儒朱子對此解釋曰: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茍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四書章句集註》)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也就是為人之道,亦即完成仁義道德的生命價值。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生命若能圓成道德,雖死無憾。生死大事,端在義利之分,生若不能成就道德,就是人禽有別,這樣的存在,生無異於死,所以「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篇》)死雖無可避免,但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如此即死而無憾,而這正是生命的意義所在,此即宋儒朱子所言: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闕,需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以盡,安於死而無憾。(《朱子語類》三十九)
又曰:
生死大事,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亦在鬼窟裡度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亦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人事典卷九十二〈生死部〉)
生命的意義在死而無憾(安於死而無愧),死而無憾即道德生命的完成。《禮記‧檀弓篇》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是盡到職分,圓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之後安然就死,這種道德生命的完成叫做「終」,此在根本上截然不同於凡庸小人輕於鴻毛的「死」。 孔子雖不畏死,但有終生之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篇》)孔子之所憂並非死後遭人遺忘,而是擔心無德以供後人稱道其名。孔子曾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篇》)
「死之日民無德而稱」,此即孔子之所憂也。明儒羅倫曰: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眾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唯聖賢乎!(《一峰詩文集》)
人皆有死,聖賢與眾人無異,然聖賢則有立德之不朽,「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正是孔子對於死亡態度的最佳寫照。
基本上,孔子對生、死及死後的關懷,都把焦點放在道德的層面,因此對於鬼神的態度,雖不否認,但也抱持存而不論的立場,這從孔子尊崇祖先、重視祭祀喪葬的情形可以看出,只是孔子並不在此議題上多所著墨,因其所側重的旨趣並不在此。孔子基本上是就傳統之宗教信仰與予一種徐復觀先生所謂之「價值的轉換」 ,將傳統宗教的鬼神崇拜轉換為道德意識的呈現。
事實上,孔子對於祭祀鬼神非常重視並且相當認真,其言:「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篇》),又讚美大禹說:「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論語‧八佾篇》)。從孔子對於鬼神存而不論卻又重視祭祀鬼神的態度來看,其之所重乃在祭祀這一面,而非鬼神那一方;亦即孔子之所重乃是道德上的虔敬而非鬼神之信仰崇拜,此儒家之所以不是宗教。 這也就是為什麼孔子說「祭鬼神」而又要「遠之」,指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後還要強調「吾不與祭,如不祭」的道理。很明顯,孔子對於敬事鬼神並不是從鬼神之受祭面來立論,而是從祭者的這一面向來彰顯其意義。 基本上,對儒家而言,祭是為生人而設的社會禮儀的一部分 ,其主旨在於生人透過此一禮節儀式表達內心對受祭者的誠敬之心、哀痛之情與思念之意。因此,若祭時不親祭(「吾不與祭」),則此禮節儀式就只是一種形式虛文,祭也就完全失去其實質意義,故「如不祭」,孔子並未認真考量是否真有鬼神在享祭。若真有鬼神在享祭並以此為著眼點,則不親祭亦有其意義,因找人代祭,鬼神亦可享祭。然而對孔子而言,其所重者乃生者所處的社會層面,祭之禮儀固在表示誠敬哀思,亦在維持現世!
的社會秩序,此即「禮」之精神所在。是故,孔子在論孝之意義時說: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篇》)
「禮」者,乃純就生者而言,故孔子即反對鬼神祭拜之祈福消災的祭祀義,故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篇》)
總言之,孔子的道德取向是很明白的,在劉向《說苑‧辨物篇》中所記載子貢問孔子「人死後有無知覺」一事亦清楚表明此一立場:
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之也?」
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孝子仿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友知將無知也,死余自知之,猶未晚矣。」
孔子並未對人死之後是否還有知覺做出明白的表示,其所著重的還是在道德意義上。王充對此倒是做了一個有趣的註解,其言:
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論衡‧薄葬篇》)
荀子則對孔子這種道德取向的立場做了最明白而適切的表述:
祭者,……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篇》)
而其宗旨即在於「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道德教化,是人道而非鬼事。
孟子之生死觀乃直承孔子的思想,亦以道德為中心。與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一樣,孟子亦有「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
孟子之所憂即孔子之所疾,當我們的生命結束以後,是否有所成就德性功業傳於後世,為天下人之模範。
孟子也知道「死生有命」,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依道德而生而死,生時要成就道德,死時也要為道德而亡,道德是生的價值同時也是死的意義。生不生、死不死的抉擇端在道不道德。因此,當生命與道德有所衝突時,就必須放棄生命以成就道德。孟子論述曰: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冰!
3甚於死者,非獨聖賢有是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此以「魚與熊掌」譬喻「生與義」,雖然生與義二者皆是我之所欲,但若生義不可得兼,甚或生而有害於義,就必須「捨生取義」。人們皆欲生惡死,但不能背義而苟生,亦不可違義而避死。「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人有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生要遵之,死亦須循之,這是超乎生死的道德價值,這也是生命意義之所在,故孟子曰: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
生命之意義即在於「盡其道而死」,盡其道也就是無時無刻地做道德的修養,而道德修養的心境會在吾人形體中展現出某種光輝氣象。此即孟子的「踐形觀」,孟子說: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捐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孟子‧盡心上》)
孟子之性善論指出,仁義禮智等德性是天所賦予我們的天性,不會因吾人之得志窮困而有所增損。君子存心養性,誠於中而形著於外,故其容貌舉止乃自然顯發出一種「充實而有光輝」之氣象。孟子又曰: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孟子‧盡心上》)
形色指形體容貌,人有人之形色,禽獸有禽獸之形色,皆秉之於天,故亦稱之為「天性」。但人與禽獸有所差別之幾希,則在於與生俱來的道德本性。所謂「踐形」,就是把人之所以為人之仁義禮智的道德本性,具體表現於形色舉止之中。 若徒有人之形色而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之善性,便不能算其為人,以其未能踐形之故,踐形實即盡性。 人皆有善性,但並非人人皆可盡性,雖說人人皆可成聖,但並非人人皆是聖人,故孟子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能踐形盡性就是聖人,聖人踐形盡性,則其視聽言動渾全只是德性天理在其形色之中的具體展現,善性自然流露於其形色之光輝氣象中,動容行止無不合乎仁義道德。
依上所述,孔孟有關死亡與生命意義之觀點,可稱之為「道德的生死觀」,其根本精神不在追求死後生命的解脫,而在於完成現世生命道德人格的圓滿。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宗教與生死:宗教哲學論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宗教與生死:宗教哲學論集
死亡是生命的終極問題,不論死亡是斷滅還是斷續,都是生命不可迴避的歸宿或必經之途。面對死亡是在世存有根本之生命責任,可以忽略,能夠拖延,但終究無可避免。
宗教是人類的終極關懷,死亡之性質及其安頓乃構成宗教關懷的核心。
作者簡介:
劉見成,台灣苗栗人,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職於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已出版著作:《形神與生死》(2001年)、《謬誤、意義與推理》(與張燕梅合撰,2004)、《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2010)。詩集:《道心觀物吟:戊子詩稿》(2009)、《朝徹集》(2010)、《涵宇集:己丑詩稿》(2010)。
近年致力於道家道教思想與宗教哲學之研究,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
章節試閱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孔孟的觀點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孟子‧盡心上》
《論語‧述而篇》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不語」的態度正代表孔子對於死亡與鬼神這兩個問題的基本立場,而這兩個問題與孔子有關生命意義的觀點息息相關。孔子為何對死亡與鬼神的問題抱持「不語」的態度?從孔子回答季路的話中大略可以知道其中的原由: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
很明顯,孔子把「事人」置於「事鬼」之上,亦把「生」列於「死」之上,即以人為本...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孟子‧盡心上》
《論語‧述而篇》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不語」的態度正代表孔子對於死亡與鬼神這兩個問題的基本立場,而這兩個問題與孔子有關生命意義的觀點息息相關。孔子為何對死亡與鬼神的問題抱持「不語」的態度?從孔子回答季路的話中大略可以知道其中的原由: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
很明顯,孔子把「事人」置於「事鬼」之上,亦把「生」列於「死」之上,即以人為本...
»看全部
目錄
序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孔孟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荀子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列子》中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一個哲學的省思
死亡、後世與生命的意義:《古蘭經》中的生死觀
作為後設科學的哲學觀點
柏拉圖的死後生命觀及其道德意含:從蘇格拉底之死探討起
一道同風‧萬教歸宗:淺論宗教大同的哲學基礎
死後生命之信仰對生命意義的影響:以《中有大聞解脫》為例的哲學考察
淨土法門的臨終關懷
尋找上帝:人性中的宗教關懷──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哲學
止於至善:人文精神與莊子的精神超越
和諧與至樂:威廉詹姆斯與...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孔孟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荀子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列子》中的觀點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一個哲學的省思
死亡、後世與生命的意義:《古蘭經》中的生死觀
作為後設科學的哲學觀點
柏拉圖的死後生命觀及其道德意含:從蘇格拉底之死探討起
一道同風‧萬教歸宗:淺論宗教大同的哲學基礎
死後生命之信仰對生命意義的影響:以《中有大聞解脫》為例的哲學考察
淨土法門的臨終關懷
尋找上帝:人性中的宗教關懷──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哲學
止於至善:人文精神與莊子的精神超越
和諧與至樂:威廉詹姆斯與...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劉見成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1-04-01 ISBN/ISSN:978986221528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6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