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緒論:晚近中國──循環往復的歷史
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描繪了歷史循環往復的場景。在他的筆下,西方以物質文明為主的時代興起時,以精神文化為主的時代必然逐漸沒落。這一時代相交的轉變出現在拿破崙時代。為了佐證這一觀點,斯賓格勒不無深意地談到了中國的秦漢時代,印度的阿育王時代,希臘的亞歷山大時代以及中東的穆罕默德時代。斯賓格勒將歷史看作一個循環的過程,當某一時代走向終結時,也即意味著它走向另一個時代的起點。而作為起點的這個時代恰恰在漫長的歷史之前,為已經走向終點的這個時代所代替。
斯賓格勒寫作此書時在一戰之後肅殺的時代?,陪伴他的只有昏暗的房間以及同樣昏暗的燭火。他獨處一隅的書寫,成就了歷史敘述嶄新的面貌。而他所闡述的歷史循環論,恰恰可以作為中國晚近歷史極為精準的概括。斯賓格勒對於中國秦漢時代文化脈絡的細緻把握,讓他抓住了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根本特性。晚近歷史之於中國歷史整體的大循環而言,是相對微小的輪迴。這種微小僅僅只是就事件的跨度而論,在內容以及所包含的深刻意味方面,乃是對於過往歷史極具反叛意味的顛覆。
中國晚近歷史這種輪迴,對應斯賓格勒歷史循環論的言說,便是文化、歷史本身的循環往復。其中文化貫穿於歷史之間含義在於,任何歷史事件無論具有怎樣的歷史定義,都無法抹卻其固有的文化象徵意味。例如晚近歷史中太平天國的興起、曾國藩的平叛、北伐的幽靈復生抑或是文革的從天而降,都一一標注了歷史、文化的象徵色彩。同樣,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所描繪的歷史,恰恰以文化為基礎,指出歷史的走向與循環,由此揭示了歷史的另一層含義。
這種迥異於以往的揭示,是對所謂進化論史觀的歷史反動。作為一種極具魅惑的言說,進化論史觀雖然有其無可厚非的合理性,但在對於歷史的把握上相當膚淺,僅僅是停留在最為基礎的層面上作出相應的闡釋。只是這種充滿了基礎性膚淺的言說,乃是以一種進步的面目呈現於世人。不僅這種進步性令人質疑,而且在對於具體歷史的分析與闡述時,往往形成套路式的話語,從而使得人們對於歷史的印象枯燥無味,充斥著單調的理論教條。
更具悲劇性的是,晚近歷史上進化論史觀的氾濫,幾近將歷史本身埋葬。因而晚近歷史充斥著焦灼,充斥著鬥爭,充斥著革命所張揚的運動與批判,使得晚近歷史烈火雄雄,滿是高漲的情緒與沸騰的氣氛,幾近把歷史融化。這種由嚴復舶來中國,經由所謂馬克思唯物主義催化的所謂進步史觀,終究被歷史證明為一出荒誕的悲劇。
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對於晚近歷史的敘述,僅僅著眼於歷史本身的人物與事件,不再為主義所擾,為史觀所困,而著重闡述其所象徵乃至標注的文化意味。秉承斯賓格勒歷史循環論的觀點,我將晚近歷史視作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這一過程無所謂起點與終結。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其內部充滿了某種前後相繼的歷史循環,而在這種歷史循環之中,充滿了難以預知的劫數與變數,從而使得晚近歷史作為一段曾經謝幕的時候留下了眾多意味深長的命題。
晚近歷史之間前後相繼的歷史循環,指的是晚近歷史中諸多歷史人物與事件之間所擁有的帶有傳承意味的輪迴。其間不僅有諸如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歷史傳承,北伐與文革的歷史傳承,還有曾國藩所代表的洋務精英與康梁所代表的維新諸子的歷史傳承,李慎之王元化所代表的世紀末文化老人之於胡適陳獨秀所代表的五四先賢的歷史傳承。當然也還有王國維至陳寅恪的歷史觀照,孫中山與毛澤東的歷史聯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些傳承與觀照標明了歷史並不是如同進化論史觀所闡述的直線式的上升式形態,而是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傳承與循環,由此構成了歷史的完整與輪迴。
所謂晚近歷史之劫數與變數,意指晚近歷史中諸多人物與事件所昭顯的象徵性意味與轉折性意味。這些人物與事件互為聯繫。由此構成了歷史的細密與深邃,也為歷史染上了無法抹去的慶幸與悲涼。這種慶幸代表了變數,這種悲涼代表了劫數。變數就其所指,例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洋務,康梁諸君之維新,胡適、陳獨秀之啟蒙運動等等。而劫數則指向了太平天國、義和團、北伐、反右、文革,洋溢著暴動快感與暴動熱忱對於歷史具有深度破壞的事件。雖然就其本質而言,太平天國至文革都指向了理想社會的構建,但無一例外的在實踐中反其道而行之,對歷史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而例如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之類帶有改良主義傾向的試圖以漸進的方式將中國改造成為現代社會的努力,則因為諸多的歷史原因折戟沉沙,給後世乃至歷史留下了諸多遺憾。
晚近歷史之劫數與變數除卻剛才所言的人物與事件之外,更為細微之處在於時代中的個人偶然性的舉動之於歷史影響的悠遠。這種由偶然性所引發的巨大影響包含著時代性的緣由。例如宋教仁之被刺,昭示了晚近歷史至少在相當長時間內走向民主憲政的無望,孫中山與蘇俄的合作標明了蘇俄暴力革命在中國的生根發芽,陳寅恪雙目失明著述代表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柳如是別傳》意味深長地對革命時代的專制予以抗議,毛澤東發動文革標注了封建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殘渣依然陰魂不散。時代中人物不經意的舉動,成為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由此在晚近歷史上留下了印痕。
劫數與變數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了晚近歷史的進程。由此我將晚近歷史分為日落時代、盛夏時代、革命時代。日落時代作為清季的迴光返照,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為晚近歷史提供了原動力。而盛夏時代則構成了晚近歷史上最為光輝奪目的時期。盛夏這一指稱不僅意指其時代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活力,更為重要的是它以夏日暴雨般的思潮,讓天地煥然一新,精神為之一振。而革命時代則意指在革命作為一種浪潮風行於世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階段雖然中國由大亂走向治平,但是與革命相生相隨的諸多政治事件,則將社會由治平推向了大亂,因而革命時代充滿了未知的變數與劫數,恰恰可以反映出晚近歷史駁雜的面目。
以日落時代曾、李諸人所開創的洋務運動為起始,歷經康梁維新、新文化運動直至八、九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復生,一一標注了歷代精英的努力,而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至北伐經由反右直到文革,以暴力蠻橫地將歷代精英的努力打壓下去,埋進歷史的墳墓。直至世紀之交晚近歷史由終點走向起點的時候,從歷史的墳墓中復活的歷代精英的努力所標注的曾經,則因為時代之幸以及有限度的開放得以為人們所銘記以及言說,只是此時革命時代的喧嘩已然褪去,此時已是革命時代的尾聲。晚近歷史由此靜默地走向了終結。只是歷史走向終結的當口,曾經的歷代精英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尚未結束。由革命時代褪去所引發的新一輪歷史的循環,則將中國推向了充滿可能的十字路口,此時的抉擇至關重要,承接先賢的歷史遺產,摒棄晚近歷史中的種種惡性循環,接下來的歷史才能不重演晚近歷史的諸多悲劇,由此獲得新生。這便是本著所要提示的應有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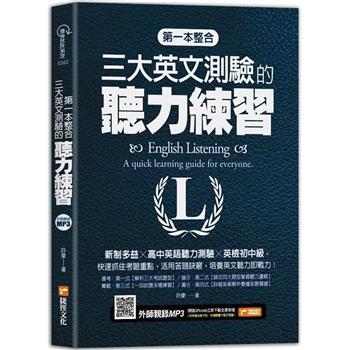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