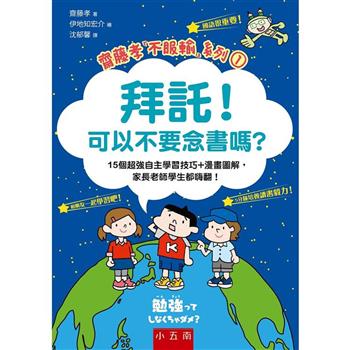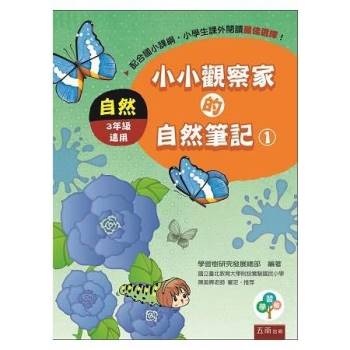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閒事莫理」是這世界的生存法則,不管在哪,有些事都不該惹……
香港發生了好幾件學生命案與失蹤案,這些案件看似沒有關聯,各種線索卻又都指向校園間流傳的恐怖傳說。
直到負責承辦的歐陽劍崎發現,原來這些學生,都曾經參加一個「台灣交流團」,而他們在台北住的地方,是死過許多人的「西寧國宅」——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通靈校舍的圖書 |
 |
通靈校舍 作者:畢名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9-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7 |
二手中文書 |
$ 87 |
驚悚/懸疑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通靈校舍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畢名
在畢名架設的驚悚世界,盡是呈現現實中人性魔性殘忍角力的畫面。鬼可怕嗎?他告訴你人一樣可怕。
由香港寫到台灣,以精鍊的文字、扣人心弦的驚悚佈局、充滿電影感的情節,七年間出版二十四本小說,並三度入選香港十本好讀選舉我最喜愛作家名單。
2008年憑《娃娃契約》登上香港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暢銷書榜,2012年加入明日工作室推出明日名家系列【靈異出版社】,其後作品《畸羅之眼》、《嬰之契約》、《終結者》(上下冊)分別入選第六屆香港書獎提名名單。
其他著作:《鬼界夢劫》、《恐怖病‧失蹤》、《別殺我媽媽》、《守護者》、《沉淪者》、《末殺者》、《恐怖潮》I及II、《七天房客‧相遇九如坊》等。
官方Facebook:www.facebook.com/bedming
官方網站:bedming.wix.com/-novel
畢名電郵:bedming@yahoo.com.hk
畢名
在畢名架設的驚悚世界,盡是呈現現實中人性魔性殘忍角力的畫面。鬼可怕嗎?他告訴你人一樣可怕。
由香港寫到台灣,以精鍊的文字、扣人心弦的驚悚佈局、充滿電影感的情節,七年間出版二十四本小說,並三度入選香港十本好讀選舉我最喜愛作家名單。
2008年憑《娃娃契約》登上香港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暢銷書榜,2012年加入明日工作室推出明日名家系列【靈異出版社】,其後作品《畸羅之眼》、《嬰之契約》、《終結者》(上下冊)分別入選第六屆香港書獎提名名單。
其他著作:《鬼界夢劫》、《恐怖病‧失蹤》、《別殺我媽媽》、《守護者》、《沉淪者》、《末殺者》、《恐怖潮》I及II、《七天房客‧相遇九如坊》等。
官方Facebook:www.facebook.com/bedming
官方網站:bedming.wix.com/-novel
畢名電郵:bedming@yahoo.com.hk
目錄
序 章 – 以眼還眼
第一章 – 血案登場
第二章 – 中大重遇
第三章 – 一條辮子
第四章 – 舊情人
第五章 – 西寧國宅
第六章 – 羈留室
第七章 – 荷花池之約
第八章 – 恐怖大樓
第九章 – 停屍間
第十章 – 等著你……來
終 章 – 通靈
後 記 –
第一章 – 血案登場
第二章 – 中大重遇
第三章 – 一條辮子
第四章 – 舊情人
第五章 – 西寧國宅
第六章 – 羈留室
第七章 – 荷花池之約
第八章 – 恐怖大樓
第九章 – 停屍間
第十章 – 等著你……來
終 章 – 通靈
後 記 –
序
作者後記
終於完成第一本明日文庫小說。
對一直有支持便利書或文庫的讀者來說,「畢名」這個名字可能會較陌生,但如果有捧場名家系列的讀者應該知道,我其實就是【靈異出版社】系列的作者,在明日已出版的小說有《畸羅之眼》、《嬰之契約》、《別殺我媽媽》、《恐怖病‧失蹤》及《鬼界夢劫》五本。
作為來自香港的海外作家,加入明日工作室這個大家庭很快就經已兩年,期間得到叔慧姐、令葳、君宇等同事的信任,令我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台灣恐怖書市的文化,亦令我有幸認識到不少愛書又可愛的台灣讀者。
我覺得,我是無比幸福的人。
自從二零一三年出席過台北國際書展後,我在每一次構思小說時都會掙扎,究竟應該寫貼近台灣讀者生活的題材,曾加共鳴感,還是寫關於香港背景的小說,帶大家縱橫香港這個小島的恐怖故事。
這個念頭直至我完成【靈異出版社】系列,收到明日邀稿寫文庫小說後,又再次在腦海纏繞著我。最終,經過反覆跟編輯討論,我決定以香港大學校園的恐怖都市傳聞故事,作為第一次跟文庫讀者見面的禮物。
但你要我平舖直敘寫「中文大學辮子姑娘」、「香港大學荷花池女鬼」、「城市大學半夜哭泣女生」等等鬼故事,我又做不到。因為要看這些都市傳說,只要打開Google Ghrome、Safari等瀏覽器,輸入關鍵字就不難找到。對於一個熱愛創作的小說作者,接受不到這種不經轉化,就直接就把它出版的方式,因為這會對不起一直每晚在網上留言打氣的讀者。
思前想後,這本文庫小說就面世了。
這本《通靈劫》(暫名)一方面貫徹我的寫作風格,希望透過傳聞中各間大學的都市傳說故事帶出人性之惡,另一方面亦想盡最大的筆力,利用全新故事呈現都市傳說中最詭異、最恐怖的畫面。而小說以跨越香港和台灣作背景,亦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設定。
每一次出版小說,對我來說都有著最後一次的覺悟,因為我不會知道,市場、讀者還會不會給予我下一次的寫作機會。輾轉經已在香港、台灣出版第二十四本小說,我盼望還會有第二十五、二十六……一直寫下去的恩賜。
感謝大家支持這本小說。
如果喜歡的話,不妨把我的書介紹給其他同學、朋友認識。
最後補充一點,這本《通靈劫》(暫名)的男主角歐陽劍崎,曾經出現在明日名家系列【靈異出版社】《嬰之契約》之內,而書中某些情節補完了《嬰之契約》某些空白,對有支持前作的讀者,是一點心意。
我們約定在下一本小說再見。
有緣的話,在Facebook搜尋「畢名」,可以在專頁上跟我談天說地交朋友。
小說作家 畢名
終於完成第一本明日文庫小說。
對一直有支持便利書或文庫的讀者來說,「畢名」這個名字可能會較陌生,但如果有捧場名家系列的讀者應該知道,我其實就是【靈異出版社】系列的作者,在明日已出版的小說有《畸羅之眼》、《嬰之契約》、《別殺我媽媽》、《恐怖病‧失蹤》及《鬼界夢劫》五本。
作為來自香港的海外作家,加入明日工作室這個大家庭很快就經已兩年,期間得到叔慧姐、令葳、君宇等同事的信任,令我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台灣恐怖書市的文化,亦令我有幸認識到不少愛書又可愛的台灣讀者。
我覺得,我是無比幸福的人。
自從二零一三年出席過台北國際書展後,我在每一次構思小說時都會掙扎,究竟應該寫貼近台灣讀者生活的題材,曾加共鳴感,還是寫關於香港背景的小說,帶大家縱橫香港這個小島的恐怖故事。
這個念頭直至我完成【靈異出版社】系列,收到明日邀稿寫文庫小說後,又再次在腦海纏繞著我。最終,經過反覆跟編輯討論,我決定以香港大學校園的恐怖都市傳聞故事,作為第一次跟文庫讀者見面的禮物。
但你要我平舖直敘寫「中文大學辮子姑娘」、「香港大學荷花池女鬼」、「城市大學半夜哭泣女生」等等鬼故事,我又做不到。因為要看這些都市傳說,只要打開Google Ghrome、Safari等瀏覽器,輸入關鍵字就不難找到。對於一個熱愛創作的小說作者,接受不到這種不經轉化,就直接就把它出版的方式,因為這會對不起一直每晚在網上留言打氣的讀者。
思前想後,這本文庫小說就面世了。
這本《通靈劫》(暫名)一方面貫徹我的寫作風格,希望透過傳聞中各間大學的都市傳說故事帶出人性之惡,另一方面亦想盡最大的筆力,利用全新故事呈現都市傳說中最詭異、最恐怖的畫面。而小說以跨越香港和台灣作背景,亦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設定。
每一次出版小說,對我來說都有著最後一次的覺悟,因為我不會知道,市場、讀者還會不會給予我下一次的寫作機會。輾轉經已在香港、台灣出版第二十四本小說,我盼望還會有第二十五、二十六……一直寫下去的恩賜。
感謝大家支持這本小說。
如果喜歡的話,不妨把我的書介紹給其他同學、朋友認識。
最後補充一點,這本《通靈劫》(暫名)的男主角歐陽劍崎,曾經出現在明日名家系列【靈異出版社】《嬰之契約》之內,而書中某些情節補完了《嬰之契約》某些空白,對有支持前作的讀者,是一點心意。
我們約定在下一本小說再見。
有緣的話,在Facebook搜尋「畢名」,可以在專頁上跟我談天說地交朋友。
小說作家 畢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