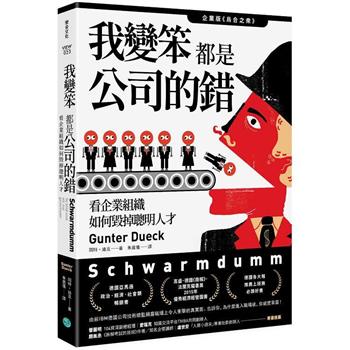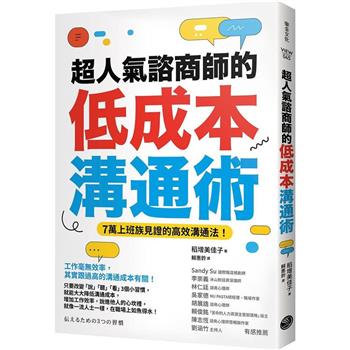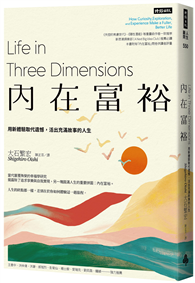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青春期就像一場漫長的不合作運動。」
一場無聊的翹課,看著浪花引出對世間萬物存在的感傷。
陷入瘋癲的表哥,彷彿就是帶來幸福的「白馬」?
連自己都無法撫養的輟學少女,撿到了一隻有白襪子的黑貓。
穿上玩偶裝後就再也出不來,彷彿真的變成了一隻熊的人類……
在劉子新的故事裡,每個人總有需要「逃避」的時刻,不論是被迫、或是主動的逃跑,而他們會在那些瞬間,細膩地向世界提問──那些規則、那些常識,都是這麼理所當然的嗎?
就是因為還存有好奇,所以在逃避之後仍然選擇回頭。
這是一場由劉子新所創造,沒有任何企圖的,盛大的逃跑。
★「怪物級新人」劉子新 首部短篇小說集
★獲第21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小說、散文雙首獎,新詩優勝
★朱宥勳、李欣倫──專文推薦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白腳底黑貓的圖書 |
 |
白腳底黑貓 作者:劉子新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5-22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5 |
迷誠品走進閱讀世界 |
$ 300 |
現代小說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文學作品 |
$ 300 |
迷誠品走進閱讀世界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白腳底黑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