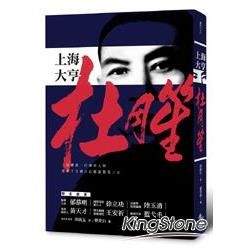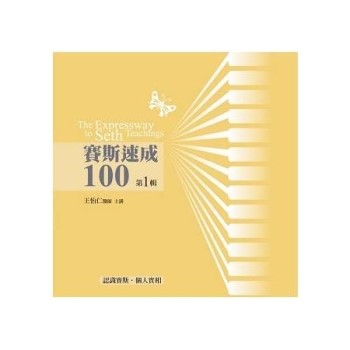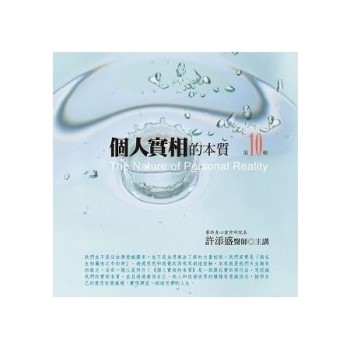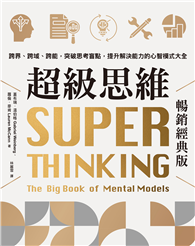序
一本被輕忽的重要傳記──寫在《杜月笙傳》之前
杜月笙(1888-1951),名鏞,號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富傳奇性的人物。不僅於他以一個來自鄉下的十五歲孤兒,單槍匹馬闖入上海灘,由一個三餐不繼的小混混,在小東門外十六舖水果行當一個小學徒,中年以後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威震上海灘的大亨;還在於他發跡之後的所作所為,儼然已由流氓白相人「脫胎換骨」,成為了現代實業家、社會名流與地方領袖,成為相當活躍的政治風雲人物。
杜月笙長袖善舞,對前清遺老、軍閥政客、黨國高層、社會名流,乃至金融工商鉅子,無不執禮甚恭,看他恂恂如也,鞠躬如也的周旋於達官顯宦群裡,揖讓於耆老縉紳中間,傾力結交,甚至結拜為把兄弟,或收為門生弟子,給予經濟支援,或月奉規銀,養為食客。而蔣氏高層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無不結為杜氏豪門密友。有這樣一張足以操縱政界、工商金融界的關係網,有法租界做靠山,杜月笙在上海灘可謂左右逢源、縱橫捭闔,一呼百諾,各方信服,萬姓輸誠,終成為一代人豪。
劉紹唐在談到《杜月笙傳》時說:「杜氏自稱『樸實無文』,因為他出身寒微而未受教育,終其一生沒有信函日記等材料遺留下來。中年以後,雖顯赫一時,對民國政治及政治人物有極重要的影響,也主持過許多大企業,但正式史料記載則絕無僅有。推其原因一方面由於杜氏具有謙沖的美德,許多事情由他出面解決,他卻不願別人在事後提起;另一方面,若干人士受杜氏之惠以後,往往有一種極微妙的心理,即在事後多不願、或不敢甚至不屑把杜某人的關係坦白地說出來。在這種『口說為憑』的情形之下寫傳記,最容易也最困難。容易者可以說『死無對證』;困難者眾說紛紜,各是其是,取捨為艱。」劉紹唐在出版這部由章君榖詳細採錄杜月笙身邊門人、親屬、好友等口述的杜月笙生平行跡,而擴展和演繹的《杜月笙傳》時,都已經有如此的感慨了,何況其餘呢?
因此坊間雖出版了大量的杜月笙傳記,或傳奇,它們都犯了一個嚴重的弊病,那就是游談之雄,好為捕風捉影之說,故事隨意出入,資其裝點。更有甚者,更以「遺聞」、「佚事」、「揭秘」為名,大肆謾罵、譏詆,遂行其某種政治目的。而其內容往往只是拾綴陳言,輾轉傳述,甚至以訛傳訛,離所謂歷史真相,真不可以道里計。
「傳記」雖然不全等於「歷史」,但它多少必須忠實於「歷史」。如果「傳記」不忠實於「歷史」,那不是「傳記」,而是「小說」而已。因此史學大師孟森(心史)說:「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並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為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辯也。」
而當今之所謂《杜月笙傳》者,可說都是後來者誇誇其談的,甚至都沒有人親見過杜月笙本人。即令名記者徐鑄成寫的《杜月笙正傳》,作者與杜氏也僅有一面之緣,其中的可信度有多少?實在令人懷疑。等而下之的寫杜月笙者,更令人不忍卒讀。但這其中有本一直被人輕忽的《杜月笙外傳》,是反而更有史料價值的。《杜月笙外傳》原刊登於香港《春秋》雜誌,登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出了單行本,作者署名「拾遺」,採「拾遺補闕」之意。他甚至在一開頭就故意與杜月笙劃清,不讓人有任何的聯想。後來我從金雄白的文章得知拾遺就是胡敘五的筆名,他正是杜月笙的中文秘書之一。杜月笙因不通文墨,後來很相信捏筆桿兒的人,為了做好文字工作,他請了翁佐卿(左青)、邱訪陌、王幼棠、胡敘五,四個人當秘書。其中翁佐卿是張嘯林的門生,由張介紹給杜的;邱訪陌,由陳群介紹的;王幼棠(曾任淞滬員警廳秘書)由劉春圃介紹的;胡敘五由黃炎培介紹(曾在上海地方協會任秘書)。而其中以胡敘五先生做的時間最久,胡敘五甚至一直跟隨杜月笙到香港。這事我也求證於杜月笙的女兒杜美霞女士。
金雄白說:「我一向認為寫像杜月笙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不失為極佳題材,但任何人有他的長處,也會有他的缺點,更何況於他。所以為杜氏立傳,褒貶之處,下筆頗難得當,而敘五以與他多年賓主之情,知道得多而翔實,評論得生動而中肯,文字的優美,反成餘事。」幾年前,我在上海見到杜月笙好友楊管北的兒子楊麟,他的書架上也有本《杜月笙外傳》,我問他對此書的看法如何?他說真實,尤其寫他父親的那段,真是親歷其境。
胡敘五因長期跟隨杜月笙,因此該書有極高的真實性,例如有關「高陶事件」,書中說:「月笙看過字條,深悉寄老(案:徐寄廎)為人,十分謹慎,如非千真萬確,落筆不致如此堅定。認為事不宜遲,利在速洽。即於翌晚飛往重慶,一面囑采丞留港稍候。其時蔣委員長適有桂林之行,原擬小駐,聞此密報,一宿還渝。召見月笙,前席專對。即囑月笙從速返港秘密進行。月笙返港後,又著采丞從速返滬。纔逾十天,溯老(案:黃溯初)蒞港。當將宗武(高宗武)去日經過、密約要點,逐一和月笙細說,並製成筆錄,俾月笙不致遺忘,得向當局詳陳。於是月笙在同一月內又作第二次重慶之行。」據徐寄廎〈《敬鄉樓詩》跋〉回憶:「時杜月笙君在港,與溯初無素,余為介紹,一見如故,爰偕赴陪都,以某事言之於當路。」而據蔣介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記云:「下午與俄使談外交,與月笙談汪事。」是胡敘五的記載真實不虛。
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杜月笙叫來胡敘五,說是要口述遺囑。時家人、好友均在室內,拭淚點頭。杜月笙這時已是兩頰凹陷,臉色白中透灰,說上幾句話就要大喘幾口氣。他緩緩說道:我已病入膏肓,行將離世,茲將所遺財產(包括現金、債券、不動產等),按具體分配方案,留給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繼承人要努力守成,艱苦創業,云云。杜月笙口述後,叫胡敘五重讀一遍,然後掙扎著簽上自己的名字「杜鏞」。老友錢新之、陸京土、顧嘉棠、吳開先、徐采丞五人,應杜之邀請,於遺囑上副署,監督以後遺囑的執行。八月十六日杜月笙病逝香江,一代人豪在此劃上句點。
胡敘五則孑身客寄香江,僅靠賣文為生。據金雄白說:「敘五狀貌如三家村學究,木訥又如一謙謙君子,對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即服膺勿替,說話帶有濃重的安徽土音,雖訥訥不出於口,但嫉惡如讎,極富正義感。他因曾為杜月笙佐筆政,過去時與俠林中人交遊,最難得的就是並未沾有此中習氣。敘五下筆輕盈,辭意茂博,如以貌取人,不信是出於其手。」一九七0年他病逝香港,身邊沒有一個家屬,也沒有一個親戚,寥寥十餘朋友,為他在殯儀館草草辦妥了臨終大典,就送往火葬場安葬。
是《杜月笙外傳》其史學意識、其文筆、其閱歷,足可作史,不宜等閒以內幕、秘聞之屬視之。為此這次重排出版特將書名更名為《杜月笙傳》(因已有徐鑄成的《杜月笙正傳》在先),並恢復其本名「胡敘五」及職位「杜月笙的秘書」,還其本來面貌,亦希望讀者更能重視此書之價值,它遠較之坊間誇誇其談的「杜月笙傳奇」,還是高明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