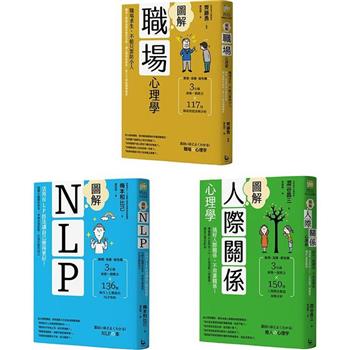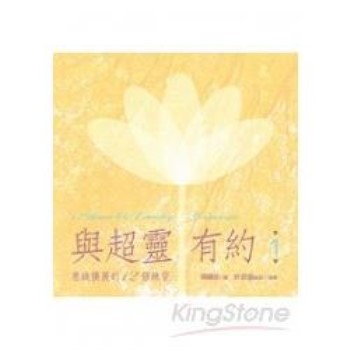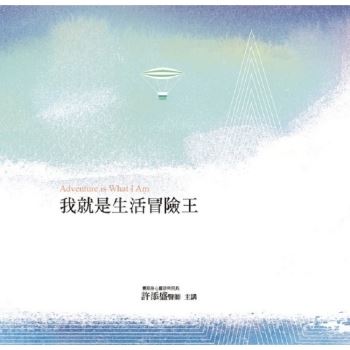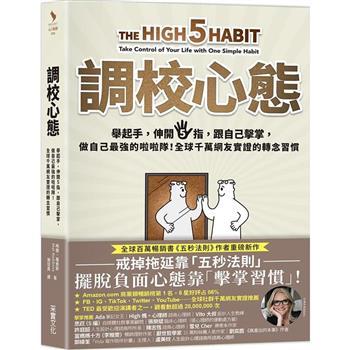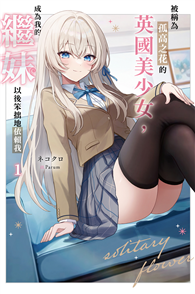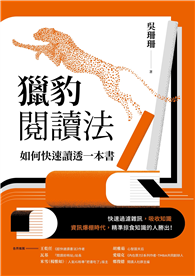第一部:生在大溪
孤獨感形成的真相
我出生在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現改一德里)的三板橋水利工作站附近。當地是廖家村,鄰居都是姓廖的人家(即廖厝)。我家是向前屋主買來的廖姓祠堂左邊護龍的房舍,因前屋主在此製茶,所以屋舍隔間很空闊,能讓小孩任意活動。從屋前向西方遙望,夕陽和晚霞會在如長城般隔斷的大漢溪對岸,緩緩消失,此時若向祠堂後面的東方山嶺高處回首,清涼夜空中的新眉月色和點點星光,會讓人產生諸多感觸或遐想。
我的父母皆為世居大溪鎮月眉灣江氏大宗族的童養子女,因我祖父早逝,祖母年輕守寡,為了經營所繼承的本房龐大田產,分別收養兩位童男童女,長大再予婚配。我曾有一位從未認識的姑姑,但對於她的容貌和年齡,完全沒有印象。所領養的另一對童男童女,即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大伯父老早死在菲律賓的某地,有關他的際遇,都是聽我母親說的;至於大伯母,我也是在多年後才認識她和領受其精明。她在落難後才帶著兩個男孫,來和我們同住。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年輕力壯且精於劍道的父親並未被徵調到南洋或中國戰場當兵。因為動用關係,及父親平素和日本警方交往密切,便得以「隘勇」的身分,協助日本警方駐守在北部泰雅族重鎮的角板山附近。
父親本業是裁縫師,技藝高超,容貌俊帥,是大溪鎮上公認的美男子。因平素喜歡練劍道和各種運動,加上家境富有,所以三教九流的朋友皆有。在大溪鎮仍流傳著,父親在南雅廳警部的武德殿競技,連敗十八名高手的光輝紀錄。而唯一擊敗父親的許振來,是大溪最資深的刑警、蔣總統大溪賓館的長期管區員警,則是日後我的岳父。
雖然如此,父親的婚姻始終潛藏著不安和分裂的危機。可以說江家日後的悲劇,都和這一不幸的婚姻有關。父親和母親是在日治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結婚。當時父親十八歲,母親十七歲。因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的七月七日,在大陸有所謂「盧溝橋事變」,日軍進攻華北,激起中國全面抗日的決心,展開長期(前後八年)對日抗戰。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也促使日本在臺灣加速同化政策,在島內展開所謂「皇民化運動」。
戰爭的危機感使得島內的民眾也跟著被迫動員。其中一部分臺籍壯丁被徵調至大陸戰場充當日軍的隨附軍伕,協助日軍作戰。為了逃離這種戰場勞役的徵調,父親要求和同為童養媳的母親結婚,然後設法到大溪附近的山區警部服務。不料這一要求,立刻被母親斷然拒絕了。母親拒絕的理由,是瞧不起父親的行徑,是個十足的浪蕩子弟,吃、喝 、玩、樂,樣樣皆精。
另一方面,母親未到江家之前,是黃家的長女,精明能幹,八歲到江家後,立刻獲得養母的賞識和歡心。不久,即成了養母的得力幫手,舉凡內外一切家務和田產收租的繁瑣事務,皆能處理得井井有條,宛若《紅樓夢》裡的「鳳辣子」王熙鳳一般。但也由於她大小權力一把抓,其他同被收養的二男一女,都對她有畏懼之感。這一由權力操控所形成的雙方緊張性,甚至導致日後彼此之間的情感疏離,不能合作無間。
先結婚的大伯父和大伯母,期待經由結婚成家,可以分得部分資產或擁有較大的家產支配權。後來發現,除非父親也能和母親結婚,否則所有大權不可能被釋放出來。父親也知道,除非有母親的精明和經濟方面的支援,否則他的活躍和光彩會迅速架空和黯然無光。可是,母親心儀從事運輸業的表兄,無意和父親結婚。
於是這件求婚與拒婚的風波,只有仰賴家族長輩的仲裁了。當時在月眉灣的江家,已是大溪僅次於李騰芳家族的大家族,土地廣大、物產豐饒,生活相當奢侈,據說由於經常宰殺雞鴨魚肉等,在江宅邊整條用來洗滌的溝水,整年都是帶著腥味和淡紅色。像這樣的地方望族,自然不允許子孫輩有公然反抗的行為。因此,養母只得敦請族中長老出面,要母親和父親一起到祠堂的大廳,跪在歷代江家祖先牌位前聽訓。家族長老首先指責拒婚的不當,因江家收養的目的就是要等長大成親,為江家繁衍後代子孫。如今撫養成人卻違背母命,是十足大不孝,要求母親在祖先面前親口答應婚事。於是在家族長老的嚴命下,母親噙著淚水,點頭答應和父親結婚。在此種強壓下才不自然結合的年輕夫婦,彼此之間潛伏著不確定的崩解地雷,不知何時會因被踩到而炸爛勉強美滿的被動婚姻。
由於要迅速擺脫拒婚風波所帶來的閒言閒語,母親除了交出家中經濟大權,也建議搬出月眉灣的江家,先到鎮上開一家裁縫店,儲蓄了一些資本,長子誕生後,父親又老毛病發作,經常不顧店裡的忙碌,還是如往昔一樣,到大溪街上找朋友們玩樂。畢竟店是靠老婆經營,在未脫離老婆的視線之前,他既勤勉又善良,加上好脾氣、好手藝,以及為人親切和慷慨,使他永遠不愁沒有朋友。這方面,老婆可能會羨慕他。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一切都充滿了不安全感。他接受老婆的建議到山裡服務,以避免被徵調到大陸或南洋。他往日擅長的社交關係,此時頗發揮作用。於是一對年輕夫妻帶著剛滿週歲的長子,順利地來到角板山山區。這裡是淡水河上游,也是原住民泰雅族的居住地區,據說名作家鍾肇政所寫的《插天山之歌》,即以這一帶的風土民情為寫作素材。雖是遠離大溪街上的繁榮生活,卻可以從山川秀麗的景色,以及悠閒的山地生活取得補償。
更何況,雖說到山區要防泰雅族作亂,父親卻早已在原住民部落裡交到一大票喝酒的夥伴,甚至和原住民婦女也處得不亦樂乎!公私兩便,沒什麼可抱怨。老婆對他的作為在結婚後漸漸學會不過於計較,免得雙方老是勃谿、爭鬧。同時,趁著在山上開銷少,可以多積蓄,母親利用戰時的配給品,像菸、鹽、糖等,跟原住民交換土產,像雞、鴨、竹筍或獵物等,經加工,再和駐山警衛交換配給品。除此之外,她也縫製衣服,賣給原住民。她在這一期間,有相當可觀的利潤落入口袋,荷包大為充實。這也是戰爭結束後,父母親可以迅速回到鎮上購買大批田產的原因。
在戰爭結束前兩年,次男英俊誕生了。至於排行老三的我,是戰後第二年在大溪鎮東郊農家出生。父母也從在大東亞戰爭期間避居生活幾年的角板山區,遷回大溪近郊人稱「廖厝」的新購一處自宅。但在戰後第二年才出生的我,因父母經濟已變得相當不錯,有請鄰婦當我個人的專屬保母,好照顧年幼還不會自行站立與獨立行走的我。儘管如此,在戰後一回大溪,即開始忙碌於經營田產的父母,無形中也逐漸疏遠了對我的關懷。
這對我的幼稚心靈,造成極深的負面影響,使我日後一直存有漂泊的不安全感,孤獨的心頭陰影,強烈地籠罩著幼年時期的我。
貪玩的代價
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爆發了所謂「二二八事件」。在大溪地區,有相當多外省住民遭到攻擊和凌侮。隔月,白崇禧來臺安撫,事件平息。但隨之而來的清鄉運動,使不少滋事的本地青年被槍殺在大溪橋下的沙洲上。其中被挾怨報復者,也不能說沒有。對忙於經營田產耕種的父親來說,幸好未被牽連,總算逃過一劫。這其實是非常僥倖的。日後我無意中發現,家中實際藏著武器。而且父親的結拜兄弟甚多,其中也可能有實際參與過「二二八事件」。只是時過境遷,這一切也就化為過眼雲煙了。
此年照顧我的,是鄰居守寡的阿波嬸。她是一位貧窮的佃農之妻,已五十幾歲了,有一大群兒女,是廖厝中較清苦的。她的兒女已大,到處為人幫傭或佃耕,她則替江家照顧我。因家住隔壁(向父親夫婦租屋),所以我是在阿波嬸的背上,度過最初童年。
一九四八年,我漸會自行遊戲,穿開襠褲的我開始在家中庭院到處玩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之前的屋主為了製茶需要,將屋宇建得很高大寬闊,一間接一間,彷彿走不完似的。屋內的天井中有一囗淺水井,沒有裝井圈,一探手,即可接觸到井水。我的哥哥在井中放養了烏龜,頗引起我的興趣。
這年秋初,阿波嬸回家煮飯,放我一人在天井的空地上自行玩耍,我先好奇地走近井邊,對著井水照出自己在水中的臉影。正興奮的當兒,忽然看到烏龜浮出水面,彷彿在水底沉太久,需要透氣似的,同時四隻龜腳也輕划著井水,以防有緊急狀況時,可以迅速逃走。這樣一來,更挑起兒童的好奇心,就好像小貓在戲弄老鼠一樣,我不自禁地伸手要抓烏龜,烏龜則趕忙潛回水中。可能是清澈的水裡映著白雲藍天,使我忘記了井深一丈多,心一急,怕烏龜逃走,也跟著躍向龜潛水處,雖然烏龜是抓著了,人也噗通一聲掉在水裡。
正在水中驚慌掙扎的當下,我吃了好幾口井水。幸好母親回家來提茶水,正好聽到井中有掙扎聲,趕快衝到水井邊一看,馬上看到我掉在井裡,已快要下沉到井底,趕忙朝水中一撈,抓住小孩的衣服,提了上來,但她發現我當下雖然嚇得哭出聲,兩手還是牢牢抓住烏龜沒放掉。母親一面把烏龜搶過來丟掉,一面怒責在隔房煮飯的阿波嬸,告訴她由於她的疏忽,差一點讓小孩子淹死在井裡。阿波嬸只好惶恐地一再道歉。最後還是請人收驚,此事才告一段落。
按照當時的習俗,母親也替大哥義雄領養了一個童養媳,叫邱花子。花子的父親叫蔡林達,母親叫邱銀,從母姓,是靠替人打工為生的窮家子女。她在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從鄰近溪邊的樵寮埔被領養到江家,一方面準備日後和大哥義雄成親,一方面來接替阿波嬸,負責照顧我。到江家後,「花子」改稱「秋菊」。
這一年,也因國軍在大陸的戰爭中節節失敗,大批軍隊和難民,相繼撤退渡海來臺。為了穩定島上的政局和治安,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在五月二十日下令實施戒嚴,並開始逮
捕大批逃到臺灣的大陸籍而未報戶口的僧侶,以「無業遊民」的罪名加以審訊。才四歲的我絕未想到,再過四十四年後的自己居然會撰寫論文,揭發這一段僧侶受難的插曲。
事實上,這一年也是我的不幸年。
這一年秋末,由於秋菊貪玩,疏於照顧我,導致我被停放在稻田中的打榖機,將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幾乎完全彈裂和彈斷。當時,鄰居的小孩和秋菊帶著我到稻田裡玩,看到打穀機停放著,便慔仿大人收割時的動作,先用腳踩踏板,驅動帶角齒的轉輪,然後將田中的稻草成束地放進打穀箱內讓帶齒的轉輪彈打,就好像農忙峙,大人在彈打稻把上的穀粒一樣。
當較大的孩子玩得興高采烈的當兒,沒留意到較小的孩子也在旁跟著模仿,一樣拿著稻草把,悄然靠近,將手伸向快速轉動的打榖滾輪,結果當稻草把接觸轉輪時,輪上彈打稻草所產生的強大內拉力,將我拿著草把的右手往箱內帶,就在那一瞬間,右拇指和食指分別被打得肉綻骨碎,鮮血直流,痛得我哀號大叫不已。
其他小孩看見這種情形,趕快將我背起來離開現場,也嚇得大聲喊叫,大人聽見了,紛紛從家裡衝出來,奔向小孩的叫聲處,才發現我的右手指部分血肉模糊,傷勢嚴重,必得趕快處理。經送往街上的醫院處理後,將裂開的大拇指縫合,碎了中節指骨的食指先挑去碎骨,然後指尖的一節縫到手指根上。也由於這個緣故,我的食指只有常人的一半長度,而且因缺乏關節,右手第二指指尖的一節從此未隨年齡發育,仍保留著四歲時的小孩手指;而手指和手掌相連的部分,則粗壯和常人無異。大拇指縫合的裂痕,長大後依然清晰可見。以後雖然痛苦消失了,但拿筆寫字時,必須倚賴中指和大拇指,所以用力很大,常有將筆尖折斷或折彎的情形。用右手三指行童子軍禮時,也會被不知情的教官懷疑為什麼少了一根指頭?惹得同班同學笑話不已。不過,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不便之處。長大一樣當兵,一樣可以用中指開槍。說起來,
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的圖書 |
 |
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 作者:江燦騰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4-12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45 |
人物傳記 |
$ 277 |
Books |
$ 277 |
Books |
$ 277 |
Books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現代散文 |
$ 315 |
現代散文 |
$ 315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
一個曾中輟失學十八年的產業技術勞工,之後像變魔術一樣蛻變成臺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優質文學博士;爾後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正教授退休將近十年,還年年持續勤奮治學又不斷發表新作品。本書就是講述他的堅毅奮鬥人生傳奇。
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教授曾說:
「江燦騰,對人熱誠,對事執著,所以在論述之際,常赤裸裸地將內心的感受,形之於文或出之於口,因此不知不覺中,也遭某些人的猜忌。」
大陸著名學者葛兆光認為其:
「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常常從歷史的縫隙處切入,找到新的問題。」
大陸首席宗教學理論家呂大吉教授,在分析作者的為學與做人時,更深刻提到:
「犀利如刀的的言詞反映了他觀察的敏銳,嚴苛的評價反映其思考的深度,快人快語可見其天性的單純與赤誠,不善交際可見其不媚於俗的赤子之心。」
作者簡介:
江燦騰
1946年生,桃園大溪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教清大、臺大、擔任新文豐佛教化叢書主編等,現已退休。
學術著作:《晚明佛教改革史》、《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灣佛教史》、《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臺灣民眾道教三百年史》、《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風城佛影的歷史構造:三百年來新竹齋堂佛寺和代表性人物誌》等十多種以上。
學術榮譽:
榮獲八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紀念獎。
第一屆宗教學術金典獎得主。
第二屆臺灣省文獻傑出工作獎得主。
章節試閱
第一部:生在大溪
孤獨感形成的真相
我出生在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現改一德里)的三板橋水利工作站附近。當地是廖家村,鄰居都是姓廖的人家(即廖厝)。我家是向前屋主買來的廖姓祠堂左邊護龍的房舍,因前屋主在此製茶,所以屋舍隔間很空闊,能讓小孩任意活動。從屋前向西方遙望,夕陽和晚霞會在如長城般隔斷的大漢溪對岸,緩緩消失,此時若向祠堂後面的東方山嶺高處回首,清涼夜空中的新眉月色和點點星光,會讓人產生諸多感觸或遐想。
我的父母皆為世居大溪鎮月眉灣江氏大宗族的童養子女,因我祖父早逝,祖母年輕守寡,為了經營所繼承...
孤獨感形成的真相
我出生在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現改一德里)的三板橋水利工作站附近。當地是廖家村,鄰居都是姓廖的人家(即廖厝)。我家是向前屋主買來的廖姓祠堂左邊護龍的房舍,因前屋主在此製茶,所以屋舍隔間很空闊,能讓小孩任意活動。從屋前向西方遙望,夕陽和晚霞會在如長城般隔斷的大漢溪對岸,緩緩消失,此時若向祠堂後面的東方山嶺高處回首,清涼夜空中的新眉月色和點點星光,會讓人產生諸多感觸或遐想。
我的父母皆為世居大溪鎮月眉灣江氏大宗族的童養子女,因我祖父早逝,祖母年輕守寡,為了經營所繼承...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無悔人生的往日歷程
年過古稀又五,猶能有新著問世,特別欣喜。就像面對美麗的夕陽,衣襟雖被冰冷的晚風習習吹拂,但我環顧天地間視野時,遼闊世界依舊,且能察覺自己身體的清晰感覺與思維敏銳且專注。因而處在此時此境中,依然心際優遊自在,愉悅無比。就像再次體驗令人珍惜的歡快時光之旅,讓記憶更鮮活銘刻,回味也更綿遠無窮。
回想從半世紀前, 我從世居桃園大溪的故鄉, 在當兵退伍之後, 隻身來到新竹縣竹北鄉的大外商荷蘭臺灣飛利浦電子公司竹北廠擔任機房操作員近二十年(一九七一
一九八九),如今(二○二一)此地已是嶄新...
年過古稀又五,猶能有新著問世,特別欣喜。就像面對美麗的夕陽,衣襟雖被冰冷的晚風習習吹拂,但我環顧天地間視野時,遼闊世界依舊,且能察覺自己身體的清晰感覺與思維敏銳且專注。因而處在此時此境中,依然心際優遊自在,愉悅無比。就像再次體驗令人珍惜的歡快時光之旅,讓記憶更鮮活銘刻,回味也更綿遠無窮。
回想從半世紀前, 我從世居桃園大溪的故鄉, 在當兵退伍之後, 隻身來到新竹縣竹北鄉的大外商荷蘭臺灣飛利浦電子公司竹北廠擔任機房操作員近二十年(一九七一
一九八九),如今(二○二一)此地已是嶄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無悔人生的往日歷程
致讀者
第一部 生在大溪
孤獨感形成的真相
貪玩的代價
生命、韓戰之體悟與啟蒙
七歲秋寒覺醒
兄長們
雙面的小學風景
鮕呆生涯
夢魘
庭園中的芭樂樹
巴陵峰頭春意濃
《冷暖人間》與我
謎樣的父親
婚姻與情慾
輟學與長期孤寂自學
第二部 走出大溪
淡水人情
這裡沒有小姐
青春玫瑰心影
蘇格拉底門徒的告白
胡適的死亡和李敖的崛起旋風
練字、習字
入伍前
從王少校到水月法師
代筆情書與越級指導寫作
失聯黨員、反共義士與左派書
驚險經驗談
食色,性也
第三部 來到竹北
竹北...
無悔人生的往日歷程
致讀者
第一部 生在大溪
孤獨感形成的真相
貪玩的代價
生命、韓戰之體悟與啟蒙
七歲秋寒覺醒
兄長們
雙面的小學風景
鮕呆生涯
夢魘
庭園中的芭樂樹
巴陵峰頭春意濃
《冷暖人間》與我
謎樣的父親
婚姻與情慾
輟學與長期孤寂自學
第二部 走出大溪
淡水人情
這裡沒有小姐
青春玫瑰心影
蘇格拉底門徒的告白
胡適的死亡和李敖的崛起旋風
練字、習字
入伍前
從王少校到水月法師
代筆情書與越級指導寫作
失聯黨員、反共義士與左派書
驚險經驗談
食色,性也
第三部 來到竹北
竹北...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