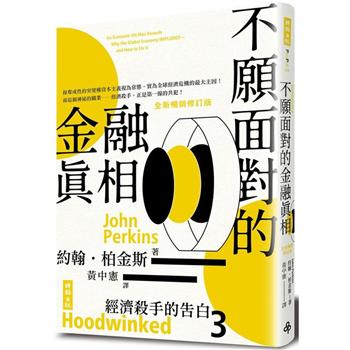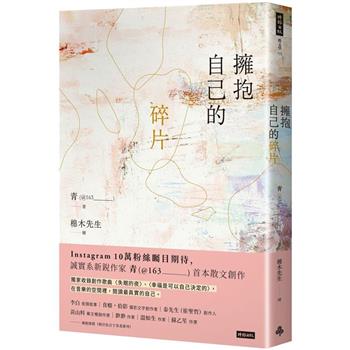他們傳承的不僅是一項技藝,更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宇文正(聯合報副刊主編)
吳懷晨(詩人、大學教授)
高翊峰(小說家)
童偉格(小說家)
廖偉棠(詩人)
——一致推薦
他們在漫漶、脫損的紙頁間彌縫貼補,窮盡心血與手段,為的卻是「整舊如舊」,只希望讓書冊能保有時間留下的印痕。在如草的鬚髭青絲裡俐落翻飛的剃刀和髮剪,理髮師傅打理的不止是他人的門面,更召喚著理想中那個光彩閃耀的自己。無數次反覆摔打中緩緩成形的守護神獸,守望著人們在亂世中對平安的冀望,同時守候著一個家族榮衰合離的悲喜……
精熟各種技藝的人們,透過自己的一雙手和藉之演現的手藝,撐持的不僅是自身的溫飽,也撐起一整個時代的記憶。然而在科技奔騰的年代裡,匠人們卻逐漸被世人遺忘;人們忘了如何體會一門圓熟技藝的可貴,或是那迢遞傳衍下來的手感溫度。
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手藝人」的作品,也是對手工時代最深情的回眸。作者藉由三位不同藝匠的故事,刻畫不同匠人的技藝和屬於他們的年代,還有歲月流轉沖汰的無情。用最雋永真摯的文字,向那個時代溫柔道別。
三則以手藝渡己渡人的故事,那是修復的故事,傳承的故事,也是時間的故事。小說家葛亮,正是以小說這門最精巧最神祕的手藝渡己渡人啊!
——宇文正
《瓦貓》以敘事出入匠師軼事,補綴了時間,暗渡了歷史陳倉;動靜一源,往復無際,葛亮的小說手藝讓人折服。
——吳懷晨
作者簡介:
葛亮
作家,學者。 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文學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燕食記》、《北鳶》、《朱雀》、《瓦貓》、《七聲》、《戲年》、《問米》、《謎鴉》、《浣熊》,文化隨筆《小山河》、《梨與棗》,文學評論《此心安處亦吾鄉》、《繁華落盡見真淳》 等。作品譯為英、法、義、俄、日、韓等國文字。
曾獲「中國好書」獎、 「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台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長篇小說代表作兩度入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 作者獲頒「2017 海峽兩岸年度作家」、《南方人物週刊》「年度中國人物」。
章節試閱
江南篇:書匠
不遇良工,寧存故物。
——明 周嘉胄《裝潢志》
一.簡
借人典籍,皆需愛護,
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北齊 《顔氏家訓•治家》
我遇到簡,十分偶然,是因為我的朋友歐陽教授。
歐陽教授是個很有趣的人。這有趣在於,他經常興之所至,出現突如其來的舉動。作為一個七十多歲的人,他經常會自嘲說,這就是老夫聊發少年狂。
這一年大年初三,我照例去他家給他拜年。歐陽教授,其實是我祖父的學生,在中央大學學藝術史,後來又在祖父的母校杭州國立藝術院執教。祖父早逝,他作為門下得力的弟子,對我的父親盡過兄長之責。我父親對他便格外尊敬。後來他移民香港,而我成人後又赴港讀書。每到年節,我父親便囑咐我去看望他。
歐陽太太是紹興人,到了香港三十多年,早就烹得一手好粵菜。間中,仍然拿出加飯酒,溫上。歐陽教授便與我對飲。我不是個好酒的人,但歐陽喝起酒來,有太白之風。剛剛微醺,行止已有些豪放。忽然站起身來,引吭高歌。自然還是他的招牌曲目——《費加洛的婚禮》中的詠嘆調「再不要去做情郎」。歐陽太太放下筷子,和我對視了一下,搖搖頭。目光中帶著縱容和無奈。歐陽教授卻俯下身,將一塊椒鹽石斑夾起來,放到我的盤子裡。同時並沒有停下喉間震顫的小舌音。我自然沒有吃那塊魚,因為照例很快到了高潮,是需要鼓掌的。
然而,這酒勁來得快,去得也快。到了家宴的尾聲,我們都知道,餘興節目是展示歐陽教授近來的收藏。教授很謙虛地說,毛毛,我這一年來的成果,很一般。市面上今不如昔,能見到的不是新,就是假。
說罷,便在太太的攙扶下,搖搖晃晃地引我去他的書房。
歐陽有一個很令人羨慕的書房。尤其在香港這樣寸土寸金的城市,居然有三面靠牆的通天大書架。書桌則對著落地玻璃窗,可觀得遠山點翠。歐陽常為此顧盼自雄,稱自己有遠見,早早搬離了中心區,在新界置業,才不用受逼仄之苦。他的藏書雖不至汗牛充棟,但在我一個青年人看來,確有洋洋大觀之象。據說這只是數分之一,有些善本書,因為要防香港的潮濕和久存的書蠹,送去了專業的倉儲。
我抬頭看見,歐陽親書的大篆「棗莊」二字,懸在書桌上方。這是教授書房的名字,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教授是山東人,棗莊確是他的故里。然而還有一層深意,確是凡俗學淺之人未必能領會的。舊時刻書多用梨樹與棗樹,作為書版,取其緻密堅固。刊印書籍也稱「付之梨棗」。教授將其書房命為「棗莊」,便有以一室納萬卷之意,可見過人氣象。
歐陽教授拿出一只匣子,打開來,撲鼻的塵味。說,去年七月在東京開研討會,結束了就去鎌倉逛了一遭。在臨街瓷器店裡,看到有人寄售。這套《水經注圖》,全八冊,可惜少了第三冊。不過打開來,有楊守敬的批注,算是撿了個漏。
我討喜道,老輩兒人都說呢,收藏這事像盲婚盲嫁,大半靠運氣。
教授說,可不!有心栽花花不開。春天時候,西泠放出一箱璧園會社石印《吳友如畫寶》,我可上了心,竟然沒有拍到。
還有這個,也是造化。在上環飲茶,說是中大一個老夥計要移民,把家裡的東西盡數出讓。我是趕了個大晚集。但這個收穫,算是藏家小品,卻很有意思。我看到他拿出殘舊的一些紙頁,打開來,是竪版印刷。教授說,這是六十年代香港「友聯」出版的「古文活頁」。
我問,友聯,是出過張愛玲的書嗎?
他說,正是。這個活頁是仿照歐洲傳統出版方式推出的。當時在香港很風行,特別在年輕學生裡。數十頁成章為一份,讀者逐份購入,輯錄成冊,再自己找釘書公司釘裝。歐洲出版社,經常只印不釘,叫Temporary Cover。老時候的香港也有。你瞧這個,釘書公司潦草得很,完全西洋的釘法。外頭是假書布,裡頭這個還是以往線裝書的版式。我打算重新整一下。
對了,毛毛。上次聽你母親說,找到老師的手稿,可帶來香港了?
我說,是。包裹在一大袋子生宣裡。杭州那邊的檔案室要清理,這才發現。
歐陽說,謝天謝地。當年從江津寄過來時,還是我接收的。做夾板,先師《據几曾看》的書名,也是我拓的。後來竟然遺失了。保存得可還好?
我說,那些宣紙都發了霉,書稿也受了潮氣,還好外面有一層油紙,又用木夾板包著。只是書頁有些黏連起來。
我打開手機,給他看書稿的圖片,說,一個台灣的出版人朋友,想拿去掃描。但又怕毀了書。
歐陽看一看,先皺起眉頭,但很快又舒展開,笑道,不打緊,這才是睡覺有人遞枕頭。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說完,他收拾起那些活頁,又在書架上上下下地找,找出一本書,一起小心翼翼地放進背包裡去。
然後對太太說,晚飯不吃了,我帶毛毛去一趟上環。
歐陽太太正端了一缽楊枝甘露,嘆口氣說,你呀你,說風就是雨。可有半點長輩的樣子。今天可是大年初三,你也不問問人家在不在。
教授說,怎麼問,她手機都不用,電話不愛聽。現在發電郵恐怕也來不及。
歐陽太太追上一句,好歹我辛苦做的甜品,吃了再去。
教授拉著我,頭也不回地往外走。
歐陽教授喝了酒,不能開車。雖然到了樓下,風有些凜冽。酒已經醒了一大半。等了許久,也沒有一輛出租車。我們只好走到更遠的地方,去坐小巴。
大年初三,車上並沒有什麼人,倒好像我們包了一輛車。
教授依然很健談,說起以前在央大的往事。說我祖父的不苟言笑,令人生畏。祖父開的「宋元藝術史」,最初報名的有二十多個學生。因為他太嚴苛,到學期末,只剩下了七個。「不過,我大概學到最多東西的,還是你爺爺的課程。用現在的話來說,一點都沒有放過水。筆記簡直可以直接出版。但時下,恐怕這樣上課是吃不開了。如今上課得像說書,不講點八卦,哪裡會有學生來聽。」
歐陽忽然定定地看,幾乎讓我不自在起來。他說,毛毛,你長得可真像你爺爺。不過看上去可隨和多了。對了,你聽說過他老人家年輕時的羅曼史嗎。哈哈,想起來了,你知道的,在你的小說裡看到過。
他促狹地眨一眨眼睛。
我這才問,我們要去見什麼人。
教授想了想,說,書匠。
我有些不得要領,重複說,書匠?
嗯,經她手,讓你的書煥然一新。不,煥然一舊。教授笑著說。
小巴在半山停下,不遠處是煙火繚繞的天后廟。還在年裡,自然是香火鼎盛。我們沿著扶手電梯,穿過整個Soho區,又爬上好一段階梯。景物漸漸變得有些冷寂,不復過年時候應有的熱鬧。我博士在港大念的,這一帶算是熟悉。但居然四望也有些茫然。歐陽畢竟年紀大了,終於氣喘。我替他背了包,一邊攙扶了他。教授這時候有些服老,說,這路走得,像是去西藏朝聖。自己開車停在羅便臣道,下來倒方便些。
我們兩個,都沒了說笑的興致。人是越來越少,兩側的房屋依山路而建,尚算整飭,也很乾
淨。但紅磚灰磚,都看得出雕落。畢竟是在山上,看得見經年濕黴和苔蘚灰黃乾枯的痕跡。教授終於說,哎呀,歇一下。
我們便在台階上坐著,回望山下。竟可以看見中環的景貌。中銀和IFC都似樂高玩具的一樣形容。陽光也淺了,這些建築間,便見繚繞的游雲。教授笑道,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啊。
我一聽,心倏然一涼,趁不上教授的浪漫。此情此境吟賈島,想起上兩句,實有些不祥。
再接再厲,我們終於走到了一幢小樓前。這樓比較鄰居們的,模樣有些奇怪,顯得狹長。有個很小的陽台,幾乎只能稱之為騎樓。鑲著巴洛克式樣的鐵藝欄杆。上面有一叢火紅的簕杜鵑,倒開得十分茂盛,垂掛下來,將陽台遮住了一大半。
教授按一按底下的門鈴。我看到門鈴旁邊的郵箱上,鐫著黃銅的JL的字樣。應該是主人名字的縮寫。
門開了,是個矮胖的南亞姑娘。看見教授,眼睛一亮,開始用歡快的聲音向他打招呼,並且擁抱。教授居然也熱烈地響應。兩個人用我不懂的語言交談。是那種高頻率的鏗鏘的音節。姑娘引我們進去。教授輕聲對我說,這是他們家印傭吉吉。吉吉聽到自己的名字,嬌俏地向我眨一眨眼睛。我說,教授,我不知道你還會印尼語。教授略得意地說,兩年前學的,所謂藝不壓身。
我們順著狹窄的樓梯走上去,腳下是吱呀的聲響。彷彿往上走一級,光線就黯淡了一點。
走到二樓,吉吉敲了敲門,用英文說,歐陽教授到訪。
裡面也用英文說,請進。
房間裡,很暗。四圍的窗簾都拉著,只開了昏黃的一盞頂燈。有濃重的經年的紙張與油墨的味道。這味道我不陌生,每次打開箱子,檢點爺爺的遺物,都是這種味道。但在這主調之外,還有一些淡淡的樟腦與腐敗植物的氣息。
我的眼睛適應了光線,看見房間裡碩大的寫字台後,坐著一個女人。
Surprise!哈哈,我就知道你在。教授的情緒延續了在樓下時的熱烈:看我還記掛著。給你帶了朗姆酒和年糕。等會讓吉吉煎了吃。過年嘛,年糕就酒,越喝越有。
不知為什麼,我有一些尷尬。並不在於教授即興地修改了中國的民諺。而是,他這番長篇大論,好像是在對著空氣說。對方始終靜默著。
恭喜發財。終於,我們聽到了一句廣東話的祝福。聲音冰冷而乾澀,聽來是有多麼的言不由衷。
我這才看見,這女人的面容已經蒼老了。乾瘦,有很深的法令紋。這樣的面相,往往顯得嚴厲。但她的眼睛很大,而且目光倦怠。因此柔和了一些。她穿著有些發舊的藍花棉袍,披著厚披肩,是深冬的打扮。但這裡畢竟是香港,雖說是過年,氣溫其實很高。她手裡執著一柄刀,正在裁切一些發黃的紙。她將那些紙靜靜地收下去了。
桌子上有一些我沒有見過的器具。有一只像個迷你的縫紉機;另一個似乎是那種切割軸承的機床。還有一個像是小型的絞架,上面還墜著繩索。
簡。我給帶你帶來了一個年輕的朋友,毛博士。
我的目光正在那些機器上盤桓,一愣神,聽見教授提到我,這才有些倉促地一低頭,說,您好。
這個叫簡的女人抬起臉看我一眼,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
這時候,吉吉推門,端著茶盤進來。女人揚手,請我們在沙發上坐下。
我坐下來,端起茶。茶具是歐洲的琺瑯瓷,描著金。有些鳶尾花枝葉漫溢到了茶杯口。
但是沙發有些不舒服,我隱隱覺得裡面的彈簧,在硌著我的屁股。沙發想必用了很多年了。
教授婉拒了吉吉讓他加塊糖的好意,說「畢竟自己已經年紀大了」。
他說,簡,我要好好地謝謝你。上次修復的《水經注圖》,惹得很多人眼饞。特別是那只布面的函套,都以為是原裝的。哈哈。
簡說,第五冊,有一根紙捻我忘記去掉了。
教授說,不打緊。我這次帶來一些友聯出的「古文活頁」,你幫我看看。
簡接過來,湊著燈光看看,說,裡頭線裝,外頭是西歐 Temporary Cover。不倫不類。再說,不過幾十年前的東西,也不值得費周章了。
教授笑笑說,算是我收藏的一個小品,取其有趣。
簡點點頭。
教授又說,另外呢,毛博士的祖父,是我讀大學時候的教授。最近新發現了一份手稿。有些散頁黏連了,也想要勞你的大駕。
簡看看我,說,我不幫人補手稿。修壞了,賠不起。
教授說,這份手稿,對我們挺重要的。是我的恩師呢……
簡倦怠的眼睛閃了一下,繼而黯沉下去。她說,是你的恩師,不是我的。
這句話,說得很突兀沉重,並不是舉重若輕的口氣。這時候,連達觀隨和的歐陽教授,臉上都掛不住了。
此時,不知哪裡,有一隻灰色的貓,跳到了教授的身旁,蹭了蹭他的腿。是隻英國短毛,牠抬起眼睛,眼神十分陰鬱。
教授趁勢起身,對簡說,天不早,那我們不打擾了。
我連忙也跟著起身。但胳膊一抬,不小心碰到了身後的書架。一冊精裝書掉到了地上。我急忙撿起來,將書頁撣一撣,闔上。嘴裡說著「對不起」,又放回書架上去。
好在簡並未說什麼,她讓吉吉送客。
吉吉將我們送到樓下。關上門之前,忽然用蹩腳的廣東話跟我們說「新年快樂」。聲音還是歡天喜地的。
我們沿著山道望下走,歐陽教授回過身,又看了看那幢房子,嘆口氣。
天色已經徹底暗下來了。萬家燈火,唯獨那個房子黑黢黢的,因為拉上了厚厚的窗簾。
還在年關,半山上的許多餐廳,都沒有開門。走進一家很小的壽司店。一個梳著油頭、面容和善的大叔,招待了我們。
我們坐定下來。歐陽教授喝了一口茶,說,她或許是因為痛風……
我急忙說,沒關係。
我知道教授是因為他的引見,有些不過意。
教授說,不過呢,話說回來。有手藝的人,總是脾氣特別些。在這一行,簡有資本。她是英國書藝家協會的會員,The Society of Book Binder,香港唯一的一個。
我認識她很早,那時她在灣仔開了一家二手英文書店。她幫我找到過幾本孤本書。後來因為不賺錢,也倒閉了。
教授接過大叔遞來的味噌湯,沒再說什麼。
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了歐陽教授的電話。
教授說,毛毛,簡讓你帶著老師的書稿,去她那裡。
我一時沒晃過神,問,讓我去?
教授說,對,我也納悶,是什麼讓她改變了主意。
依然是熱情的吉吉引著我,走上咯吱作響的樓梯,進入昏暗的房間。
我聽到了簡的聲音。乾澀,但比前次柔和,招呼我坐下。
她站起身,走到了窗戶跟前,將窗簾拉開了。光進入了室內,也照到了她的臉上,她微闔了一下眼睛。我這才看清楚了簡的面目。青白的臉色,是因終年不見陽光。其實她並不如印象中蒼老。光線平復了她的一部分皺紋,這其實是個清秀的人。
簡轉過身來,對我說,歐陽上次拿來的那套「古文活頁」,我整好了。麻煩你幫忙帶給他。
我接過來,看到Temporary Cover已經釘成了傳統線裝,融合宋款和唐朝包背。我由衷地說,漂亮得多了。
簡搖搖頭,說,裡頭我就沒辦法了。內頁是木質紙,纖維短,太容易氧化,脆得很。所以用了修復紙夾住,做成了三明治。這種西式蝴蝶頁,開卷加上「Waste paper」總算牢固些。說到底還是中西合璧,只比原先調了個個。
我將爺爺的書稿拿出來。她戴上眼鏡,小心翻開來,慢慢地看了一會兒,說,書法真是好。歐陽說,令祖父是在杭州國立藝術院讀書的?
我點點頭。她說,我舅舅以往在西泠印社。他們可能會認識。
你放心的話,這份書稿,我先洗一下,除除酸。她說,民國的書,紙張教人頭痛,稍翻翻就脆斷、發黃。你爺爺用的是竹紙,上好成色,他是個行家。
她隨手將桌上一本還在修的書,翻給我看,說,紙壽千年,絹壽八百。你看,這是光緒年的書,還蛀成這樣。有些宋版書用純手工紙,品相卻好很多。這就是所謂新不如舊。
我發現她的話,比預想中的多,我不知如何應對。
我說,那就拜託您了。這書稿受了潮,黏連在一起。我有個朋友還記掛著要掃描,時間可能會趕些。
她說,不妨事。一個星期來拿。
我謝謝她道,那太好了。爺爺留下的,獨一份。交給您就放心了。歐陽教授也說,您到底是看重和他的交情,我是沾了光了。
簡微笑,搖搖頭。
她往前走了幾步,從靠門邊的書架抽下了一本書,對我說,還認得嗎?讓我回心轉意的是這本書。
這是一本精裝的英文書,我看一眼書名。是一本心理學的論文選集,感覺不到有什麼特別之處。
她說,那天你把這本書碰掉在地上。還記得你撿起來的時候,做了什麼。
我仍舊茫然。
簡慢慢說,當時雖然倉促,但是你還是把這本書的Dog ear捋捋平,才闔上書。看得出是順手,下意識的。
我這時才恍然,她說的「狗耳仔」,是指翻看書頁無意折起的邊角。我對那一剎那毫無印象,或許只是出於本能。
簡說,我想,這是個從小就惜書的人。年輕人,你要謝謝自己。
我知道此時,自己走了神。因為簡的話,讓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
江南篇:書匠
不遇良工,寧存故物。
——明 周嘉胄《裝潢志》
一.簡
借人典籍,皆需愛護,
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北齊 《顔氏家訓•治家》
我遇到簡,十分偶然,是因為我的朋友歐陽教授。
歐陽教授是個很有趣的人。這有趣在於,他經常興之所至,出現突如其來的舉動。作為一個七十多歲的人,他經常會自嘲說,這就是老夫聊發少年狂。
這一年大年初三,我照例去他家給他拜年。歐陽教授,其實是我祖父的學...
作者序
自序:物是
打算寫關於手藝人的小說,是久前的事了。
與這個人群相關的,民間常說,藝不壓身。學會了,便是長在了身上,是後天附著,卻也就此與生命一體渾然。
談及手藝,最初印象,大約是外公家裡一只錫製的茶葉盒,上面雕刻遊龍戲鳳,久了,泛了暗沉的顏色。外公說是以前經商時,一個南洋商人的贈與。我記事還在用,春天擱進去明前的龍井茶,到中秋泡出來還是一杯新綠。少年時,大約不會關注其中技術的意義,但仍記得那鐫刻的細緻。龍鬚躍然,鳳尾亦搖曳如生。後來,這只茶葉盒不知去向。外公每每喝茶,會嘆息,說時下所謂真空包裝,其實是將茶「養死了」。在他看來,茶葉與人一般,也需要呼吸。這茶葉罐便如皮膚,看似容器,實則接寒暑於無間。一鱗一焰,皆有溫度。而今機器所製,如何比得上手工的意義。
數年前寫《北鳶》,書名源自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中一章—《南鷂北鳶考工志》。這一番遇見,也是機緣。不類《紅樓夢》的洋洋大觀,《廢藝》是曹氏散逸的作品,得見天日十分偶然。據馬祥澤先生回憶,這既是中日文化間的一段流轉,但也終於有殘卷難全的遺憾。我感興趣,曹雪芹何以致力於此書。其在《考工志》序言末尾云:「以集前人之成。實欲舉一反三,而啟後學之思。乃詳查起放之理,細究紮糊之法,臚列分類之旨,縷陳彩繪之要。彙集成篇,以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謀其有以自養之道也。」說得透徹,教的是製風箏之法,目的是對弱者的給養。由是觀,這首先這是一本「入世」之書。由紮、糊、繪、放「四藝」而起,縱橫金石、編織、印染、烹調、園林等數項技能。其身體力行,每卷各釋一種謀生之藝,並附有詳細圖解及深入淺出、便於記誦的歌訣。其二,這亦是「濟世」之書,《蔽芾館鑒金石印章集》一章,「蔽芾」諧為弼廢。此書創作之初,有一段佳話,緣由於景廉戎馬致殘而潦倒,求助其友曹霑,曹氏並未直接接濟,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故作此書,教殘疾者「自養」之道,寓藝於義。
由此,寫了《北鳶》中的龍師傅,便是紮風箏的匠人。失意之時,盧家睦給他「四聲坊」一方天地,他便還了他一生承諾。「這風箏一歲一只,話都在裡頭了。」其三世薪傳,將這承諾也傳遞了下去。
「匠」字的根本,多半關乎傳承、抑或持守。「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韓愈在〈師說〉中批評所謂「君子」輕薄相師之道,猶不及「百工」。匠人「師承」之責,普遍看來,無非生計使然。但就其底裡,卻是民間的真精神。當下,這堅守或出於無意識,幾近本能。時代日新月異,他們的手藝及傳統,看似走向式微。曹氏以「廢藝」論之,幾近成讖。淡出了我們的生活,若不溯源,甚至不為人所知。教學相長的脈絡,自不可浩浩蕩蕩,但仍有一脈涓流,源源而不絕。
寫〈書匠〉篇,是因為先祖父遺作《據几曾看》手稿的救護,得以了解「古籍修復師」這一行業。「整舊如舊」是他們工作的原則。這是一群活在舊時光裡的人,也便讓他們經手的書作,回到該去的斷代中去。書的「尊嚴」,亦是他們的尊嚴。所寫的兩個修復師,有不同的學養、承傳與淵源,代表著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脈絡,而殊途同歸。「不遇良工,寧存故物」,是藏書者與修書人之間最大的默契。一切的留存與等待,都是歲月中幾經輪迴的刻痕。連同他們生命裡的那一點倔強,亦休戚相關。
〈飛髮〉與〈瓦貓〉,發生於嶺南和西南的背景。因為在地,則多了與空間長久的休戚與共。這其中有器物的參與,是人存在過的憑證。或者說,經歷了磨礪與淘洗,更見匠與時代之間膠著的堅固。他們的命運,交織與成全於歷史,也受制於那一點盼望與落寞。他們是這時代的理想主義者,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走訪匠人,於不同的行業,去了解他們手藝和背後的故事。他們多半樸訥,不善言辭。或許也便是這一點「拙」,建造了和塵世喧囂間的一線壁壘。只有談及自己的手藝,他們會煥發光彩,因來自熱愛。他們亦不甚關心,如何被這世界看待。時代淘洗後,他們感懷仍有一方天地得以留存。自己經手而成的物件,是曾過往於這世界最好的宣示。事關薩米文化的人類學著作《知識與手工藝品:人與物》,作者史文森(Tom G. Svensson)有云:「傳承譜系中,對於『敘述』意義的彰顯,將使『物』成為整個文化傳統的代言者。」換言之,「故物」與「良工」,作為相互成全的一體兩面,因經年的講述終抵達彼此。辛波斯卡的詩歌中,是物對時間的戰勝;而匠人所以造物,則是對時間的信任。如今屋脊上踞守的瓦貓,經歷了火煉、風化,是以靜制動的根本。時移勢易後,蒼青覆苔的顏色之下,尚餘當年來自手的溫度。因其內裡魂魄,屬上古神獸,便又有了庇佑的意義。匠人們眼中,其如界碑,看得見莽莽過去,亦連結著無盡未來。這一點信念,為強大之根本,便甘心晨鐘暮鼓,兀兀窮年。
庚子年於蘇舍
自序:物是
打算寫關於手藝人的小說,是久前的事了。
與這個人群相關的,民間常說,藝不壓身。學會了,便是長在了身上,是後天附著,卻也就此與生命一體渾然。
談及手藝,最初印象,大約是外公家裡一只錫製的茶葉盒,上面雕刻遊龍戲鳳,久了,泛了暗沉的顏色。外公說是以前經商時,一個南洋商人的贈與。我記事還在用,春天擱進去明前的龍井茶,到中秋泡出來還是一杯新綠。少年時,大約不會關注其中技術的意義,但仍記得那鐫刻的細緻。龍鬚躍然,鳳尾亦搖曳如生。後來,這只茶葉盒不知去向。外公每每喝茶,會嘆息,說時下...
目錄
自 序:物是
江南篇:書匠
嶺南篇:飛發
西南篇:瓦猫
附 錄:一封信
後 記:藏品
自 序:物是
江南篇:書匠
嶺南篇:飛發
西南篇:瓦猫
附 錄:一封信
後 記: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