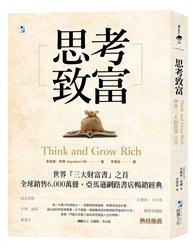自序
人活著不是為了拖動鎖鏈,而是為了張開雙翼
在我動身的時光,祝我一路福星罷,我的朋友!天空裡晨光輝煌,我的前途是美麗的……雖然間關險阻,我心裡也沒有懼怕。旅途盡頭,星辰降至。──泰戈爾
我將美國視為彼岸,抵達美國十年之後,寫了《此心安處:美國十年》一書,記述了在美國開啟人生下半場、重新確認身分和願景的過程。
與此同時,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敘利亞內戰和烏克蘭戰爭引發數百萬難民在國境內和國境外逃亡。中國人的逃亡,則迅速演變完成「偷渡」、「潤學」(「跑」的英文RUN,音譯為「潤」,習近平暴政下,關於如何逃出中國的討論被稱為「潤學」,「潤學」是當代中國無與倫比的顯學)和「走線」三部曲。
巴拿馬移民機關統計顯示,二○二三年一月間通過「達連隘口」的中國移民有九百一十三人,到了九月間人數增至兩千五百八十八人,從一月至九月的累計人數則有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七人。 相較之下,二○二二年全年只有兩千零五名中國移民通過「達連隘口」,從二○一○年到二○二一年之間累計則只有三百七十六人。這一增長速度極為驚人。過去,「偷渡」是祕而不宣的;如今,「潤學」和「走線」在社群媒體上堂而皇之地討論,網上很容易找到事無巨細的「攻略」和「寶典」,參與者公開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訪問。《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這一現象與習近平的統治有關係,該報基於對十幾位正在「長途跋涉之中」或「近期剛剛抵達美國」的中國人的採訪分析說:「在中國各個收入階層,都有大量的人在外流,這些不顧危險經由拉丁美洲進入美國的中國移民是其中一部分。習近平上臺後,民營部門受到擠壓,被迫裁員,這促使企業家外逃。還有人擔心,隨着習近平開始第三個執政任期,政治高壓只會變得更讓人窒息。」其中,最普及的一條「走線」線路是:第一站到土耳其,再飛厄瓜多,經祕魯,沿着南美洲海岸線向北走,抵達委內瑞拉。接下來,穿越安地斯山脈,前往加勒比海,坐船或坐飛機前往巴拿馬、尼加拉瓜等。在中美洲地區繼續向北走,穿過瓜地馬拉、貝里斯等國家,最終抵達墨西哥與美國的邊界,然後輕而易舉地跨越川普尚未完成的邊境牆,就大功告成了。
我不能認同非法越境行為,但我對這些放棄安土重遷的文化傳統、孤注一擲挺進異國他鄉的中國人又心存憐憫,畢竟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下鐫刻著詩人艾瑪.拉撒路的詩句:「那些窮苦的人,那些疲憊的人,那些蜷縮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那些被你們富饒的彼岸拋棄的,無家可歸、顛簸流離的人,把他們交給我,我在這金門之側,舉燈相迎。」當年,一位來自希臘的移民回憶道:「我看到了自由女神像。我對自己說:『女士,你可真美!你張開雙臂,讓所有的外國人都來到這裡。給予我機會在美國證明自己的價值,成就事業、成就自我。』那座塑像將永遠留在我心裡。」
我就想,僅僅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多逃離故土、追求民主、自由和安全的流亡者的故事需要被講述。於是,有了這本《活著就要RUN :流亡者讚歌》。這本書描述了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流亡。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寫過一篇名為《多彩的流放》的小說,寫二戰期間逃亡到加拿大蒙特婁的難民的故事,「這是個無邊的奇蹟,我簡直看不夠他們,他們自己從我閱讀和嚮往的文學園地的曙光裡走出來。我把他們視為是值得期待的社會秩序的先知,這個秩序由公正、平等、藝術、人際關係、勇氣和慷慨組成。他們中的每個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德國天主教徒、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猶太人、捷克人──都是一本我想從頭讀到尾的書。」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指出,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深刻不安的文學。流亡者也是一群深刻不安的群體,他們將黑暗拋到身後,但前方能否找到光明,他們並不確認。他們能將深刻的不安轉化成源源不斷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讓自己的生命在由陌生而熟悉的土地上如深夜的星辰般閃耀嗎?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此心安處是吾鄉」,克服鄉愁,戰勝悲苦,免於恐懼,獲得心靈的充盈、安寧、快樂與幸福?
上部「中土乃惡土」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
以時間而論,當代史上大規模的流亡潮有四個時間節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席捲中國,「不從中共者」逃往香港、臺灣以及更遠的地方;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文革暫告結束,中國緩緩打開國門,被關在鐵幕後將近三十年的人們,終於有了飛越瘋人院、走向自由世界的希望;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逃離中國,已在美國和歐洲的數十萬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因禍得福獲得「六四綠卡」;二○一二年,習近平上臺後中國走向全面法西斯化,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封控防疫讓人窒息(時間節點更早可追溯到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大國崛起」元年),不願做「韭菜」和「人礦」的中國各階層人士,紛紛用不同方式離開愈來愈像地獄的祖國。在這些時間節點上,更有藏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等諸多受到中國殖民暴政壓迫的少數族裔走上流亡路。
以地點而論,作為流亡之島的臺灣和作為流亡之城的香港,以及兩地「風水輪流轉」的「雙城記」,尤其值得關注。李登輝執政後,發動寧靜革命,臺灣告別白色恐怖、走向民主化,由流亡者的中轉站和淒風苦雨中的「亞細亞的孤兒」,鳳凰涅槃般成為美麗島福爾摩沙,成為亞洲乃至全球民主自由燈塔及良善力量,大部分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實現「在地化」,成為認同臺灣的臺灣人,願意「同島一命」,用生命捍衛土地和自由。反之,一九九七年,中共接管香港後,二十多年時間,香港一步步淪為一座被惡魔攻破的「逃城」。香港再也無法接納和庇護流亡者(如一九八九年「黃雀行動」拯救被通緝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香港已然自身難保:香港的監獄中塞滿數以萬計抗爭者,更多抗爭者被迫踏上漫漫流亡路。
更有數萬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建起一座新的聖城──達蘭薩拉。這座小城的居民全都是流亡者,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本人也是流亡者,小城雖小,卻成為圖博民族保存其文化、宗教和民族精神的樞紐。
流亡者逃離的路線錯綜複雜,逃離的方式驚心動魄。他們看似被故國和故人唾棄,卻昂首挺胸、在風雨中擁抱自由。流亡者的是非成敗,不會轉頭即空。流亡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在流亡路上,他們看過更圓的月亮和更壯闊的風景,遇到過更貼心的同伴和更美妙的故事。高行健說:「這是一段流浪,一種自我解脫。最好獲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條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為我的創作尋找新的主題。」哈金說:「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性,正是這個邊緣性使流亡作家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獨特的抱負。」
下部「世界是我家」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
以時間而論,從古希臘到古猶太,放逐與自我放逐一直是英雄和先知的宿命,以及某些民族的宿命(猶太人)。近代,大航海和全球化時代來臨,陸上和海上交通更容易,但民族國家成形,國境上建起圍牆和鐵絲網,政府變成權力無邊的利維坦,公民出國和進入別國需要護照等旅行證件,流亡反倒變得更不易。一戰、二戰及冷戰三個重要時間節點,帶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有時是整個種族和整個階層被連根拔起,拜「現代性」所賜,「大屠殺」和「集中營」成為籠罩在移民(難民)頭上的烏雲與雷電。
以地點而論,我特別選擇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南美等極權肆虐、流亡者前仆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暴政肆虐的國家必然盛產流亡者。有些不幸的流亡者,經歷過多重流亡生涯:先逃離蘇俄的暴政,然後還要逃離納粹的暴政。流亡者的多產之地還有拉美、亞洲及非洲的獨裁諸國。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勒寫道:「這裡不是我的家/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在獨裁國家,唯有獨裁者一個人活得滋潤快樂,其他人(包括其身邊的打手)都是卑賤的奴才,「如果一位獨裁者在頭腦中需要一個家鄉的話,那麼它只能是:蔑視人……為了他自己作為統治者能夠病態地自尊,獨裁者狂熱而不顧一切地蹂躪著國家和人們」。毫無疑問,對自由人而言,「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亦可置換為「哪裡有暴政,哪裡就是異鄉」、「哪裡有暴君,哪裡就是異鄉」。暴政和暴君張牙舞爪的地方,就是必須逃離的「垃圾場」。
很多流亡者在移居地取得了在出生地無法想像的成功。他們不再是千夫所指的「寄生蟲」、「流氓」、「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的走狗」,而是萬眾矚目的諾貝爾獎得主、藝術大師、學術巨匠。流亡者在更加廣袤的天地中漂泊或定居,穿梭於多種迥異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之間,用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經歷無法避免的流亡生涯,巴拉圭流亡作家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說:「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帶給我的除了對暴力和人類價值失落的憎惡,還有對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給予我一種視角,以這種視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觀點來看待我的國家,並因為那裡發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或許,唯有身在別處,才能對原來隸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作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對於我熱愛的別爾嘉耶夫、艾茵.蘭德、納博科夫、布羅茨基、米沃什、馬尼亞,我用最大的篇幅向他們致敬。納博科夫說:「在美國,我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感到快樂。正是在美國,我擁有最好的讀者,他們的心靈與我相遇。在美國,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覺,美國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布羅茨基說,「我在冰山之上眺望過大半個世界,測量地球的寬度」,而「流亡是詩人終其一生的命運」。米沃什說:「在困境中,一個作家的質量便取決於他騰空跳躍的能力,取決於跳板給他的反彈力量。」他將自己視為一個在「荒原」上尋找出口的人,即便其努力失敗、被人視為「怪胎」,此種努力「不僅是最為理所當然的,還是可敬的」。同樣也是流亡者的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安慰、鼓勵和愛。
很多人被厄運套牢,未能「潤」出牢籠。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班雅明因為西班牙拒絕他入境,在法國邊境那一側的一個小旅館房間裡吞下大量嗎啡,並於次日上午去世。
年輕的歷史學者沈元是天縱奇才,在現實生活層面卻是不諳世事的書呆子,裝扮成黑人闖入非洲某國駐北京使館,導致他被捕並被槍殺。
殷海光從中共得勢的中國逃亡到臺灣,但臺灣不是「自由中國」,他的特務環伺的家是「孤島中的孤島」,他憂憤成疾,英年早逝。
此前多次放棄流亡機會的劉曉波,在癌症的最後時刻,期望攜帶妻子出國治療,卻在全世界媒體的關注下,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地死去。
他們未能逃出生天,不是他們不夠努力,而是現實太殘酷。
我質疑和批判的對象,是另一種意義上「失敗的流亡者」──他們的肉體已「潤」出中國,精神卻從未離開,就如同哈金的比喻:就像天上的風箏,看上去飛得很高很高,線卻仍掌控在放風箏的人(共產黨)手中。他們沒有張開雙翼,身後依舊拖著沉重的鎖鏈。
一九八○年代在中國洛陽紙貴的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的創作和思想,自流亡之後就停止了。他被「中國的良心」這個宏大敘事壓垮──他以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之後兩三年就會垮臺,他能載譽歸來,但中共迅速站穩腳跟並讓經濟高速發展,此一事實給他沉重打擊。實際上,沒有人能充當「中國的良心」,每個人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劉賓雁與被譽為「俄國的良心」的索忍尼辛一樣,終身都在此一「神光圈」中打轉,未能善用流亡的命運開創一段嶄新人生。同為流亡作家的蘇曉康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指出:「對賓雁,無論歐陸古典、英美氣象,仍不過是西洋鏡,他卻只惦念江東父老。與其說中國的百姓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更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裡摘除出來。」
詩人顧城「潤」到紐西蘭激流島,他在島上幹了很多事情──從原始的採摘,採野菜、海菜吃,到種菜、養雞,算「農業」;還養過羊、兔子,賣雞蛋、賣雞肉春捲,進入「畜牧業」、「商業」;再回到藝術創作,進入本行「文藝事業」,寫作,給人畫像。他似乎可自食其力。他卻因為「女兒國」烏托邦破滅,悍然殺死妻子,再殺死自己,留下孩子孤苦伶仃在人間。在人心深處,有不忍和殘忍,也有悲哀和狂喜。如傅雷給傅聰的家書中所說,先做一個人,再做一個音樂家;詩人也當如此──先是人,再是詩人。可惜,顧城將此一秩序顛倒過來,以為詩人就有殺人的特權。哈金在詩歌〈流亡的選擇〉中寫道,即便在一座安靜美麗得快讓人窒息的島上,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他最終選擇自殺/甚至對妻子也下了毒手/因為他覺得實在無路可走/完全被瘋狂和恐懼壓垮」。哈金提出的正確出路是,「一開始他就應該明白/選擇了流亡/就不會再有自己的土地/──他心裡將湧起/不斷出發的欲望/他的家園只能在路上」。
鄉愁是很多流亡者不能順利開始一段新人生的關鍵障礙,歌德認為鄉愁是病態,毫無用處。哈金指出:「漢文化中流亡的概念與西方不同,中國古代的流亡者無論飄落到多遠,也走不出漢文化圈。最多是蘇武牧羊北海,但那裡仍是漢文化的邊緣,是匈奴等部落繁衍的地方。如今流亡意味著去國離鄉,不得不在異國生活──學習外語,學會謀生,接受人類共有的價值,甚至生根。在中國人的基因裡,這種異化的生存狀態很難承受,所以許多海外流亡人士常談起將來能『回家吃餃子』,好像餃子只有故鄉的香。」是的,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刮骨去毒、跟出生地「斷奶」,空間上的流亡仍然無法帶來精神上的自由。
詩人宋琳說過,真正的流亡,一個人就是一個種族。以此與所有勇敢的流亡者共勉,讓我們都用生命來寫流亡的故事,這個主題無窮無盡。
二○二三年一月初稿
二○二三年十月二稿
二○二四年一月定稿
美國維吉尼亞州費郡綠園群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