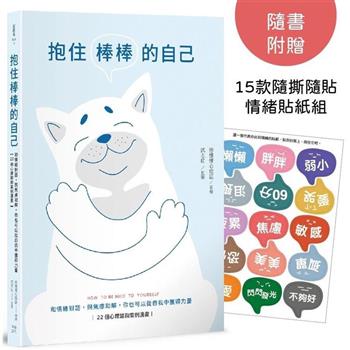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第五章_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
〈從漢人到雲南人──十三世紀之前漢人的本土化〉
普遍來說,元代以前所有移民到雲南的中國人,全都被吸納入土著社會之中。莊蹻採納土著習俗來進行統治,他的士兵們生活在當地社會中,應當是和土著女性結合,他們後裔擁有的楚人認同因此日益衰微。漢代時期出現西南地區的第一波中國移民潮,幾乎所有移民都淹沒於廣大的土著人口之中。漢代日益頻繁的軍事、政治、經濟接觸與互動,造就出許多地方酋長與氏族,也就是所謂的「夷帥」與「大姓」。夷帥是透過與中國政權接觸而增加權力的土酋,大姓為力量最強大的移民及其後裔,他們利用漢朝政府來增進自身在當地事務中的影響力。大姓多是漢代官員或菁英的後裔,不過他們已適應地方社會。大姓的例子揭櫫土著文化所具有的力量,驅使中國移民們採納土著習俗以求生存並累積勢力。考慮到那時土著人口占絕大多數,難怪本土化的過程全面碾壓華化的過程。
南詔時期,主流趨勢持續為本土化。據《通典》記載,有些鄰近大理地區的人們宣稱自己是漢人後代,雖然他們的漢人特質已經因為本土化而消磨殆盡了。《蠻書》也有類似的論述,說有些當地人本是漢人。此外,有些漢人開始服務於西南土著社會或君主,這是政治認同的轉變趨勢。政治認同的轉變恰恰呼應了中國帝國統治者的擔憂,也就是擔憂在邊疆的臣民可能喪失自己的文化和身分意識,改變自己的政治效忠而服務於「蠻夷」君主。
總結而言,西漢以降,中國人便持續向西南移民,但移民的數量無法與土著人口相比。此種人口比例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會被整體同化入當地社會。雖然到了明、清時期有百萬漢人遷徙入雲南,根本上改變了人口組成,進而導致華化的成為主流;但是,在塑造後征服時代(post-conquest)的雲南社會,本土化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所以絕不能低估本土化的重要性。
氣候、地形、礦產以及土著的經濟慣習,全都在驅使中國移民採納特定時刻雲南本地的也就是土著的經濟結構與模式。元、明、清政府引入並移植中國式農業生產體制時,卻受到雲南當地氣候與地形的挑戰。「男耕女織」這一理想式的中國方式,在雲南很多地方難以實施。一位明代學者指出,滇民「知農而不知桑」。即便是在那些氣候適合養蠶的區域,地方官們呼籲人民養蠶常常難以奏效。舉例而言,即便到十九世紀末期,鶴慶府地區的女性並不紡織,這項地方傳統因此被視為嚴重的經濟與文化缺點。
由於礦產資源豐富,許多漢人移民在雲南從事礦業與貿易。儘管雲南農民的人數確實遠高過礦工,但礦工在當地所占的人口比例絕對高於中國本部許多。雲南是中華帝國晚期的主要礦產區;採礦業的蓬勃事實上促成了雲南的城鎮化。而這樣的城鎮化模式鮮少發生在中國本部。
雲南原有的地方貨幣制度也形塑了中華帝國的貨幣體系。在元代,紙鈔被指定為全中國的官方通用貨幣,這是元朝的重大經濟措施之一,也是首次由帝國政府所支持的紙幣體制。然而,該制度最後以失敗告終。紙幣在雲南的流通情況也許是全國最糟的,因為雲南使用海貝作為貨幣已經有好幾百年的光景。因此,國家所推行的紙幣並不被土著社會所接受,顯然阻礙了元代行政體系之運作。賽典赤.贍思丁注意到此事,允許雲南繼續沿用貝幣。結果,貝幣不只被允許繼續為民間貿易與其他經濟活動所使用,而且還被官方接受,用來繳稅。到了明代,明王朝在雲南繼續沿用貝幣。在整個元、明時期,貝幣,而不是中國的銅錢,是雲南的主要流通貨幣。貝幣這一經濟習俗生動地證明了邊疆社會如何迫使中央征服不得不加以妥協。
地方市場也能證明土著社會的影響。土著居民有定期貿易或趕集的習慣。漢人移民立刻參與了雲南的本地集市,雖然後者在許多方面與中國本部有別。一般而且,定期集市白天聚集,但是在喜洲(大理)地區,集市卻是在夜晚進行。此外,雲南本地也有獨特的節慶日,同時也是各地商人聚集開市的日子。大理在每年三月十五日和二十日之間會有「觀音市」,很多商人會前來買賣,政府也會動用差役與士兵來維持治安,保護商業。
雲南的漢人移民借用了土著生活方式的許多層面。服裝便是其一。大理土著會用一片藍布蓋住頭頂並戴上「氈笠」──一種由本地植物作成凸顯地方風格的帽子──而漢人移民也馬上仿效,以便在強風拂面的大理地區內保護自己。在金齒衛(永昌)地區,漢人女性穿著與僰人相同的服飾。有時候,即使是城裡的漢人,為了適應環境也會改穿土著服裝。「鶴慶之俗,婦帽三尖,以布為之」,鶴慶知府周贊對此風俗感到憤怒,命令「易以髻簪」這樣的中國女性髮飾,當時民間有歌謠曰:「我周公,變夷服,易簪髻,去布幪。」這反而說明了夷服當時之流行。
地方食物當然也影響了漢人移民的飲食習慣。土著們喜歡吃生肉,將豬肉、魚肉、鵝肉、鴨肉切塊,再混上各式各樣的調味品。在雍正年間(公元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五年),有些仕紳與學者們接受了這種吃法,甚至將其變成一種風尚。
很多地方文化活動或受到中央政府的接納,或有漢人也參與其中。佛教是雲南最為盛行的宗教。大理國王們曾經自稱「摩訶羅嵯」(maharajah,梵語意為「偉大統治者」)。當蒙古人到來之際,他們認可並接受此項傳統,將此頭銜授予段氏。當清政府企圖與土著酋長們結盟之時,有時會舉辦佛教式的立誓儀式,以獲得土著的支持。漢人移民們也會參加本地許多佛教節日,有的是中國內地沒有的慶祝活動。雲南全省都盛行的佛教節日包括「浴佛節」(Viskha Puja),以及大理的「觀音市」。漢人移民頁參與了其他族群的節日也,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花市、火把節以及潑水節。
地方薩滿教的存在也表現於諸多日常活動,例如遍布四川、雲南、貴州的「土主」崇拜。「土主」即村社保護神,是古早以前留下來的土著薩滿教遺物,在西南民間有廣泛的信眾和影響力。南詔時期就已經從事土主崇拜儀式,雲南的少數族群與漢人至今依然保持著這項傳統。十七世紀初劉文徵所著之《滇志》記載,全雲南幾乎每一個府都有土主廟宇,有些府甚至有二或三座土主廟。有部地方誌甚至歌頌土主是最為「靈異」的神明,記載稱土主廟中的蜂群驅逐了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一九年)的安南侵略者。
漢人移民到了雲南之後很快接受而且學習當地的語言。「滇」本是土著用詞,大致用來指稱整個雲南,「滇」字成為了官方對於雲南的簡稱而且被沿用至今。「滇人」是一個新的中文詞彙,這個詞出現在明代,指稱「全雲南的人」──包括土著與漢民。其他的土著詞彙例如「海」(「海」的意思是湖泊)、「賧」(河、湖),至今依然廣為使用。此外,眾多當地地名提醒著我們,土著居民的分布異常廣闊。為了便與土著溝通(例如進行貿易),移民(如蒙自縣的漢人自然開始學習土著語言。孤立的漢人社群在經過幾個世代之後,其後裔已經不太會說先人的方言或中文,他們的日常溝通都是用土著語言進行。有些明、清時代的地方誌裡,會有關於土著語言的篇幅(列入「方言」之下)。
雲南當地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頗為普遍,這可能是讓中國移民本土化的最有效方法。有許多漢人士兵娶了土著女人,這是邊疆社會性別比例失衡的結果。「夷娘漢老子」的結合頗為流行,大大促進了漢人移民群的本土化,因為在絕大多情況下兒童是整天跟隨在「蠻夷」母親的身邊。早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許多孤立的明代軍事社群便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明末徐霞客抵達納西人(麼些)居住的麗江地區時,他寫道:「其地土人皆為麼些。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這樣的案例在滇西北部並非特例,事實上,同樣的情形在由土司主宰的滇南更為常見。例如騰越地區的明代士兵與其後裔,根據記載,他們在乾隆年間(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已經變作「蠻夷」了。今日,雲南(貴州也是)有許多群體,他們與周遭族群並無差異,卻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漢族」,理由只是因為他們是明代移民的後裔。
應當指出,性別比例並不是通婚的唯一原因。通婚能夠帶來經濟利益,並且提供了移民在邊疆地區普遍欠缺,但又亟欲獲得的文化與政治紐帶。舉例而言,中國商人往往會娶土著妻子,就像是歐洲商人在東南亞或北美洲的情況一樣。無論哪種案例,土著女性都以擅長貿易與交涉所著稱。許多中國移民透過通婚的方式,開始進入地方政治或菁英圈子(值得注意的是,土著菁英也需要這類漢人移民來增進自身利益,因為這些中國顧問們能夠熟練運用中國知識來幫助土酋與帝國政府交涉)。一代接一代,漢人的後裔在地方社會上的力量變得愈來愈強大,有時甚至成為主宰的勢力。
經濟與文化的互動往往造就雙重的政治與文化認同。紀若誠曾經探討,漢人移民(及其後裔)是如何成為礦業的領導者,然後再變成有時與土司及清廷官員合作的強權人士;有時他們則會發展自治力量,足以威脅清廷利益。這種本土化的例子出現最早在明代,而且不限於礦工社群。如前所述,諸多位於山區軍屯田莊,周遭都是非漢人的環境與「蠻夷」。這些移民們就像是一艘位在洶湧波濤的土著海洋上的小船,逐漸被吸入土著社會之中。他們開始講土著語言,採取土著的生產方式,享用土著飲食。
更重要的是,漢人移民後裔開始了「多重族群」(multiethnically)、「多重文化」(multiculturally)的身分認同。他們既認同自己的漢人祖先,也接受自己的本地身分標籤。在某些案例中,漢人後裔很高興擁有緬甸的名字、頭銜或關係。有時候,他們對自身土著身分高於中國身分的認同。更有甚者,漢人移民會站在土司一方來對抗帝國政府,因為統治該區域且掌握資源者不是別人,乃是地方土司。身在南方邊疆的江西商人之子岳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岳鳳的故事不但呈現了一個漢人移民文化與政治認同的轉換,也告訴我們土著文化如何傳播到了遠方的中華帝國。
岳鳳,史載「江西撫州人,黠而多智,商於隴川」,因此,隴川宣撫使多士寧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岳鳳,對他深加信任。但是岳鳳野心勃勃,陰謀篡奪取代多士寧。他勾結其他土司,尤其是木邦宣撫使罕拔。兩人一拍即合並歃血為盟。他們引誘多士寧前往擺古去面見莽瑞體(Mangruiti,緬甸國王),對多士寧下毒並殺害他的妻小。接著,岳鳳奪得中國帝國政府授予的隴川金牌印符,將其獻給莽瑞體。此時,莽瑞體正在擴張領土,他很熱切地接納了岳鳳,並授予他多士寧原來的頭銜。
莽應里(Mangyingli)登上緬甸王位之後,岳鳳與其子曩烏伏擊打敗了明朝的軍隊,虜獲多士寧之母與六百多位族人,並將俘虜獻給莽應里。岳鳳於是接管了多士寧的子民。此外,岳鳳還秘密與孟連土司刀落參結盟,然後說服莽應里入侵明代邊界,他們占領並燒毀了順寧府。岳鳳子曩烏領六萬緬甸兵攻打孟連,明王朝的雲南指揮使吳繼勳在該役中身亡。鄧川土知州何鈺是岳鳳朋友的女婿,何鈺派遣使者至岳鳳處,岳鳳卻將使者逮捕後交給莽應里。
當時,木邦宣慰使司土舍罕拔與其子罕效忘投降明政府。莽應里大怒,占領了罕拔的城市。在帝國援軍前來之際,何鈺又派了一次使者招降岳鳳,此時刀落參在戰役中被殺。岳鳳感到憂心,遂派遣姪兒岳亨至永昌納降,明將劉綎接受他們的投降,並保證岳鳳可以倖免於帝國法律。
公元一五八五年正月,岳鳳與其妻子、兒子、兄弟、姪甥、軍隊──包括夷人與漢人──全都投降,「盡獻所受緬書、緬銀及緬賜傘袱、器甲、刀槍。鞍馬、蟒衣並偽給關防一顆,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岳鳳被送往北京獻俘。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最能夠彰顯土著文化對於岳鳳的影響。岳鳳被送往北京處決之時,被發現全身都有刺青(這是典型的土著文化標誌),而且他的「陽道」亦嵌數顆「緬鈴」,令人嘖嘖稱奇。明代學者沈德符慨歎:「鳳本華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為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勛臣家。最上者值至蜀百金。鈴本震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猶搖盪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寧居也?」這段文獻記載讓人好奇的是,朝廷勛臣家購買陽具與「緬鈴」意欲何為?
作於明代中期最有名的中國情色小說《金瓶梅》,或許能對理解明代菁英的色情文化有所幫助。《金瓶梅》主角西門慶是中國北部山東省的一個有錢商人、花花公子、地方菁英。小說當中西門慶便曾經使用緬鈴。當西門慶最喜愛的妻子潘金蓮向他問起緬鈴時,西門慶回答:「喚做勉鈴,南方勉(緬)甸國出產的。」接著兩人便關門歡娛。這就是為什麼勛臣要購買岳鳳緬鈴的原因了。
緬鈴之使用在雲南頗為盛行,正如十七世紀初雲南官員謝肇淛的觀察。謝氏指出,緬甸男子為了性趣會將緬鈴嵌入陽具;他注意到,緬鈴也被賣給中國人。更有趣的是,謝肇淛表示緬鈴有一個中國式名稱,叫作「太極丸」,中國人把它當成禮物送人,官方或私人的書信中都曾經提起它。謝肇淛的紀錄顯示,勳臣購買岳鳳陽具或許真有此事,因為緬鈴的使用情況很廣泛。
性工具之使用──尤其是將這種珠子嵌入陽具──確實是流行的東南亞習俗。東南亞女性在其社會當中享有頗高的地位。所謂緬鈴便是證據,表明當地男人願意接受痛苦的陽具手術,來增加女性的性快感。同時代的中國人及歐洲人都注意到了東南亞的這一習俗。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手術就是嵌入金屬針,附帶各式各樣的輪、刺、釘。一位親眼目睹的歐洲人曾寫道:
男性──無論大小──會用大如鵝羽毛的金栓或錫栓,在自己的陽具近首處,從一端穿到另一端。同一隻栓的兩端,有些看起來像是馬刺,頂端有凸點;有些看起來則像是貓爪的尖端。我常常請他們──無論老少──給我看他們的陽具,因為我對此不敢相信。在那隻栓的中間有一個洞,他們才能夠排尿。…他們說,是他們的女人希望如此;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他們的女人就不願意跟他們性交了。
另外有一種比較不痛的手術,是十五世紀的中國人馬歡在暹羅所觀察到的:「凡男子年二十餘歲,則將陽物周圍之皮,用如韭菜葉樣細刀挑開,嵌入錫珠十數顆,皮肉用藥封護,待瘡口好時才出行走,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開鋪,專與人嵌妝以為藝業。如國王或大頭目或富人,則以金為空珠,內安砂子一粒嵌之,行動扱扱有聲為美。不嵌珠之男子,則為下等人也,最為可笑也。」
中文的「鈴」,可以指會發出聲響的珠、輪、刺、針。岳鳳是真的接受過那類手術,西門慶則是使用自緬甸引入的類似工具,來讓自己的女人增加性快感。岳鳳和西門慶的故事,顯示東南亞的性習俗被中國菁英文化所引入、仿效(此為一種東南亞化的過程),而這些性習俗最初可能是經由雲南所傳播,這更進一步象徵著雲南在「中國─東南亞」交流互動中的角色。
(摘自:《流動的疆域》,〈第五章_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製造「雲南」就是創造「中國」!
從古滇國、南詔國、大理國,再到雲南省,
「雲南」曾經主導東南亞的全球貿易中心,
為何最終被中華帝國統合,而淪為邊疆省分?
中國歷史特殊論?且看本書如何挑戰葛兆光《宅茲中國》論述!
*****
■「雲南人」的地方認同,是大一統帝國的發明
中國大多數含有「東西南北」等方位名詞的省分名稱一般都與河流或山脈有關,如兩河、兩湖、山東、山西等等,但「雲南」卻是例外——作為地名的「雲南」,既與河流、山脈無關,也不是當地族群自發形成的政治地理名稱。
既然「雲南」原本不存在,自然也就沒有「雲南人」。事實上,「雲南」源自於一種來自遙遠北方的距離感與陌生感——它是中國歷代王朝製造出來,強加給帝國西南邊陲地區的一種「想像」。本書便是以「中國的東方主義」及「中國中心論」來形容這種隱藏於漢字觀點下的偏見。
雲南自古以來就是部落林立、政權更迭的獨立區域,一直要到十四世紀才正式被蒙古帝國征服,此後歷經明清兩代,成為「中華帝國」的邊疆省分直到今日。雲南這一省級行政區是元帝國的發明,在此政治空間之下,本地原住民與漢人移民逐漸融合,服膺於帝國秩序,並透過科舉制度與儒家文化,逐漸催生了「雲南人」這個「大一統王朝臣民」的身分認同。
因此,「雲南人」不是「獨立」的想像,而是「臣民」的想像。從明代開始,「雲南」在政治和文化上成為中華王朝的重要部分。所謂的「雲南人」,同時也成為「中國人」的具體表述。
■從雲南的形成,思考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本質
今天的雲南地區,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前就獨立形成了發達的青銅器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那裡生活著不同的部落、部落聯盟和王國,使用具有異國風味的名稱(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勞浸、靡莫、邛都等)。「雲南」這兩個漢字首次出現於西漢時期,屬於漢王朝在西南邊疆設置的「益州郡」之下。
西漢之後,儘管中原政權聲稱其擁有對雲南地區的統治權,但從未確立過牢固而連續的統治。雲南地區出現的獨立政權,如滇王國、南詔國、大理國,不斷與向南擴張的北方政權發生衝突,同時也透過貿易與移民進行交流。直到清末民初時期,「雲南」才在「軍閥割據」狀態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在一九四九年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征服雲南,並對當地展開了「民族識別」,將官方認可的各種少數民族,歸併至「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裡,以「民族主義」的方式徹底統合了「雲南人」。
當代中國的民族政策,承接了歷史上不同政權的帝國遺產,透過「中華民族」的概念維護著古代的「大一統」帝國框架,而雲南就是最鮮明的案例。因此,理解「雲南」形成的歷史,同時也是反思「中國」作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本質。
■歐亞「大分流」時代的來臨,最終將雲南推向了中國!
雖然從中華帝國的視角來看,雲南不過是邊陲;但是,若從全球交流的視野來看,雲南絕不是封閉落後、尚待「開化」的蠻荒之地,而是一個位處西南絲綢之路上,貿易頻繁、文化多元的開放地區。雲南的傳統國際貿易網絡,不但可直接通往東南亞、南亞及印度洋,甚至遠及中亞與非洲。
縱使被蒙古帝國征服後,雲南仍然維持其國際貿易的核心要角長達數百年之久。因此,雲南文化深深受到各種國際因素的影響,帶有鮮明的異國特色。本書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分析雲南如何使用「貝幣」——來自馬爾地夫島出產的海貝、西南絲路與印度洋貿易的主要媒介——從上古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在歐洲勢力進入印度洋後,歐洲通貨逐漸取代了貝幣的使用,最終造成雲南經濟的崩潰,並轉向以中國主導的大陸貿易體系。
因此,雲南最終被併入中國,不能單獨從中國史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進一步思考世界史的關鍵影響,才能理解其中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中國」從傳統的帝國逐漸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也不只是王朝更迭的內部變化,更受到世界格局變化的外部影響。
本書特色
★獨家收錄作者新寫:臺灣版序、跋。
★臺灣第一本透過世界史觀點,論述雲南二千年歷史發展的學術巨作!
★榮獲2004年美國歷史學會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
★《中國季刊》、《東南亞研究期刊》、《中國研究書評》等學術期刊一致好評!
作者簡介:
楊斌(Yang Bin)
中國出生,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西泠印社社員,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現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論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於2004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主辦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並於2008年出版,2021年則以《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之名出版中文版;另著有《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及多篇學術論文,對中國史、全球史、科技醫療史及海洋史頗有興趣。
譯者簡介:
韓翔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譯有《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
章節試閱
【第五章_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
〈從漢人到雲南人──十三世紀之前漢人的本土化〉
普遍來說,元代以前所有移民到雲南的中國人,全都被吸納入土著社會之中。莊蹻採納土著習俗來進行統治,他的士兵們生活在當地社會中,應當是和土著女性結合,他們後裔擁有的楚人認同因此日益衰微。漢代時期出現西南地區的第一波中國移民潮,幾乎所有移民都淹沒於廣大的土著人口之中。漢代日益頻繁的軍事、政治、經濟接觸與互動,造就出許多地方酋長與氏族,也就是所謂的「夷帥」與「大姓」。夷帥是透過與中國政權接觸而增加權力的土酋,大姓為力...
〈從漢人到雲南人──十三世紀之前漢人的本土化〉
普遍來說,元代以前所有移民到雲南的中國人,全都被吸納入土著社會之中。莊蹻採納土著習俗來進行統治,他的士兵們生活在當地社會中,應當是和土著女性結合,他們後裔擁有的楚人認同因此日益衰微。漢代時期出現西南地區的第一波中國移民潮,幾乎所有移民都淹沒於廣大的土著人口之中。漢代日益頻繁的軍事、政治、經濟接觸與互動,造就出許多地方酋長與氏族,也就是所謂的「夷帥」與「大姓」。夷帥是透過與中國政權接觸而增加權力的土酋,大姓為力...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導論】
〈雲南:中國式的發明〉
在字面意義上,雲南的意思是「彩雲之南」,這原本是個中國語彙。事實上,「南」字就像是「北」、「東」、「西」一樣時常出現在地名當中,例如「河南」(黃河之南)、「湖南」(洞庭湖之南)、「海南」(海之南)、「河北」(黃河之北)、「山東」(太行山之東),以及「山西」(太行山之西)。以上這些名稱,都可以給我們基本的地理位置概念;可是雲南在哪裡呢?彩雲南端之地是哪?彩雲在哪兒?
「雲南」一詞是漢人的發明,用來稱呼當地的人民與土地。這個稱呼並不被當地原住民採納,直到中華帝國的...
〈雲南:中國式的發明〉
在字面意義上,雲南的意思是「彩雲之南」,這原本是個中國語彙。事實上,「南」字就像是「北」、「東」、「西」一樣時常出現在地名當中,例如「河南」(黃河之南)、「湖南」(洞庭湖之南)、「海南」(海之南)、「河北」(黃河之北)、「山東」(太行山之東),以及「山西」(太行山之西)。以上這些名稱,都可以給我們基本的地理位置概念;可是雲南在哪裡呢?彩雲南端之地是哪?彩雲在哪兒?
「雲南」一詞是漢人的發明,用來稱呼當地的人民與土地。這個稱呼並不被當地原住民採納,直到中華帝國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臺灣版序∣何以雲南?何以中國?
第一章∣導論
・「雲南」與「西南」的演進與使用
・邊疆的視野:雲南的融合
・文獻資料與全書架構
第二章∣西南絲綢之路:全球脈絡中的雲南
・導論
・歷史上的雲南:中國、東南亞、南亞與西藏的交叉路口
・西南絲路概述
・滇─緬甸─印度貿易通道的產生
・滇越通道
・滇藏通道
・元、明、清三代及此後的西南絲路
・西南絲路的案例研究──市馬
・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三條絲路的重要性
・結論
第三章∣征服雲南:一個跨區域的分析
・導論
・雲南與秦帝國的形成
・西漢對雲南的「再發現」
・諸葛...
第一章∣導論
・「雲南」與「西南」的演進與使用
・邊疆的視野:雲南的融合
・文獻資料與全書架構
第二章∣西南絲綢之路:全球脈絡中的雲南
・導論
・歷史上的雲南:中國、東南亞、南亞與西藏的交叉路口
・西南絲路概述
・滇─緬甸─印度貿易通道的產生
・滇越通道
・滇藏通道
・元、明、清三代及此後的西南絲路
・西南絲路的案例研究──市馬
・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三條絲路的重要性
・結論
第三章∣征服雲南:一個跨區域的分析
・導論
・雲南與秦帝國的形成
・西漢對雲南的「再發現」
・諸葛...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