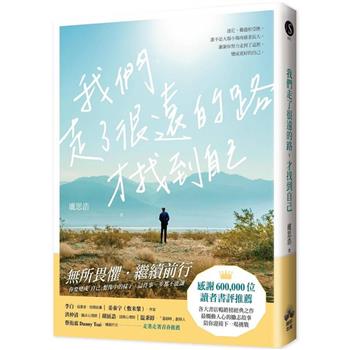本集主要講述了知青到農村農場後所感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惡劣困境,以及文化生活貧乏、農業生產勞累,尤其是人格地位遭受的管制和壓抑,思想上所產生的迷茫。巨大的心理落差,使知青產生了大量的「扒車回家」、「沒病找病」的奇聞趣事,派生了盛行一時的「傳抄傳唱」地下知青文化,其中《第二次握手》和《南京知青之歌》作者險遭死刑的冤案更是扣人心弦。此外,還介紹了轟動全國的李慶霖「告禦狀」和張鐵生、鐘志民「反潮流」事件的經過,並通過內蒙知青王亞卓的勸告信風波,反映了知青在「913事件」的震憾下,從困惑中走向覺醒……
本書特色
文中引用大量珍貴史料,以及近百名親歷這一過程的知青講述的切身經歷。一套五冊,有關知青曾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事例,全景式的揭示從一九五五年至今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上山下鄉運動對兩千多萬知青的學業、青春、愛情及回城後的就業、婚姻、養老等身心的傷害或摧殘。從而讓人們看到這一空前絕後的人類大遷徙運動,對國家、民族及經濟發展的重大損失和影響。以冀望後人能牢記這一近乎野蠻行徑對人類文明踐踏的教訓。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二):青春困惑的迷茫的圖書 |
 |
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二):青春困惑的迷茫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5-09-0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6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2 |
科學科普 |
$ 457 |
中文書 |
$ 458 |
中國歷史 |
$ 468 |
中國歷史 |
$ 468 |
社會人文 |
$ 468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二):青春困惑的迷茫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自由兄弟編纂
名羅玉良。中國鐵路作家協會和廣西作家協會會員。1954年生人。1969年不足16歲下鄉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 1974年返城後,自學獲得大學本科文憑。後在鐵路系統宣傳部門工作多年,所寫的報告文學和文學作品等,曾先後獲得中國鐵路和自治區二三等獎。
自由兄弟編纂
名羅玉良。中國鐵路作家協會和廣西作家協會會員。1954年生人。1969年不足16歲下鄉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 1974年返城後,自學獲得大學本科文憑。後在鐵路系統宣傳部門工作多年,所寫的報告文學和文學作品等,曾先後獲得中國鐵路和自治區二三等獎。
目錄
第一章 初臨農場農村的困窘與畏懼
第一節 驚愕難忘的農村農場失落心緒
第二節 驚恐難眠的農村農場簡陋住房
第三節 羞愧難言的粗劣飲食與如廁窘態
第四節 偏僻難行的農村農場交通閉塞
第五節 心境難忍的極度貧乏文化生活
第二章 知青相互生活的摩擦與歧途
第一節 集體戶知青做飯的難題與趣聞
第二節 惡劣大自然對集體生活的考驗
第三節 逢年過節孤苦可憐的生活情景
第四節 難耐飢餓困頓四處尋吃的狼狽
第五節 無可奈何走上偷雞摸狗的歧途
第三章 意想不到的勞動艱辛與缺失
第一節 下鄉初期農耕手作的茫然
第二節 缺乏安全保護的農業生產
第三節 缺乏安全常識的盲幹行為
第四節 缺乏自然常識付出的代價
第五節 面對各種疾病困擾的惶惑
第四章 知青對再教育地位的心理失落
第一節 與農民農工心理素質的巨大落差
第二節 對農村農場陳舊風俗習慣的迷茫
第三節 對農村農場領導粗暴方式不適應
第四節 對自身處於教育地位的心理失落
第五節 對極左路線粗暴言行的困惑反感
第五章 林彪外逃事件對知青狂熱的喚醒
第一節 林彪事件後對自身前途的迷茫
第二節 想念親人與探親假的故意刁難
第三節 擅自爬車回城探家的瘋狂舉動
第四節 同情關愛知青探親的好心人們
第五節 勞累疲憊下沒病找病的知青們
第六章 思想迷茫引發的精神錯亂和自殺
第一節 對改造農村農場自然條件的失望
第二節 階級鬥爭之弦對知青心靈的恐嚇
第三節 限制男女戀愛引發的性壓抑心理
第四節 因思想迷茫引發精神錯亂的事例
第五節 借酒澆愁而命喪黃泉路上的知青
第七章 派生於苦悶迷茫中的知青文化
第一節 因為偷看封資修文化而被批判
第二節 悄然流行的地下手抄知青文化
第三節 一個手抄本製造的文字獄冤案
第四節 派生於苦悶迷茫中的知青歌曲
第五節 險遭死刑的《南京知青之歌》作者
第八章 知青群體困惑對社會的衝擊
第一節 知青迷茫對父母家長的心理傷害
第二節 兩個請求截然不同的「反潮流」知青
第三節 無法勝任學業的知青工農兵學員
第四節 一封對中學生妹妹勸告信的風波
第五節 知青迷茫心理對其人生的後遺症
第一節 驚愕難忘的農村農場失落心緒
第二節 驚恐難眠的農村農場簡陋住房
第三節 羞愧難言的粗劣飲食與如廁窘態
第四節 偏僻難行的農村農場交通閉塞
第五節 心境難忍的極度貧乏文化生活
第二章 知青相互生活的摩擦與歧途
第一節 集體戶知青做飯的難題與趣聞
第二節 惡劣大自然對集體生活的考驗
第三節 逢年過節孤苦可憐的生活情景
第四節 難耐飢餓困頓四處尋吃的狼狽
第五節 無可奈何走上偷雞摸狗的歧途
第三章 意想不到的勞動艱辛與缺失
第一節 下鄉初期農耕手作的茫然
第二節 缺乏安全保護的農業生產
第三節 缺乏安全常識的盲幹行為
第四節 缺乏自然常識付出的代價
第五節 面對各種疾病困擾的惶惑
第四章 知青對再教育地位的心理失落
第一節 與農民農工心理素質的巨大落差
第二節 對農村農場陳舊風俗習慣的迷茫
第三節 對農村農場領導粗暴方式不適應
第四節 對自身處於教育地位的心理失落
第五節 對極左路線粗暴言行的困惑反感
第五章 林彪外逃事件對知青狂熱的喚醒
第一節 林彪事件後對自身前途的迷茫
第二節 想念親人與探親假的故意刁難
第三節 擅自爬車回城探家的瘋狂舉動
第四節 同情關愛知青探親的好心人們
第五節 勞累疲憊下沒病找病的知青們
第六章 思想迷茫引發的精神錯亂和自殺
第一節 對改造農村農場自然條件的失望
第二節 階級鬥爭之弦對知青心靈的恐嚇
第三節 限制男女戀愛引發的性壓抑心理
第四節 因思想迷茫引發精神錯亂的事例
第五節 借酒澆愁而命喪黃泉路上的知青
第七章 派生於苦悶迷茫中的知青文化
第一節 因為偷看封資修文化而被批判
第二節 悄然流行的地下手抄知青文化
第三節 一個手抄本製造的文字獄冤案
第四節 派生於苦悶迷茫中的知青歌曲
第五節 險遭死刑的《南京知青之歌》作者
第八章 知青群體困惑對社會的衝擊
第一節 知青迷茫對父母家長的心理傷害
第二節 兩個請求截然不同的「反潮流」知青
第三節 無法勝任學業的知青工農兵學員
第四節 一封對中學生妹妹勸告信的風波
第五節 知青迷茫心理對其人生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