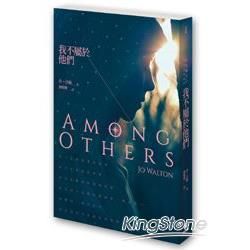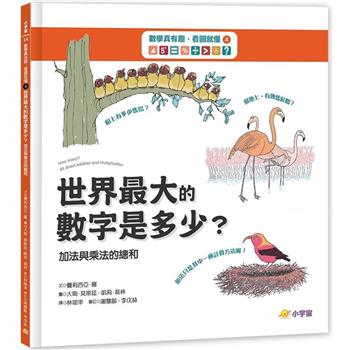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我不屬於他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0 |
二手中文書 |
$ 270 |
小說/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我不屬於他們
這不是個快樂的故事,也不是輕鬆的故事,但它是關於妖精的故事,所以你可以將它想成是一則童話……沒關係,我不在乎,反正你也不會相信我所說的一切。
你是否曾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你拯救了世界,但似乎沒人知道、沒人在乎,只有你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為了抵抗沉迷魔法的母親,莫兒失去了最親近的雙胞胎妹妹,她的腿也重傷致殘,雖然因此逃離母親的掌控,生命中已留下無可彌補的巨大空洞。莫兒被迫離開她深愛的威爾斯,離開妖精出沒的廢墟荒地,到英格蘭投靠她未曾謀面的父親,旋即又被送往寄宿學校。全然孤立的莫兒只能在她最愛的科幻、奇幻小說中尋求慰藉。
莫兒試圖以魔法找尋同類,不料卻因此被她的母親發現了她的魔法痕跡。
這一次,她將再度挺身對抗。
母親想要全世界的人都愛她,而她能對我做出最可怕的事,就是把我變得像她一樣。
「我不想要變得邪惡……真的不想。」
【本書特色】
1.骨子裡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拯救世界之後適應不良的故事。
2.女孩藉由陽性的力量(科幻小說)得到自我認同。
3.不同於一般大和解式的結局,以較寫實的手法呈現親子衝突。
【名家推薦】
◎黃明慧(南科實中圖書館主任)
◎江國樑(宜蘭羅東高中圖書館主任)
◎呂紹敏(高師大附中圖書館主任)
「精彩至極……徹底翻轉神祕的寄宿學校故事。」
──《出版人週刊》重點書評
「一本令人驚艷的美麗傑作。」
──浪漫時代書評
「這個故事很有趣,而且意味深遠、引人入勝。」
──娥蘇拉.勒瑰恩(《地海系列》作者)
我不屬於他們 相關搜尋
奇幻生物孤兒院:榮登亞馬遜網站奇幻小說暢銷榜No. 1!入圍全球最大書評網站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最佳奇幻小說!我不是怪物:英雄真諦
侑美與夢魘繪師(邪惡奇幻天才大神超凡驚豔震撼全球祕密計畫,限量典藏豪華全彩精裝版,隨書附贈燙金藏書票「夢中的你」)
破空.卷二(暢銷華文創作大神級作家,時空跳躍玄幻冒險力作)
創仙誓:玄明聖使傳 第二話 荒城聖域
善惡魔法學院(1):天選之子的詛咒【暢銷新版】
降魔人幽池2:鸞缺篇(♛古典奇幻浪漫小說才女李莎,最新代表作,28萬字的視覺打造,四篇靈與魔交織情仇的故事)
勤儉魔法師的中古英格蘭生存指南(專屬於你的跨次元體驗平裝版,邪惡奇幻天才大神超凡驚豔震撼全球祕密計畫)
地獄反轉(上):亞馬遜當月編輯選書、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NO.1奇幻小說!
地獄反轉(下):亞馬遜當月編輯選書、Goodreads讀者票選年度NO.1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