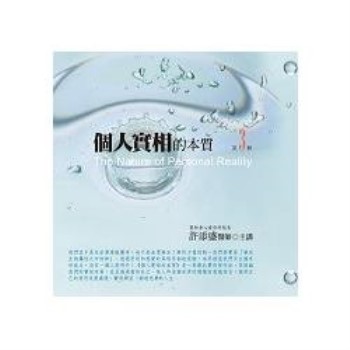無法改變的皮膚,魔力持續發酵……
提普崔獎(Tiptree Award)得主凱瑟琳.M.瓦倫特在《黑眼圈I:荒原之書》與《黑眼圈II:海之書》中帶領讀者進入一魔幻花園,又在《黑眼圈III:風暴之書》施展說故事魔法於「錢幣與香料之城」。如今她編織出更多奇幻、充滿異域情調的聖獸妖靈群魔飛舞於《黑眼圈IV:灼枯之書》,令人彷彿置身另一壯闊瑰麗的遙遠史詩中。
神祕的孤女住在王宮花園裡,眼皮上紋著密密麻麻的黑字,寫的是似乎永無止境的神奇故事。
女孩和伊斯蘭君王的小王儲分享她的故事,令他深深著迷,不斷回來聽象牙籠與鐵籠的祕密,留下來的巨人、貪得無厭的寶石老饕、羽毛斗篷和藍色海蛇,火舞者、火鳥和巨靈的奇談。
但小王子姊姊蒂娜薩的婚禮在即,粗暴的現實開始侵入脫離現實的花園,而這時孤女的故事終於要說盡了……黑眼圈女孩的身世之謎呼之欲出,盤根錯節的大小迷霧終將撥雲見日?
前所未見的不可思議之旅,隨手翻開,就會落入書中的魔咒,因為生生不息的魔法才剛開始。
【本書特色】
給人無窮無盡的驚奇
提普崔獎(Tiptree Award)得主凱瑟琳.M.瓦倫特在《黑眼圈I:荒原之書》與《黑眼圈II:海之書》中帶領讀者進入一魔幻花園,又在《黑眼圈III:風暴之書》施展說故事魔法於「錢幣與香料之城」。如今她編織出更多奇幻、充滿異域情調的聖獸妖靈群魔飛舞於《黑眼圈IV:灼枯之書》,令人彷彿置身另一壯闊瑰麗的遙遠史詩中。
2008年創神文學獎
2007年World Fantasy Award提名
2007年紐約圖書館青少年選書
2006年科克斯書評年度十大奇幻小說
作者簡介:
凱瑟琳.M.瓦倫特
Catherynne M. Valente
1979年生於西雅圖,成長於北加州麥草連綿的天堂。高中畢業後即進入加大聖地牙哥分校以及愛丁堡大學,學的是古希臘語言學,不過後來重返人世,於樟腦味瀰漫的日本荒野久居。
目前和她的兩隻狗住在俄亥俄州。這是她的第五本小說。平時寫詩與小說,後現代筆調融合瑰麗的文字以及超現實元素,後期則投入童話創作,並以《黑眼圈I、II》獲2006年「詹姆斯.提普奇獎」(James Tiptree, Jr. Award),《黑眼圈》系列亦獲得2008年「創神文學獎」(Mythopoeic Award)。
或許因為瓦倫特學的是古希臘語言學、曾於樟腦味瀰漫的日本荒野久居,其筆下的人物或哀傷,或邪惡,或調皮,總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優雅與古典氣息。瓦倫特不諱言因為長期接觸古希臘文學,古典文化中的神話以及原型已經深植於她的靈魂中。再加上從瓦倫特還是小女孩的時候開始,《一千零一夜》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也難怪瓦倫特會以《一千零一夜》的結構為基礎,寫下全新的神話:「我想要創造一個龐大的民間傳說集,同時還要觸及許許多多童話故事的核心:一個簡單的故事,關於一個迷失的小女孩。我們已經太久太久都沒有新的童話故事,而我們的時代就需要童話故事的滋潤。」
作者與本書官方網站:www.orphanstales.com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8年創神文學獎
2007年World Fantasy Award提名
2007年紐約圖書館青少年選書
2006年科克斯書評年度十大奇幻小說
媒體推薦:
「本書是交織美麗的童話。」──《科克斯書評》
「詩情畫意,魅惑人心……尤如女性主義的堅毅混合了仙子塵。」──《娛樂週刊》
「瓦倫特如詩如畫的文字與老練的敘述,栩栩如生地呈現一個奇妙的世界,同時隱固了瓦倫特在奇幻故事最前線的地位,值得任何規模的圖書館收藏。」──《圖書館學刊》
「本書中有完整的一個神話,神話裡,最熟悉的童話場景被拆碎,重組為奇妙完整的新故事……美妙地闡釋了童話應該是什麼樣子。」 ──《書評雜誌》
「瓦倫特的文字複雜而獨具創意,她的想像細膩而引人注目。喜歡精采奇幻作品的人,一定很享受這本書。」 ──《綠人書評》
得獎紀錄:2008年創神文學獎
2007年World Fantasy Award提名
2007年紐約圖書館青少年選書
2006年科克斯書評年度十大奇幻小說媒體推薦:「本書是交織美麗的童話。」──《科克斯書評》
「詩情畫意,魅惑人心……尤如女性主義的堅毅混合了仙子塵。」──《娛樂週刊》
「瓦倫特如詩如畫的文字與老練的敘述,栩栩如生地呈現一個奇妙的世界,同時隱固了瓦倫特在奇幻故事最前線的地位,值得任何規模的圖書館收藏。」──《圖書館學刊》
「本書中有完整的一個神話,神話裡,最熟悉的童話場景被拆碎,重組為奇妙完整的新故事……美妙地闡釋了...
章節試閱
《黑眼圈Ⅳ:灼枯之書》
花園中
花園下起了雪。
這種事並不是史無前例。蘇丹的書裡一定有仕女穿著毛皮衣領在雪中嬉戲的木版畫,她們腳邊還會有繫著鈴鐺的小狗蹦蹦跳跳的。女孩還小時,下過幾場小雪,不過絕不是這樣,這是能讓人陷入及膝冰雪中的暴風雪。檸檬樹的葉子太久沒結霜,因此即使躺在床上巍巍顫顫,年事最高的貴族女性,也只能依稀記起當時她的狗是什麼顏色,狗脖子上叮噹作響的鈴鐺是什麼聲音。湖面凍結成蘆葦包圍的鏡子,松針裹了玻璃,冰冷沉靜地閃爍。孩子嬉戲;狗兒騰躍。新的木版畫趕著印製。
栗樹的樹幹凍住了,婚禮設在一年最長的那一晚,讓人盡情歡宴。遠方的野獸送進宮裡燒烤,男孩嗅著一盤盤犀牛、鱷魚、駱駝、熊和河馬的肉,憂愁地納悶自己婚禮上不知會有什麼佳餚。他受夠了女裁縫咂咂嘴要他過去,只為了討論他長大多少,幾年內他的胸膛會有多寬闊。她們嘴裡銜的針像冰一樣閃閃發亮。
落雪令人欣喜,花園裡蠟燭與旗幟繽紛亮麗,宮裡的人都渴望親自嚐一嚐、摸一摸雪。廚房女僕伸著舌頭接雪花,年輕男子帶冰凍的柳橙給他們的愛人。紫羅蘭色與翠綠的裙子掃過小徑;喀喀作響的獸角和上油的公鹿皮做的鞋留下腳印,像新紙上隨意塗寫的墨汁,汙染了純白。男孩有時覺得,自己在這一切中看到女孩——但王宮裡好多黑髮女孩,而他每次跟著披散的黑色鬈髮繞過一叢籬笆、一只種了冬季百合的泥碗或一株光禿禿的棕櫚,結果都只是搽著胭脂、額前戴了珠寶的漂亮孩子。他有時慚愧得連道歉也說不出口。
但他確信她一定會再來。他知道一定會的。低平的天空裡飄滿雪,雪在他頭皮上融化,但他不覺得冷。她就在花園的某處,他確定她就在下一堆雪後等他,因此他已經很開心了。從前她消失時,他覺得她拋下了他,但現在呢——他聽過阿七和蒂勞的故事,不是嗎?他知道自己像獨臂的男孩一樣,是忠心的朋友,而她則像樹妖一樣狂野又可人,不是嗎?冬日漫漫,積雪未融,她也沒出現,而他的信心像落葉松在強風中吹彎了一樣,只削弱了一點點。他像兔子一樣追逐著綹綹黑髮,隨著婚禮之夜漸漸接近,她依然沒出現。狗兒騰躍;鈴鐺叮噹。
婚禮的前一晚終於闇淡地降臨了,空中無星無月。花園裡唯一的光源是高處的炭盆和蠟燭,火焰讓閃爍的冰凍地面映著藍白光芒。
男孩穿過栗樹禮拜堂,裡面從祭壇到走道,一切都罩著布,以免結霜,因此蒂娜薩寶座看起來積雪最深。他經過那兒時,覺得似乎聽到小鳥鳴叫;他心砰砰跳著,衝進雪中跟了過去。他穿過沒開花的玫瑰叢、石榴的黑殼,穿過花朵盛開的冰凍柿子樹和結瘤的刺槐,一路來到花園中央,又繼續去到花園外圍,到了像河一樣圍著王宮區域的大銀門;他以前從來沒跑這麼遠過。鳥叫繼續引著男孩,男孩跑到金絲大門時,呼吸又快又急,滿頭大汗。金絲大門環繞著花園,上面是頭尾相接的場景,敘述著人類與怪獸的大戰,裡面的人有著銀和珍珠的眼睛,鐵鑄的怪獸則帶著怯畏的表情。大門上每隔一小段距離就架著炭盆,後方的林木黑暗深邃。
怪獸身邊,站著身穿紅斗篷的女孩。
這一刻,男孩真感謝他姊姊把那件誇張的東西偷塞進他包包裡——女孩嘴脣蒼白,眉毛覆著白雪,長髮上的雪花有如珍珠。她兩手捧著有著金藍長尾的寶石鳥兒,沒微笑,也沒抬眼。他不確定她是不是在哭,但她的呼吸溫暖,在空氣中結成白霧。
她輕聲說:「我不知道別的故事了。」
「什麼?可是妳說過還要跟我說故事啊!」
「我沒得說了。」
「可是故事結束的話——」
「我沒說故事結束了。我是說我沒得說了。」女孩扯著她那隻鳥兒上的珍珠。
「我不懂。」
女孩抬起眼,墨黑甜美的眼皮下,眼眶眨紅。「我很久以前跟你說過,我是在丟棄的鏡子裡,或池塘、噴水池裡讀眼睛上的故事。我說過讀起來很辛苦,一次只能讀一隻眼,而且我得倒著慢慢讀,那樣的苦差事總得這麼做。我跟你說了我左眼皮和右眼皮上的故事,說了我從鏡子、噴水池和池塘裡能讀到的故事。能說的都說完了。剩下的是從一眼開始、另一眼結束的故事,字句橫過兩邊的眼皮和睫毛,彼此交疊——那些故事我不知道,所以沒辦法說。我不能閉上眼睛,還從水裡或玻璃上讀那些字。我沒辦法看那些故事。」
男孩張開口,欲言又止,最後喊道:「可是我還想聽啊!」
女孩微笑了,他從沒見過那麼徐緩的微笑。「我的王子,願意跟我說一個故事嗎?你能從我閉上的眼睛讀故事,讓我喉嚨休息,讓我聽聽我身上寫的最後一些東西嗎?」
「可是……我做不到啊。我沒辦法像妳樣說故事。我不像妳,不知道怎麼說故事,而且不曉得怎麼模仿那些聲音說話。」
「都已經寫在那兒了。拜託。我好想聽。我想知道等在我皮膚上,等著被述說、傾聽的是什麼。我跟你說了那麼多——你當我是朋友的話,就跟我說一個故事吧。」
男孩面紅耳赤,在火光下把自己的斗篷鋪到堅硬凍結的雪上,給了女孩小小一瓶橙酒和一片河馬肉,兩人一致覺得河馬肉不太好吃,嚐起來有點像在嚼塗了層蜜的泥巴和河水。最後,男孩才彎身向前,直到兩人鼻子幾乎碰在一塊兒。他像之前一樣看到她眼睛上的線條和文字,而愈是仔細看黑斑,就有愈多的字湧出來迎向他,字母和印符則沒入其中。他頭暈目眩,也閉上眼,像波濤洶湧的海裡被拋來拋去的小船一樣穩住自己,然後再看一次,那些字還在那兒平靜地浮動。一開始他的聲音尖細顫抖,沒有信心,打從骨子裡擔心會在女孩面前表現笨拙。
「在一片星星不會注視的荒蕪平原上,熱風像咆哮的狂風一般襲捲,鼠尾草灌叢低伏在白色岩石上。」他像剛學認字一樣慢慢讀著。「這片平原有個巨大的鐵架掛著巨大的鐵籠,風吹過籠子,就像女人在木板上給人剖開一樣尖聲呼號……」
荒境的故事
天空裡的月亮有如老鼠的頭蓋骨。夜的氣息深藍,又濃又沉,如海床的顏色,卻炙熱燃燒,而金黃的石頭襯著地平線,氤氳顫動。乾渴大地深色的裂痕像尋找一丁點兒水分的爬藤,像四面八方分岔蔓延;三道長長的影子投在大地上。鐵籠降貴迂尊地將欄杆的影子投向塵土中,在那兒與女人和豹獅奇異的影子相交,豹獅坐在那兒,耳朵往前探,顯得機警而好奇。女人用長長的銀鍊拴著她的大貓,銀鍊在風中來回擺擋。她從頭到腳都裹在厚重的黑面紗下,面紗在她身後拍打波動,只露出一對黃如皺縮檸檬的眼睛,虹膜是病態的紅色。
而籠裡漫著煙。
煙吹過鐵籠。精巧的鐵條扭曲成一個交叉的圓形,用比男人手腕粗的鍊子懸掛在鐵架上。籠子黑暗銳利又刺人,旋轉、飛旋打著轉,惡毒卻受困於原地。煙裡有兩隻橙紅色的眼睛閃爍著,眼睛充滿敵意,眼上垂著火焰睫毛,上面挑著火焰眉頭。那團煙猛地彈了兩下尾巴,一具身體便從煤灰中半升起,有如一隻美人魚躲在自己帶鱗的尾巴後窺視。她的臉上都是火,頭髮是滾滾煙霧的來源,從她深色燃燒的身影旁彎彎地吹開。但她的腰也飄出了煙,她的肉體像美人魚的身軀一樣在那兒消失,而該長腿的地方,卻是一片漆黑,陣陣紅色火花蜿蜒冒出。她一絲不掛,飽受屈辱,胸部的尖突是怒火,肚臍是一點醜惡的紅光,曾經屬於她的東西在籠子下積成一堆,宛如葬禮的供奉。
兩名女性像綿延孤岸上的兩隻兀鷹,靜望著對方半晌。豹獅聞風不動,尾巴偶爾掃過不毛的土地。
最後,豹獅開了口。
「親愛的巨靈,是誰把妳關在這兒的?」
那東西又彈動煙霧,烈火熊熊的眼睛迷朦了。在她身後落下的月亮襯著深藍的天空,顯得乾癟而透明,似乎也被吸乾了。
她以氣音說著:「這把戲真不錯。長的高的那個不會說話嗎?」她的聲音活像青綠的枝條剛著火時的劈啪聲。
豹獅打個呵欠,揚起觸鬍,粉紅的舌頭一時忘了收,垂了出來。
「她的喉嚨不方便,請妳見諒。她叫毀壞,我叫分離,我們一起旅行,是因為這樣正好適合。我們原先不知道這堆廢棄物是牢籠,沒料到會在這裡發現這樣的東西。」
籠中一綹纏捲的煙散向籠外,往戴著面紗的女人飄去。煙隱約帶著細瘦的手的形狀,三隻指頭上繞著火焰,彷彿富婆的戒指。
豹獅叫道:「拜託!別碰她,千萬不能碰她。」
毀壞疲憊的眼睛溫柔而帶著歉意,從黑袍中伸出一隻手以便解釋。她的手幾乎萎縮成皮包骨,皮膚像沙漠一樣龜裂開來,指甲則黑而乾裂。皮膚正一片片剝落,在炙熱的空氣中從她彎曲的指頭往後掀。她把面紗蓋回手上,羞愧地垂下頭。煙縮了回來,巨靈將之收回吊掛的籠中。
「只要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同情妳,我們就和妳分享食物和比琥珀珍貴的水,但妳萬萬不能碰我的小姐。她不太舒服。」大貓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眼睛又黑又圓,毛皮被沙鼠咬得一抽一抽。
巨靈瞇起眼睛思考,伸隻繪有紋路的手揉揉鼻子。她的手掌上有發光的圖案,圖形向內彎曲旋轉,白熾的墨水繞著緋紅的圓,如果她有掌紋,應該就在那兒吧。
巨靈終於開了口:「我是灼枯,在五大沙漠和六大海間,我是卡許三女王中,戴著餘燼王冠的女王。」
分離刨刨土地,問道:「灼枯,妳為什麼給人關起來?」
巨靈沉默了,煙霧顯得暗沉而若有所思。「我領軍越過九大海和六大沙漠,圍攻阿佳納巴城……」
象牙籠與鐵籠的故事
卡許城裡有六座城堡、六個王座與六個王位,三個女王與三個國王各有自己的宮殿。我是餘燼女王,而我炭火支撐住的宮殿立在長長的大道未端。火仙丹木夾道的大道兩側,有我姊妹火絨女王、灰燼女王的宮殿,還有我兄弟爐床國王、柴枝國王和燧石鐵砧國王的堡壘。我稱他們為姊妹、兄弟,當然無意表示他們和我有任何親戚關係——千萬別這麼想。君王是一個龐大多樣的團體,這是我和他們之間唯一的關係。
卡許卡許是世上最早的巨靈,而我們都是卡許卡許之國的繼承者。卡許卡許將我們其他巨靈從他鬍子的煙裡將我們紡出來,讓黑色的捲鬚蔓延世界各地。他心中的聖火是純粹無雜質的火焰,那就是最初我們受孕的地方。他的目光讓翁鬱的森林起火燃燒,人類女性雖然有著冷酷的眼、冷酷的心,也會臣服於他的威儀。世界各處的平原上,他飄渺的孩子在他周圍嬉鬧,在他面前起舞,而他帶領著他們榮耀強盛。
他告訴我們,我們不必像其他人一樣忙著建立城市,城市自然會在我們周圍建造;畢竟有誰不需要火呢?因此,早在沙度基安得到那個名字之前,他就立於沙度基安的中心。整個城市就在他四周翻騰湧起,包括所有的玫瑰、所有的鑽石!無論是什麼地方,只要他吩咐,巨靈隨傳隨到,進進出出那座閃亮的城市,而他的名諱在我們之中依然神聖、光明、燦爛。卡許卡許美麗非凡,他的鬍子是較弱小的巨靈無法奢望的奇觀,他能從身上拔下燈火、珠寶、火焰和雲朵的書卷,像麵包一樣分送,因此深受愛戴。他在我們真正的第一個家那些尖塔頂上舞蹈,向血染似的落日高呼著詩句,唱啊!為千年來熊熊燃燒的巨靈高呼!而遠遠的下方,群眾仰慕地尖叫。卡許卡許在那段日子裡實現了多少國王的願望?燒穿了多少處女膜?這座城市以他為名;多少世紀之後,人類的少女依然在額前塗灰粉以示哀悼。
我們吹著黃銅和瑪瑙的號角,告訴全世界這些事。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在卡許之城度過童年,盼著腰帶擊上金鈴,晚餐有香甜的蜂蜜可吃,而在我成長過程中,我也是這麼相信的。一世紀又一世紀過去,我們就是這麼告訴世人的。我年輕時,我的煙霧髮絲蜿蜒旋繞,長到得在臀部掛著兩只銀絲織的籃子來裝,其他孩子都取笑我,直到受父母勸阻——那樣的特徵其實表示我將成為女王,就像卡許卡許的大鬍子表示他是國王。他們把我從我的小房子帶走,還讓我帶走了三組金湯匙和非常高級的茶壺,帶我進入王室的奇妙世界。當時我才十歲,不過這對我的人民而言,已經是確確實實的中年了。我們不會老去,但消逝的速度卻遠比其他種族迅速。我們閃爍、冒出火花,然後便死去。如果被封蠟和圈套封進燈之類的東西裡,就像煤炭不點燃一樣, 能活久一點,但不是永遠。煤炭不是活的,關起來的巨靈也一樣。這就是我們的選擇——只要在開放的空氣中燃燒,我們就維持不久。因此九歲時我已經不是孩子了;然而,我的王權依然稚嫩,有如失去胸脯的哭泣孤雛。
灰燼女王珂希努爾和爐床國王喀阿米爾各抬著我的一只籃子,護送我到餘燼堡。他們黑皮膚上鑲著燃燒的寶石,鼻上穿著燃燒的金環,在我眼中顯得美麗而駭人。珂希努爾像鷺絲一樣高高瘦瘦,全身是黑煙,沒有一點火花;喀阿米爾比較矮胖,灼燒的皮膚上漂亮的皺褶波動著,在他肚臍裡盛著一大顆黃晶。他有隻金黃的獨眼,眼中的火焰像蘇菲教僧侶一樣飛旋舞動;另一眼的眼窩則空洞焦黑。
紅磚地板中央有一缽歪傾燒紅的炭火,那是我王位的象徵。女王讓我坐在紫色的坐墊上;我小心翼翼地調整我的煙,以免燒到流蘇。她身處高位,忙到無暇關心一躍登上王位的新女王,但盡可能堅決而溫柔地說話。他們倆都很愛戴前任女王;前一個冬天一場家族晚餐裡,前任女王就這麼起火燒盡了,使現場小小錯愕了一番。
珂希努爾已經將近十五歲高壽了,她穩穩把我放在王座上,說道:「聽著,小姑娘。不該讓妳坐在王位,卻不知我們的歷史,因此我們有責任告訴妳舊世界的情況和緣由。不過我們和柴枝國王有個午宴之約,他要請吃我們最愛的焦蛇怪,所以拜託專心聽,免得我們得重說一次……」
最初的巨靈
妳想必把卡許卡許當作祖先和最敬愛的守護神敬拜吧。別再這樣了。現在就停止。
卡許卡許之名受人景仰、畏怖,不旦是為了巨靈的榮耀,也是為了不讓我們只為滿足漁販之女的願望,無止境地受迷惑而成為各種廚房用品。寶貝,別擦那盞燈,免得卡許卡許跳出來一口把你吞了!小親親,別拿湯匙互敲,卡許卡許會從湯匙柄翻騰而出把你吃了!然而,我們自己不敬畏,卻期望別人會敬畏,沒道理,因此只有精挑細選的少數巨靈才知道煙魔的祕密過去,現在,妳是其中一員了。這個制度讓巨靈敬畏他們的君王,也讓全世界敬畏巨靈。
親愛的,閉上妳的嘴,引來飛蛾來可不好。
卡許卡許不是第一個巨靈。最早的巨靈是個可憐的蠢傢伙,名字誰也記不得,是星辰最初走過大地時燃起的火,是沒人要的孩子。所有燒焦的東西都像吐出櫻桃核一樣吐出巨靈,而我們雖然不斷燃燒,無法冷卻,但仍得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們不過是被遺忘的焦黑孩子,出生時完全沒人注意。我是從灼枯之草升起的巨靈的孩子。喀阿米爾是焦熱之風的孩子。卡許卡許希望與我們發源有關的一切知識,在以他為名的火中消毀,但女王彼此商議,留下自己的記錄。妳成了我們的一員,我們得查查妳的出身。所以,雖然很多人說卡許卡許是最初的巨靈,但他其實不是。不只一般巨靈以卡許卡許之名祈禱,許多愛體面的祭司和身居高位者即使在翻騰的心中知道真相,卻依然愛在故事裡說卡許卡許那種能得到任何女人、催毀任何男人的巨靈。
卡許卡許的確很強大,能將他的煙化為波動火焰的形狀,嚇唬年幼的巨靈;還史無前例地將煙染上顏色,有藍、有綠、有紫。他們說他的模樣非凡,而我們至少對這件事毫無異議。這些飄渺的火焰在他頭旁波動著,顯得神采飛揚,傲然自負。另外,後來稱為沙度基安的那座城市形成之初,他的確在那兒。他拖著燃燒的腳跟環繞那塊滿地糞尿的空地,當時那兒連貧民窟也稱不上,妳的城堡所在的長長大道,當時只是條紅土溪。在泥濘中因卡許卡許而醒目之地,不久就因玫瑰之城迅速發展的道路和市場而遜色了。我們依他的指示,什麼也不建造,只靠竊取和許願,讓我們最早的居住地憑空出現。卡許卡許告訴我們,別的巨靈不能像他一樣許願,因此祈求他不認同的願望就算犯法。巨靈的偉大天賦是許願,卡許卡許離世之後,我們將許願變成一門科學,只不過後來小孩子不再把我們關進油燈或湯匙裡,這門科學也不再廣為應用了。我們還小的那段日子,雖然沒辦法做得多好,但他也沒好多少;他許願要一座雪松和獸角的宮殿,升起的卻是巨靈區那些搖搖欲墜的樓塔。不過,他給我們多麼美好的承諾啊!等他知道得深、更多,等到夠多的國王成為他的奴隸時,他會替我們建造多棒的建築!他會讓我們變得多長壽呢——讓我們不再像蠟燭,點燃與熄滅都在傾刻之間。我們將成為延續千世萬代的火焰。
他後來的確知道得更多了,成為許願的奇才,但他從不為我們發揮他的天賦。他偏好只有火光、沒有煙的東西——即使再小,在他眼中也比我們美麗。
我們不該告訴外人,沙度基安不完全在煙之生物的掌握與管轄之下。就讓卡許卡許的鬼魂帶著我們和他的鬍子一起飛翔吧。我們不在乎。
卡許卡許為自己從地中拔起的巨靈區成了貧民窟,那兒的巷子裡有火焰亂竄,陰影中有鮮紅的牙齒閃過。巍巍顫顫的樓塔高高蓋向玫瑰拱頂,直到黑色塔尖穿過淡粉紅的花瓣之間,而我們在角樓之間太侷促,我們的煙甚至被擠穿牆面,在一層層樓之間噴出火焰。卡許卡許在市長官邸吃葡萄,和他商議如何在鷹架工人做完工爬下來時省點他的錢,同時巨靈卻在他們黑黑的破房子裡受苦流淚。他眼旁環著火焰在頹倒的塔頂起舞,在惡臭的風中飄著火花, 向血紅的落日高呼詩句,唱啊!為千年來熊熊燃燒的巨靈高呼!而遠遠的下方,貧民住宅在一片汙穢中仰慕地尖叫。
卡許卡許要我們這麼活著,我們就這麼活著;他要我們編捻他的鬍鬚,我們就編捻他的鬍鬚。畢竟他的鬍子比誰都長。所以後世的君王才會用那麼奇怪的標準遴選。每個王位都有自己偏好的要求——最熱的火、最甜美的聲音等等。卡許卡許聲稱他的鬍子讓他得到統治權,我們該用不同的標準選君王嗎?他揮揮鬍子,便把一整個種族壓扁成六座尖塔。他告訴我們,那只是開始,而我們不久就能在瑪瑙、黃銅和藍火似的絲上棲身。然而,隨著一個個模糊的黑夜與白日劃過巨靈區,我們臉上依然貼著其他巨靈的煙,無法呼吸。
最後,我們忍無可忍了;駭人的惡臭、未掩埋的屍體和頹敗的建築已經將我們包圍。只有少數巨靈還記得開闊的草原。牧師沒告訴妳,卡許卡許後來在貧民住宅的階梯上被煙勒死,身軀起火燃燒。樓塔一磚一瓦拆了,一個冬天之內,簇新的大理石和懸掛的繡氈之間再也占卜不到半根焦黑木材。我們找了盡可能遠離沙度基安和我們可恥回憶的一座新城市,把他埋在十字路的中央。而我們不許任何願望,僅憑雙手就建立瑪瑙與黃銅的城市,擁有藍火似的絲質長沙發,並用綠柱石鋪出長長的大道,在大道旁建起六座城堡,記念從前的恐怖之塔。
但罪惡感像馴牛師一樣驅使著我們。巨靈在埋葬卡許卡許的地方建起雕像,用他的名字發誓,隱瞞他們做的事,並將那座城市命名為卡許,希望能避開他幽靈的怒火,召來一點他從前的美麗。我們告訴世人他很偉大,只對彼此輕聲細語地說:他不在了真好。我們沒看過他長鬍子的鬼魂出沒街道間,但是不是因為我們讓他的聲名完美無瑕,誰也不敢說。語說回來,我們祈求事事平安,不是嗎?
長髮的小東西,妳明白了嗎?我們可以去午宴了嗎?再讓我們聽到妳用那畜牲的名字起誓,我們就割掉妳的舌頭,讓妳永遠不再犯。
《黑眼圈Ⅳ:灼枯之書》
花園中
花園下起了雪。
這種事並不是史無前例。蘇丹的書裡一定有仕女穿著毛皮衣領在雪中嬉戲的木版畫,她們腳邊還會有繫著鈴鐺的小狗蹦蹦跳跳的。女孩還小時,下過幾場小雪,不過絕不是這樣,這是能讓人陷入及膝冰雪中的暴風雪。檸檬樹的葉子太久沒結霜,因此即使躺在床上巍巍顫顫,年事最高的貴族女性,也只能依稀記起當時她的狗是什麼顏色,狗脖子上叮噹作響的鈴鐺是什麼聲音。湖面凍結成蘆葦包圍的鏡子,松針裹了玻璃,冰冷沉靜地閃爍。孩子嬉戲;狗兒騰躍。新的木版畫趕著印製。
栗樹的樹幹凍住了,婚禮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