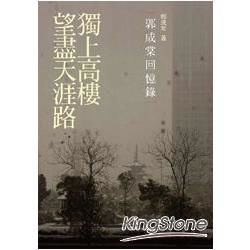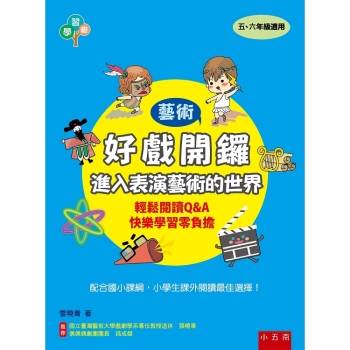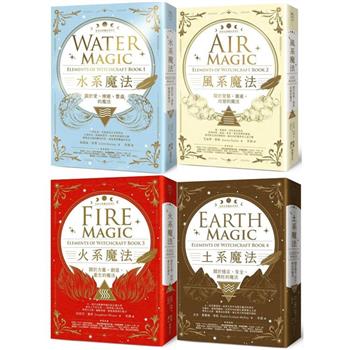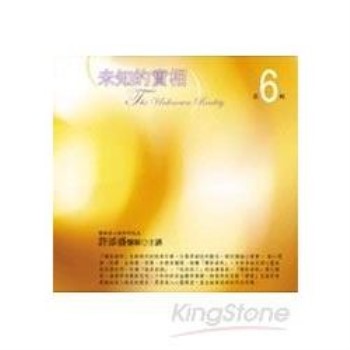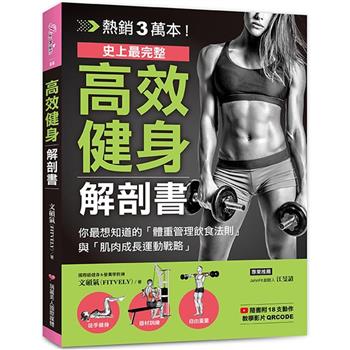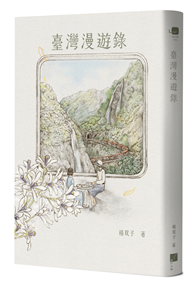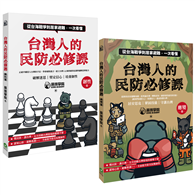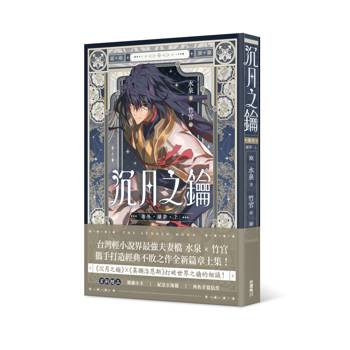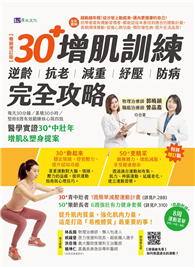序
本書讀者都應該知道:作者郭成棠教授所經歷的時代是一個多患難和多變幻的時代。單就中國而言:他曾經過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年代。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人要圖存,就非易事。如果還想將生命在遍地荒蕪和荊棘叢生的土地上,堅強地成長,並茁壯起來,不但需要堅強的意志,就更非有雄偉的資智及鋼鐵的毅力而不能也。
郭氏的回憶錄一共八章,分別刻畫出他人生的三個階段。前三章記錄其四川省隆昌縣郭氏大家族的光榮事蹟和遷移的歷史。談到他自己的家庭時,很不幸,他還在讀小學時,他的父親便突然去世了。按照家規:他的伯父便成了他們家裡財務的統率者。可是不出兩年,他家財產全都被他這位不務正業的伯父耗盡。幸好作者的母親頗能吃苦耐勞,親自製布縫衣以教養其子女。同時本書作者志氣昂然,能以一介清寒學子,自小學畢業後,從全縣千百個學生競爭中脫穎而出,考入縣城之唯一公立初級中學。畢業後更能競入全公費之省立高級師範學校修讀,最後更能考入首都之國立大學,以完成其在國立之高等教育。他這種「過五關,斬六將」的精神,確可用作鼓勵後輩發憤圖強的好榜樣。
回憶錄的四、五、六章,是敘述他在一九四八年開始的逃難過程——從南京到上海,從上海到廣州、香港,再到台灣。顯然的,這段時間,他雖然經歷了一介「無產階級」的實際生活,但因受過高等教育,內心世界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從未休止,他在台灣三年多,一直在台灣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教書;同時也恢復起他讀書時代搖筆桿的生活;辦起當時台灣有名的「兩大刊物」(當時在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書的殷海光教授認為台北市的《學生》雜誌和高雄的《拾穗》是台灣的兩大刊物)之一的《學生》雜誌來了。一九五三年,他被台灣省教育當局評選為當年全省十大優秀教師之一,並資助到美國深造。到達美國之後,他也和當時留美的中國文、法科學生一樣,苦讀、打工、摸索,終於找到了歸宿——學到了隨時隨處都可以找到工作的資訊管理學。
在這幾章中,他敘述他自己抗日逃亡和內戰時期的克難生活,以及有幸而自台灣流亡海外,所有艱辛奮鬥的歷程,真是字字血淚,句句珠璣。對於這一代人心理的描述,應該是社會學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對於意欲留洋的後生小子,更是最好的一面鏡子。
郭氏回憶錄的最後兩章(七、八章),是記錄一九六一年夏秋之交,他到了匹茲堡大學,專任圖書館專業資訊管理員以後的生活,以及三十多年來,在事業和學術上的成就。這部分的記錄,實際上已曾發表在他出版的《學府鏖戰錄》的單行本上。
一九六一年,我個人也剛吃盡苦頭,從加州柏克萊經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完博士學位課程,找到了一年代課教書的工作,碰巧也到了匹茲堡大學,且與郭君住在同街的斜對面。每日上下班雖非同進同出,卻也日日搖手對望。平時對話雖不多,到了週末,卻也一同參加國際學人活動,以解除工作上的壓力,相交一年,因而成了莫逆。
如眾所周知,在美國自艾森豪總統時期開始,東亞研究便成了熱門。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核子」俱樂部,東亞研究更是「需才孔急」。當我正在為博士論文努力之時,郭氏已在籌畫如何為匹茲堡大學建立一所屬於全國第一流的東亞圖書館,以供匹大學生和學者之用;他同時也開始選讀博士學位的課程。在短短四年中,他的兩個重大使命都已順利的完成了;換句話說,他不但順利的獲得了他的博士學位,匹大的東亞圖書館,在他的奮進下,也很快就有了第一流的藏書,而且管理和運作方式也是最進步的。更與遠東第一流的圖書館建立起交換的關係。
郭氏為了匹大的東亞圖書館,每天都是忙碌無暇,只有晚間才有屬於自己的時光。所以他總是利用晚間修改他的博士論文。不過,他的大著《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一經出版,他的學術地位立刻建立。現在來看他整個學業和事業的歷程,真是千辛萬苦,努力不懈得來的。在這過程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從不氣餒,也從來未打過一次敗仗。
他在專業領域的成就,也明顯的被同行所確認。他不但完成了博士學位,出版了博士論文,建立了具有規模而龐大的東亞圖書館,更是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機構的兼任教授;在大學圖書館系統中,升到了最高的階級。在校園外的一些學術團體中,他也登上了極峰。比如在全美東亞圖書館專業人員協會,他曾做過主席;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他也被選任過會長。更重要的,他曾被推選為著名的「福爾布萊」學人(The Fulbright Scholar),到台灣講學一年。後來又被邀參加過台灣「國建會」。也曾做過中國大陸的重點大學的訪問教授等。無疑地,他已成了一位國際知名的專家學者。
郭氏自大學時代起,就已負責編寫學生刊物工作,更不斷地在報刊發表文章。故在他的回憶錄的第二部分,便選擇了一些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泛泛地討論一些過去和當前的大問題:如史學和哲學的關係,英雄和時代的關係,國際均勢和冷戰,地緣政治和空權,馬克斯主義和聯合國,蘇聯和史達林後之諸領導人等題目,都作了清晰的解析和看法。有些情景的描述是特別有價值的;如解放前夕的南京,國民政府初遷到台灣時台灣的一般民風和情景。五十年代美東中國留學生的日常生活等,皆富有史料的價值。
我和郭氏雖然在他生命的第三階段才相識,但有整整一年,曾深切地交往,故對於他的內心世界,除他的夫人外,恐怕我是知之最深的了。譬如說:有多少人知道郭氏能文,而且也可跳一流的交際舞;他的烹調技術尤為出色,即使是今日中國大陸的一級廚師,也少有出其右者。
◎朱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