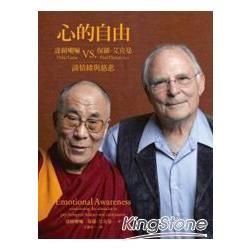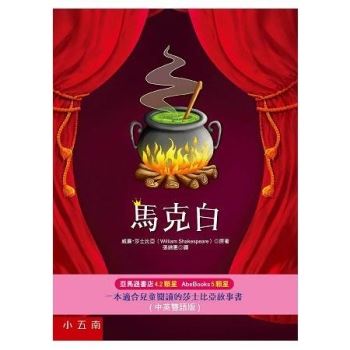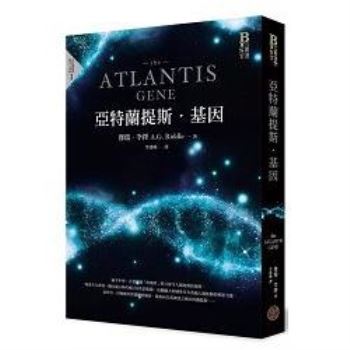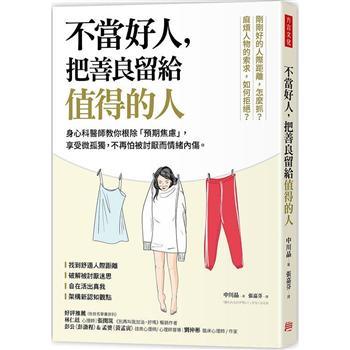世界第一的讀心專家vs.洞察人性的宗教大師
引領我們深入了解人類情緒,看見它的陰影與美麗
保羅.艾克曼,全球頂尖的情緒心理學家
專長面相術,任何人的臉部表情變化,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他是FBI和CIA的重要顧問,讓說謊的罪犯無所遁形
他也參與動畫電影的製作,讓卡通人物(如《怪獸電力公司》)的表情栩栩如生
達賴喇嘛,備受世人尊崇的宗教領袖
歷經流亡歲月,看盡世情變換,對人性有深刻觀察和體悟
卻仍堅持和平的價值,呼籲良善與慈悲
這兩位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精彩人物
一位是冷靜客觀的科學家,一位是溫暖自在的修行者
他們從達爾文一路暢談到禪修的科學基礎
又從心靈的修鍊,談到神奇的能量體驗
三十九個小時的熱情對談
引領我們看見人類情緒的本質和其千變萬化
期盼將人性蘊藏的破壞力,轉化為愛與慈悲的根基
本書特色
◎達賴喇嘛的最新著作,書中忠實呈現達賴喇嘛與艾克曼的對話。
◎公視最新影集「謊言終結者」就是以本書作者之一,擅長「讀心術」的科學家保羅.艾克曼的故事為藍圖。他說,人的表情可以裝,但臉部的肌肉、表情、聲音仍然會洩漏潛意識的訊息。這個影響二十世紀人類的重要心理學家,與達賴喇嘛之間有一段精彩且充滿火力的心靈對話。
作者簡介
保羅.艾克曼 Paul Ekman
是世界第一的臉部表情專家,也是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的心理學名譽退休教授。他曾得到許多榮譽,包括美國心理學會的傑出科學貢獻獎,還被列為二十世紀前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
艾克曼是世界知名的專家,鑽研臉部表情、欺騙和情緒,在四十年研究生涯中,曾研究新幾內亞部落民族、精神分裂病人、間諜、連續殺人犯和職業殺手的面容。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警方、反恐怖小組等政府機構,以及製作《怪獸電力公司》的Pixar動畫工作室,常常請他當情緒表情的顧問。他身為十四本書的作者或編者,其中包括《心理學家的面相術》、《說謊:揭穿商場、政治、婚姻的騙局》,美國和英國的電視節目常常向他諮詢,甚至在電視上現身說法。艾克曼目前住在北加州。
達賴喇嘛 Dalai Lama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生於1935年7月6日,在西藏東北一個叫做塔澤的小村莊。兩歲的時候被認證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五歲的時候登基接掌西藏的政治權力。1959年被迫流亡,從那時起就為了和平解決中藏危機而奮鬥。他持續的宏揚慈悲哲學,在1989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