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摘錄之一】
﹝台城悲歌 粱武帝﹞
世稱的六朝──英雄與小人同朝共舞的政治的六朝,征伐與殺戮難分難解的軍事的六朝,雕龍與畫蟲平行並重的藝術的六朝……每當想起,那一幕幕早已褪色的史劇常常會浮現在眼前,如夢幻煙雲、流水落花,其主角們或衣冠飄忽、放浪形骸,或酗酒吃藥、醉生夢死,他們崛起又毀滅、大喜又大悲、殺人又被殺的人生和命運,常常讓人感慨繫之,而其中尤以那位史稱梁武帝的蕭衍最令人欷歔難禁。
這並非因為他的文武全才,也並非他在六朝列代皇帝中活得最長(八十六歲),在位最久(四十八年),更並非他下令編撰了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啟蒙課本《千字文》,而是因為:他作為一個人,曾盡享人世之尊又飽嘗世間之苦;作為一個生命,曾盡顯剽悍奮發又終歸荒唐頹廢;作為一個帝王,既是開國聖主又是亡國之君……
蕭衍也算是皇家出身,其父蕭順之因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而被封為侯。出生在這樣的家族中,若是在別的時代,或許是幸運而令人羡慕的,但在南北朝這樣的亂世,卻並非一定是什麼幸事。宋齊時民間有一首歌謠:「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縱觀六朝列代,圍繞皇權的爭鬥,強權的統治者似乎總愛拿自家人開刀,「骨肉相殘」是那時最常見的皇家鬧劇。因此,劉宋後主劉准在蕭道成屠刀下留下的最後遺言竟是「願後身勿復生王家」。
天性聰慧而又敏感的蕭衍深深地知道,父親雖貴為王侯,但並不能保證自家不發生突然某一天被滿門抄斬的事情,從這一點來說,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並不如普通百姓牢靠。貌似平靜的深宮大院實際上是風霜的迷宮血腥的漩渦,豪華奢侈的冠蓋金輿背後,潛藏著最為血腥的殺戮。蕭衍便是懷著這樣的心態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與青少年時代。這樣的人生機遇,使他較早就懂得了韜光養晦、審時度勢,也懂得了豐滿羽翼、積聚力量,更懂得了抓住機遇,當機立斷。而這一切又正是一個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
年輕的蕭衍給世人的印象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世家翩翩公子,而實際上,他無時無刻不在觀望,不在等待,他冷靜而沉著,不急又不躁,自己的心跡決不露出半點,哪怕在自己最親的人面前。
機會終於來了,蕭衍二十六歲那年,他以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從事的身份被蕭子良推薦為襄陽太守,出鎮邊城襄陽,從此蕭衍棄文從武,開始了他的別樣人生。
蕭衍初出茅廬即鎮守襄陽,這是歷史和命運賜給他的一次機遇,他當然緊緊抓住不放。蕭衍在襄陽守任上充分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更充分顯示了他出眾的政治才幹。
西元四八三年初,齊高帝臨終之前一下子委任了六名託孤大臣。憑藉自己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覺,蕭衍斷定「齊將大亂」。看來,此時在風雨中飄搖的南齊王朝亟需要一位政治強人出來或收拾殘局,或另起爐灶了──這個人除了要有過人的才幹和膽識外,最好要有一點皇族的背景,如此他就比較熟悉和瞭解其中爭鬥的種種人事和機關;最要緊的是他決不要在明處,最好在政治中心之外,藏在暗處,要不,一旦進入齊明帝蕭鸞和東昏侯蕭寶卷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皇帝的視線,他會早早的人頭落地了──此時的蕭衍,正是這樣一位政治強人。這是歷史對他的選擇,也是命運為他作的安排。
蕭衍一面急告遠在建康的哥哥蕭懿,千萬不要「赴闕朝覲,靜待事變」;一面在襄陽城裡整軍經武,厲兵秣馬,靜待時機,一舉成事。不久,他的哥哥蕭懿,因不聽他的勸告果然被殺,他便乘機兵起襄陽,並聯合各路反東昏侯的義軍,順江東下,矛頭直指建康。
西元五○一年,蕭衍率軍攻入建康、兵圍台城,隨即位居宰相──實際上齊和帝蕭寶榮已在他掌股之間。
不久,台城中便又一次演出了一幕「禪代」的活劇,皇帝僅僅做了兩年,人卻殺了不少的齊和帝蕭寶融,將還沒坐熱的皇位讓給了蕭衍。蕭衍稱帝,改國號梁,史稱梁武帝。
開國之初有一個階段,梁武帝的確沒有令他的國家、百姓失望,也沒有令歷史失望。
據《梁書》記載,梁武帝稱帝以後,他「夕惕思治」。例如,他曾公開貼出告示,徵求朝野各方對朝政的意見,並在公車府設了兩個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兩個意見箱),一個叫「謗木函」,一個叫「肺石函」。「欲有橫議,投謗木函;……冤沉莫達,投肺石函。」(《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五)凡「不便於民」的政策,只要「具條與聞」,達帝聰,經過斟酌,覺得有可取之處的,便一定施行。在自身生活方面,梁武帝還十分注意約束自己,他十分的勤於工作,不講享受,幾近到了苦行僧的地步。
這樣的成功領袖,倘若再有一點藝術天分那更是一種錦上添花,無可挑剔,而對此梁武帝蕭衍是一點也不缺乏。蕭衍的父親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因軍功封侯。生於侯府的蕭衍,在南朝這樣一個文風盛行的時代,自然和許多士家少年一樣,在文學藝術上都曾下過相當的工夫,有著相當的造詣。的確,年少時的蕭衍性喜文學,且表現出很高的天分,他曾與沈約等人以文學才能而同為齊宗室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從事。儘管他後來位登至尊更多靠的是他的武功,但他最初在宗室士子中知名靠的卻是文學。
多才多藝,對於一個統治者來說,也許並不必苛求,也沒有必要,但這對於其個人魅力的增加自然是大有裨益。於是梁武帝稱帝後,自以為將江山收拾得差不多了,便重操起了文學的舊業,且一旦玩將起來,絕對是專業水準。
由此看來,梁武帝作為一個帝王或政治領袖,該有的似乎都有了,剩下的就看他的大有作為了。此時,歷史是很看好這位皇帝的,儘管只是一位割據王朝的皇帝。
然而,事實上這實在只是人們和歷史的一種一相情願。
不知不覺之間,梁武帝變了,變得前後判若兩人。
終於,冥冥之中註定了的事情發生了。同泰寺的嫋嫋香火還不曾散去,梁武帝還沒想明白,聽慣了的晨鐘暮鼓忽然之間亂了平時的節奏,台城的紫氣就突然之間被無情的烽煙籠罩了。侯景率領叛軍將台城團團圍住,一場浩劫就這麼開始了。
昨天還是晨鐘暮鼓、經幡飄飄,今天便是血肉橫飛、刀光劍影;昨天還是錦衣玉食、美女盈懷,今天便是饑不擇食、四面楚歌;昨天還是萬人之尊、天之驕子,今天便是我為魚肉、人為刀俎;昨天的歸降客,便是今天的奪命鬼;昨天的金鑾殿,便是今天的望鄉台。
一切變化彷彿都發生在瞬間。
然而一切變化真的都是在瞬間發生的嗎?
當初,侯景以東魏將領的身份擁兵十萬、以河南十三州請求降梁,梁臣謝舉等人曾激烈反對,但梁武帝以為這是統一中國的絕好機會,理由是侯景求降與他剛做過的一個夢相合。於是梁武帝下令收納侯景。殊不知,此舉不只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引狼入室,而且立即引起了本是友國東魏與梁的反目,是一次「雙賠」的買賣。
太清二年(五四八年),侯景據壽縣起兵,以討朱異、周石珍為名,襲取譙州(今安徽省含山縣),攻下曆陽(今安徽省和縣),引兵直驅建康台城。這時梁武帝才相信侯景叛亂是真的了,但一切已經太晚了,他只能在被圍的台城中等待活活餓死。
我們無法將那個在台城之中因得到侍者的一個雞蛋而淚流滿面的老人,與荊襄大地縱橫馳騁、漢水岸邊縱論攻戰、枕席之間奪人社稷的英雄形象重疊在一起,但他們確確實實是同一個人。他在臨餓死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梁之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複何恨!」既是如此,那麼他最後的流淚意味著什麼呢,恐懼,留戀,後悔,抑或自悼?只有他自己知道。
【內文摘錄之二】
﹝一死即永生 包拯﹞
宋仁宗嘉祐七年(西元一○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開封府衙,一切都像往常一樣,卯時一到,漆黑的大門準時被轟隆隆地打開。府尹包拯似乎已端坐大堂之上多時,隨著他輕輕的一聲「升堂」,堂下衙役齊聲高呼「威武」…… 一場審判就此開始。
然而,訴訟雙方已跪於堂下好一陣了,卻遲遲不見包大人拍下驚堂木問案。
衙役們有點奇怪,不由得朝大堂之上的包大人看去,這一看便看出了異常──平時總正襟危坐的包大人,此時竟然歪靠在椅子上,而且頭也耷拉了下來。
不好!包大人病了!
衙役們不顧一切地蜂擁而上,一面驚呼著「包大人!包大人!」一面從椅子上抱起已昏迷了的包拯;幕僚們也顧不得規矩,從幕後衝到了幕前,連忙招呼「退堂,退堂」,並高聲呼叫:「快去叫大夫!」……
僅僅十三天後,也就是五月二十四日,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名臣、清官──包拯與世長辭,終年六十三歲。
開封府衙的門楣上披上了黑紗,門旁「回避」、「肅靜」的燈籠裡的紅燭被換成了白蠟,且燈罩也被罩上了白紗,那慘白的燭光連同死亡的氣息一下子彌漫了全城,讓全城每一個人都感到悲傷與壓抑。
包拯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在危機中掙扎自強的時代,一個於紛爭中與狼共舞的時代,一個註定要成就真心英雄悲情人生的時代。
包拯就是時代造就的一位特殊的英雄。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通過「黃袍加身」取得政權的,所以他深深地知道掌握兵權對於鞏固其統治的重要,於是他一面通過「杯酒釋兵權」取得了對於軍隊的絕對統治權,一面提倡「恭謹慎為賢」,也即提倡謙恭、謹慎、聽話等。這樣的統治方針,固然使得宋代沒有出現唐朝時藩鎮割據的現象,對鞏固封建統治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其負面效應不久便顯現出來了──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代九十多年後,朝野上下循默苟且成自然,頹唐懶惰成習慣,紀綱不修,貪污腐敗之風成蔓延之勢,盜賊並起、邊關告急,看似風光無限的大宋王朝,實際上危機四伏──它像一位百歲老人,雖然看上去面色紅潤,但實際上已多種富貴病纏身,它需要健身活血,需要振作醒腦,而要完成這一切,甚至需要一點強迫與強制,因此,大宋王朝呼喚有人能給它一記猛拳,一劑猛藥,甚至一劑強心針。
一○二四年,趙禎即位,史稱宋仁宗。三年後,包拯考中進士。
包拯進士及第後,朝廷授予他大理評事銜知建昌縣(今江西修水)。建昌是一個大縣,朝廷的這項任命說明對他還是很看重的。然而包拯竟然以「父母在,不遠遊」為理由,拒絕前去上任。包拯的這種後退姿態肯定是驚動了朝廷,甚至是皇帝,因為不久朝廷便重新任命他為和州稅監──與一個縣級市的市長相比,地級市的稅務局長級別上大體相當,更主要的是和州與包拯故鄉廬州相鄰,可以邊當官邊照顧父母啊。朝廷這樣做也可謂是善解人意、仁至義盡了。
但是沒想到,包拯仍然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這讓一般人大惑不解。
或許有人會以為包拯這樣做,是為了以退為進、放長線釣大魚,為自己攢足了資本才出山謀得更高的職位和更大的權力,但是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為一是包拯在家為父母守孝一守就是十年──若說放長線釣大魚,這線放得也未免太長了一些吧?
二是當他後來出山時,上任的官職竟是一個比建昌縣小了許多的縣令──若說他是放長線釣大魚,那麼他為什麼只是將線放得這麼長,卻並沒等大魚上鉤,而只是在一條更小的魚上鉤時便收線了呢?更何況他是完全有機會等到更大的魚上鉤的。
今天的京劇舞臺上,包拯每於艱難決斷之時,常常將烏紗捧在手上,隨時掛牆而去。在我看來,這實在是編導們為包拯設計的最好的一個官場姿態了,其雖有藝術誇張,但也未必盡是誇張。
據史料記載,皇祐三年(一○五一年)六到十一月不足半年的時間裡,包拯曾連續七次向皇帝遞上辭呈,要求辭職。儘管最終皇帝並沒有同意他的辭職請求,讓人們不禁猜測這是他為了堵住仁宗皇帝的嘴,是他一種以退為進的手段,但是這樣的高頻率的辭職畢竟是古往今來的官場歷史上所罕見的。我想,如果皇帝真的批准他的請求,他一定會義無反顧地掛冠回鄉的。 這更印證了我前面對他的猜測,即包拯為自己設計的官場姿態是:你讓我當這官,我就這樣當;你若不讓,我立馬走人,絕不留戀!不就是一頂烏紗嗎?還給你就是了!而這一切又正應了一句話:「無欲則剛。」
這或許就是包拯敢於將唾沫星濺得皇帝一臉的原因!
正史上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嘉祐三年(一○五八年),包拯向仁宗建議應該立太子。沒想到仁宗竟然反問包拯道:「那你看立哪位皇子為太子好呢?」包拯立即敏感地回答說:「陛下,您一定是對我有什麼猜疑了吧?立太子這樣的事情,是國家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議;至於立哪一個,這是皇帝自己的事情,怎麼能問臣下呢?」僅從這一件事情我們就不難看出,此時的包拯雖已晚年,但頭腦仍是非常清醒的。在這一事件中,仁宗一方,他最初在聽到包拯的建議後,似乎只是不經意間的順水推舟似的一個反問,但是仁宗一定心想,包拯准會順著自己的話回答的,這便既可以套出包拯與哪個皇子關係密切,又可檢驗一下包拯是否有私心;然而包拯並沒順著仁宗的問題問答,這表面上看來好像是頂撞了仁宗,讓仁宗沒有得到他表面上想要的答案,但是仁宗一定不會有任何的不悅,相反,還會對包拯更加的信任和器重,因為他知道了包拯是那麼的坦誠和無私。而這對於包拯來說,無疑是為自己作了一次化險為夷,因為在封建社會,像立太子這樣的事情,總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危險的事情,稍不留神便是腦袋搬家血流成河。這樣的事情,若是有一絲一毫的參與進去,都無異於自己找死。包拯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是管天管地管得寬,但實際上他始終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什麼事該管,什麼事不該管,一切都非常「拎得清」。而這一點也是仁宗皇帝能容忍包拯的前提。
即使是在這一前提下,包拯也從來不莽撞行事,他在向對手發動進攻的同時也很懂得保護自己。
首先是,沒有充分的證據和必勝的把握,決不輕易出手攻擊對手。
其次,包拯向敵手發起攻擊,往往是一旦出手,便不獲勝利決不收兵。儘管包拯對張堯佐的彈劾可謂是有理有據,但是因為有張貴妃在仁宗那兒的枕邊風的力量,張堯佐不但不倒,還反而不斷升遷。面對這樣的局面,包拯百折不撓,一不做二不休,一連上摺七次,最後又通過與仁宗展開「廷辯」,將唾沫賤得仁宗一臉,才終於將其拉下了馬。如此表現出的執著精神可謂感天動地。
然而,儘管如此,並不是說包公就是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人,事實上他也很懂得變通,很懂得給對方臺階,很善解人意。總之,很講究工作手段和方法。還是在對張堯佐彈劾一事上,包拯的指責是嚴厲而無情的,甚至這種無情不但是對張堯佐,甚至在對張貴妃和仁宗也一樣,但是在關鍵時刻他又很善於設身處地為仁宗考慮,從實際出發尋到多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一個不行,兩個;兩個不行,三個……總之給仁宗留足了迴旋的餘地和下臺的臺階。如對張堯佐的彈劾結果是,仁宗罷了張的三司使,但同時調任宣徽使。
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包拯在對貪官污吏決不留情的同時,他對自己要求極嚴。就在他從發病到去世的這最後一三天時間裡,他留下的唯一遺囑是: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立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這也註定了包拯是個孤獨的人。
包拯是北宋政壇上的一個獨行俠!
【內文摘錄之三】
﹝獨守千秋 王安石﹞
那年秋天,王安石回到了自己闊別七年的「半山園」。那些日子裡,紫金山下的百姓,常常看到一個「布衣杖履」的老者在山林地頭徘徊。
離「半山園」不到一箭之地有一個不大的土墩,王安石很喜歡去那裡遊憩。
王安石一路走一路想,此次自己雖然辭去了相職,但在他的推薦下,一向支持變法被朝野上下稱為「護法善神」的呂惠卿已接任了自己的參知政事一職,變法大業也算是後繼有人了;而那些新法的反對派人物,多數已被神宗貶出了京城,新法的推行實際上已沒有太大的阻力了;雖然宋神宗廢除了新法中的一些條款,但主體還在施行;因此,王安石此次罷相南歸,並沒有太多的悲傷和憂慮,甚至他還想到,說不定哪一天自己還會東山再起,回來重掌相印!
然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宋神宗必須一如既往地支持新法這一前提之上。而神宗能這樣嗎?想到這裡,他心中又難免一陣失落。
其實,神宗的反覆與動搖幾乎是與變法的全過程相始終的。從熙寧二年(一○六九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正式實行變法開始,到熙寧七年(一○七四年)王安石罷相回江寧,王安石就已曾先後六次辭職:第一次是變法的當年,因呂誨上疏指責王安石所謂「十大罪狀」,王安石憤而辭職。 這一次因神宗對王安石非常信任,所以並沒聽呂誨之言,結果自然是以呂誨受黜王安石留職而終。但後面幾次則有所不同了,第二次是熙寧三年。第三次是熙寧四年五月,因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在一些別有用心的官員的唆使和慫恿下,聚眾包圍開封府,並闖入王安石家鬧事;第四次和第五次都發生在熙寧五年。第六次發生在熙寧六年正月,因宣德門侍衛仗勢阻攔王安石專車入內且撾傷他的馬。這幾次實際上都是有人利用了神宗的猶豫與動搖向王安石發難,王安石不得不以辭職來抗爭。雖然最終神宗都沒准王安石的辭職,王安石看上去都勝利了,但是神宗所表現出的猶豫和動搖王安石都是看在眼裡、清清楚楚的。
然而,他對神宗有再多的抱怨和天大的不滿,又怎麼能明說啊!好在中國古代詩歌中常常有借香草美人來喻指君臣,這讓他也可以借別人的酒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但也僅僅只是如此而已,不要說自己現在已身在江寧,就是還執掌著相印,也不能不把實施新法的最大希望還是寄託在宋神宗身上啊!
冬去春來,似乎不知不覺間一年便過去了,身處半山園的王安石,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來自京城的任何消息和動靜,隨著夏天的來臨,眼望著百草豐茂的鐘山,感受著大自然呈現出的一派生機,王安石在心中似乎也隱隱地萌生出了一種莫名的希望。
果然,宋神宗再次召王安石進京,並再次以相印委他。
王安石以最快的速度進京了。
在進京途中,王安石或許會想,自己這次能重掌相印,或許是因為宋神宗真的是下定決心要將變法進行到底了,或許是呂惠卿沒有忘了他的舉薦之恩,說動了神宗,或許是這朝堂之上真的還離不開自己,或許是……他萬萬想不到,事實上一切並不是這樣!
王安石罷相後,呂惠卿在王安石的力舉下出任參知政事,成了變法的接班人,此時新法推行也已有幾年了,成果也開始有所顯現,但是呂惠卿自己心裡明白,變法的領導人是王安石,所以當後來宋神宗在王安石罷相後又不時表示出對他的懷念時,呂惠卿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他怕宋神宗再度起用王安石──那樣的話,他將不但失去已坐上的參知政事的位置,而且變法一旦成功,最大的功勞也不再屬於自己。所以他要設法阻止王安石東山再起,甚至不惜將其置之於死地。正在此時,呂惠卿接到了一個皇室宗親叛亂的案子,而這個案子牽涉到王安石的一個早年的朋友──道士李士甯。呂惠卿便借此機會向王安石下手了。
或許是宋神宗看在眼裡,或許他不能相信或不願相信自己看重的新執政的宰相竟是這樣一個恩將仇報的小人,於是試探著問呂惠卿道:「李士寧案如何?」
呂惠卿回答:「如係叛國大罪,臣自當依法論斷。」
神宗又問:「安石如何?」
呂惠卿冷冷地說:「臣知,安石最為重法!」
神宗默然不語。
然而不久,宋神宗召王安石回朝,並復其相位。此時,我們再來看神宗的默然不語,此中的深味不難想像:他一定在心中想,你呂惠卿作為與王安石一起變法的戰友,明知道王安石在此案中並無瓜葛,卻不講一點義氣,不但不替王安石開脫,反而一副秉公執法、大義滅親的架勢。神宗的默然中有著太多對這位新任宰相的深深失望──正是因為對呂惠卿的失望,才讓神宗又想起了王安石。
王安石對這一切並不知道,也就是說,他對於「變法派」內部已出現的嚴重分化一點也不知道,對於自己此番進京不但將要面對「反對派」的明槍還要面對「變法派」內部的暗箭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並不知道。
果然,呂惠卿僅放出了一支暗箭,便將王安石再次置於死地。
有一天,呂惠卿將王安石曾經給他的一封私人信件拿給神宗看,因為其中王安石黑紙白字寫著「無使上知」四個字──這不是天大的欺君之罪嗎?
就這樣,王安石復相後僅僅半年,便冒著紛飛的大雪再次回到了江寧,回到了他的「半山園」。雖然神宗也給了他一個「判江寧」的官職,但他並沒去過府衙,而是將自己徹底地交給了這曾經養育過他的一方山水......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錦灰堆裡的尷尬人物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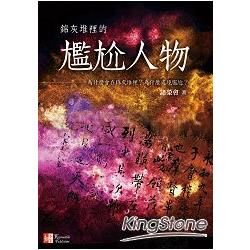 |
錦灰堆裡的尷尬人物 作者:諸榮會 出版社: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4-05-1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32頁 / 25k正 / 14.8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0 |
小說/文學 |
$ 200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錦灰堆裡的尷尬人物
「錦灰堆」始於元代,今已失傳,是一種高難度的藝術創作,懂得這種創作者需多才多藝,要能寫:善寫真、草、隸、篆還要能模仿各家字體;要能繪:山水人物、花鳥魚蟲;並要有藝術底蘊:熟知各種拓碑、青銅器造型、篆刻各種印章...等絕活。
本書以「錦灰堆」借喻古代名人雅士、高官、青樓名妓與眾不同、有時彷彿站在針尖上的生活世界。
所謂「尷尬人物」,本每一位主角身分各有不同,但在人世間高低起伏之中,難解、無奈的境地屢有出現,其他書籍的作者可能輕輕一筆帶過、不加著墨,本書作者彷彿俯瞰他們,在他們處於無奈、難解之際,用敏銳的角度、帶讀者一起加入他的「廣角鏡頭」去親身感受箇中滋味,揣摩真相的情境,這樣咀嚼本書,所帶來的閱讀享受是超乎一般的!
作者簡介:
諸榮會
‧1964年生,中國江蘇溧水人。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江蘇省書法家協會會員。
‧現為江蘇教育出版社副編審、新語文學習雜誌社社長兼主編。
‧從教期間發表過教育教學文章四十多萬字、出版教育教學著作數種、近年來發表以散文為主的文學作品百餘萬字。
‧出版散文集《最後的桃花源》、《秋水蒹葭》,系列大散文作品集《風生白下》、《風景舊曾諳》等多種,多次獲得報刊徵文獎和文學獎。
‧多篇作品被轉載和被選入各種選本、讀本和課本。
章節試閱
【內文摘錄之一】
﹝台城悲歌 粱武帝﹞
世稱的六朝──英雄與小人同朝共舞的政治的六朝,征伐與殺戮難分難解的軍事的六朝,雕龍與畫蟲平行並重的藝術的六朝……每當想起,那一幕幕早已褪色的史劇常常會浮現在眼前,如夢幻煙雲、流水落花,其主角們或衣冠飄忽、放浪形骸,或酗酒吃藥、醉生夢死,他們崛起又毀滅、大喜又大悲、殺人又被殺的人生和命運,常常讓人感慨繫之,而其中尤以那位史稱梁武帝的蕭衍最令人欷歔難禁。
這並非因為他的文武全才,也並非他在六朝列代皇帝中活得最長(八十六歲),在位最久(四十八年),更...
﹝台城悲歌 粱武帝﹞
世稱的六朝──英雄與小人同朝共舞的政治的六朝,征伐與殺戮難分難解的軍事的六朝,雕龍與畫蟲平行並重的藝術的六朝……每當想起,那一幕幕早已褪色的史劇常常會浮現在眼前,如夢幻煙雲、流水落花,其主角們或衣冠飄忽、放浪形骸,或酗酒吃藥、醉生夢死,他們崛起又毀滅、大喜又大悲、殺人又被殺的人生和命運,常常讓人感慨繫之,而其中尤以那位史稱梁武帝的蕭衍最令人欷歔難禁。
這並非因為他的文武全才,也並非他在六朝列代皇帝中活得最長(八十六歲),在位最久(四十八年),更...
»看全部
目錄
004 序 尷尬人物
011 壹 伍子胥──悖論人生
032 貳 商 鞅──作法自斃
048 參 梁武帝──台城悲歌
066 肆 薛 濤──九眼橋邊女校書
082 伍 包 拯──一死即永生
109 陸 王安石──獨守千秋
138 柒 趙孟頫──成全的是藝術
163 捌 鄭 和──海上帝王
189 玖 秦淮八艷──就那點事兒
011 壹 伍子胥──悖論人生
032 貳 商 鞅──作法自斃
048 參 梁武帝──台城悲歌
066 肆 薛 濤──九眼橋邊女校書
082 伍 包 拯──一死即永生
109 陸 王安石──獨守千秋
138 柒 趙孟頫──成全的是藝術
163 捌 鄭 和──海上帝王
189 玖 秦淮八艷──就那點事兒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諸榮會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4-05-14 ISBN/ISSN:978986622353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