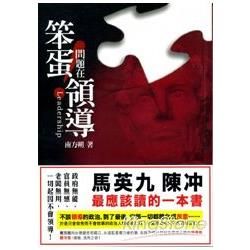小職員、大主管、最高領導者都該看此書,南方朔抽絲剝繭、一針見血的為我們揭密,原來你我身邊發生過的大小事件與熱門話題,起因都是「人」!只要從這些事例中學習「待人」和「帶人」,就是「好領導」!因為──世上沒有笨蛋,只有會不會領導。
領導是一種藝術、一門哲學、一帖補藥……
《笨蛋!問題在領導》,為你提供二十一世紀各領域領導必備的「教戰守策」!
★你是組織中的「獅、狐、鴿、蛇」性格?如何心服、如何口服?全球化是弊、是利?領導的包羅萬象、百家論點,南方朔一次剖析、去蕪存菁。
★有時需強硬、正直不可缺、高壓與放任、適時的運用手腕……服了「領導」這帖藥,想不陷入都難。不論古今中外,如何活用高明與高尚的領導,為必修之課題。
★上班族該如何優雅地進入權力的核心?專案負責人要怎麼令老闆、部屬和客戶信服?企業組織追求成就,需要怎樣的CEO領航?南方朔以古鑑今,不談深奧理論、直搗問題核心,詳舉古今中外實戰實例,告訴我們領導,只有合不合時宜與有沒有效。
柯林頓一句 "IT'S ECONOMY, STUPID" (笨蛋,問題在經濟)成為他順利入主白宮的經典名言;但是,台灣的歷任總統,卻讓「領導」成為國運興衰的最大關鍵數。南方朔做為台灣「民間最用功的學者」,「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目睹世上成功的領導者與台灣三任總統作為,以及二十多年台灣特有的怪現象、寶島藍與綠。分析成功的領導,如何化繁為簡,單一、有用,建設性地指陳新世紀最精進的「領導之道」(leadership)
當領導都不「領導」,再好的管理也沒用!
團體或組織,不論大小,要營運、要前進,領導與管理是致勝關鍵!領導重決策,管理重執行,領導者就像船長,管理者就像大副,管理學洋洋灑灑,但領導力該從何學起?
本書從國家領導人的高度來談「領導」,「民間最用功的學者」南方朔,藉由古往今來的生動事例,並援引古今中外「正典範」與「負典範」的帝君領袖,以及東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哲學等思潮、著作,來剖析好領導的本質與力度,並洞徹壞領導的無能詭計。不論你身處在團體組織的哪個位置,懂得領導就能直指問題的核心,帶領個人與團體朝「更好的未來」前進!
雨果藉著他的文學,告訴每一個人都有成為更好自己的可能;
南方朔藉著他的筆,告訴每一個人走向更好人生的領導之道。
作者簡介:
南方朔
本名王杏慶,一九四六年生,台大森林系、森林研究所畢業,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博士結業。早期是黨外雜誌的健筆,並親身參與抗爭運動,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專欄組主任、副總編輯、主筆等職,以及《新新聞》總主筆。
南方朔先生著作等身,早期著有《憤怒之愛》、《另一種英雄》、《文化啟示錄》和《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等,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的演變和思潮的介紹;近來以「語言」為範疇,陸續出版《語言是我們的居所》等系列書籍五本;近年再以「嗜詩」人的身分,出版了《詩戀記》、《回到詩》,呈現閱讀與寫作的光和熱。
除了這些身分和著述,南方朔更是一位專業的讀書人、具洞見的觀察者,大量閱讀並長期觀察台灣及全球發展,總以古往今來的帝王人物、東西思潮的理論著述,寫下領導的本質、高度及視野,領導的位置或許不同,「領導之道」卻是放諸四海皆通的。
著作
《另一種英雄──反體制的思想與人物》,1987
《捉狂下的興嘆》, 1991
《憤怒之愛: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 1991
《“反”的政治社會學》,1991
《文化啟示錄-三民叢刊61》,1993
《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1994
《李登輝時代的批判》,1994
《敬告中華民國──給跨世界台灣良心的靜言》,1995
《如何作一個積極的公民》,1995
《語言是我們的居所》,1998
《世界末抒情》,1998
《經濟是權力,也是文學》,1999
《語言是我們的星圖》,1999
《有光的所在》,2000
《語言是我們的海洋》,2000
《除魔與昇華》,2001
《在語言的天空下》,2001
《給自己一首詩》,2001
《語言是我們的希望》,2002
《詩戀記》,2003
《魔幻之眼》,2003
《白遼士浮士德的天譴》,2003
《語言之鑰》,2004
《靈犀之眼:閱讀大師2》,2004
《感性之門》,2004
《回到詩》,2005
《新野蠻時代》,2006
章節試閱
輯一 領導力
領導的守則
在戰爭史或政治史上,當一個統治者接二連三的犯下領導錯誤,到了某個臨界的不歸點,他無論說甚麼和做甚麼,都再也不會讓人相信,這種情況就是最深沉的「信任危機」。
台灣的局面搞到日益不堪,最近重讀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舊作,讀到他寫的〈總統的六條守則〉不禁油然生感。彼得.杜拉克所謂的六條是:
守則一,「需要做什麼?」是總統首先要問的問題,他不能頑固而自以為是想要做的事,這涉及審度時勢的本領。
守則二,「集中力量做必須做的事。」需要做的事有很多,然而身為總統,只能為自己負責的去冒險,排除異議,把力量集中在一件事上,否則必將一事無成。這條守則的意思是,總統永遠不可能站在穩贏不輸的位置上,他必須做重大的決定,而後調度資源加以貫徹並為此負責,這就是勇氣、判斷與擔當。
守則三,「別把賭注押在自以為已有把握的事上。」自以為有把握的事,可能一時有效,但這種爛飯吃多了反而會有反效果。以台灣為例,「清廉」或許過去有效,而現在呢?它早已被「無能」所取代,「清廉」再天天上口,已成了不可笑的笑話!
守則四,「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從不進行微觀管理。」當領導人的,最重要的是管大事,最忌諱的是大事無方向,小事卻比科員還在行。彼得.杜拉克因而說道:「對一個總統來說,沒有比事必躬親,更容易使他喪失信用的了。」領導人喜管小事,會侵占管大事定方向的腦力與時間,也會挫折掉公務員士氣。尤其嚴重的是,若領導人意圖用只管小事來閃避應管大事的責任,則整個國家就注定無方向亂轉,今天台灣政府混亂不堪,上無方向,中無團隊,下則士氣低沉,這是誰的責任?
守則五,「一個總統在政府裡沒有朋友。」這也是林肯的至理名言,它的意思是當總統的當然也要朋友,也有親信,但好的總統就應像小羅斯福一樣,他絕不把朋友親信放在他的政府內,其理由就是避免小圈圈化和以私害公。政府是個所有的參與者努力奉公的地方,不是個搞小圈圈,封官犒賞,共享榮華富貴的地方。
守則六,就是當年杜魯門送給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忠言:「你一旦當選總統,就要停止競選。」意思是說:身為總統,就應為國為民做事,心中不能總是在選票在連任問題打轉。當心中無選票無連任的自私念頭,它始能心無罣礙去做應做的事,連任只是回報,不可能是目的!
國民黨已不能繼續以「大環境不佳」這種很沒誠意的理由,也不可能靠做秀來改變頹勢,只有深思熟慮,毅然決然的全面改組改造,看看能不能有所扭轉。而第一步,乃是從「不再想連任處,重新出發」!
輯二 經濟力
消除金融文盲
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要避免我們的下一代像從前的文盲一樣被人剝削欺侮,如何普及「金融教育」降低「金融文盲」(Financial Illiteracy);讓人民對攸關自己權益至鉅的金融政策及商品有更大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也需要在「金融賦權」(Financial Empowerment)上更加努力。
「金融教育」、「金融文盲」、「金融賦權」這些觀念都不是很新,但最近突然躍升為主流的新認知,當然是拜金融海嘯之賜。在過去,由於人們的金融知識不足,因而對專業的金融管理官員及從業者,遂產生奇特的敬畏、羨慕和信任。殊不知整個金融領域,就在人們普遍都是「金融文盲」因而盲信的時代氣氛下,逐步惡化,終於製造出全人類都嚴重受害的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它顯示出:
一、當人們「金融識字程度」(Financial Literacy)不足,無法分辨金融政策的良窳,金融官員就會日益無能,金融機構也就愈會推出金融瑕疵,形同詐欺的金融商品。美國的次級房貸衍生性金融惡質商品的氾濫,信用評等機構淪為共犯成員,金融監理官員的尸位素餐,其共通的前提即是「金融文盲」的可以欺騙和易於欺騙!
二、根據近年來的研究,已發現金融與每個人的生活雖愈來愈密切,但當代「金融文盲」的程度卻嚴重到駭人聽聞。美國十個持卡人有四個不知道卡息的多少及循環利率的可怕;劍橋大學做過研究,發現有九百萬英國人是徹底的「金融文盲」。近年來率先提出「中美國」(Chimerica)這種說法而大紅特紅的哈佛教授佛格森(Niall Ferg uson)則指出,金融知識匱乏不限於一般大眾,他在哈佛MBA班的學員有許多居然不知道名目利率和實質利率有什麼不同。他認為像英美這種高度金融化的社會,國民的金融程度卻極度低水準,將來他們又怎麼能保障自己的權益和監督政府呢?
提升國民的金融程度,不要繼續做「金融文盲」,從上世紀初即有人在做著先驅工作。舉例而言,《窮爸爸.富爸爸》這本暢銷書共同作者之一的許瓦布(Charles Schwab)從一九一九年起就開始教兒童有關金錢方面的知識;美國金融圈名人,曾做過「美國聯邦金融識字程度委員會」副主委的布萊安(John Bryant)很早就認為金融問題是民權問題,因而在一九九○年代即於洛杉磯貧民窟教窮人金融和儲蓄理財;印度社會工作領袖比莉摩瑞姬(Jeroo Billimoria)也早在印度貧民社區教六至十四歲的兒童金錢知識。這些先驅人物所做的先驅試驗,近年來已獲普遍回響,據了解美國已有三州將金融教育納入教育課程,有十五州準備納入,美國聯邦政府準備像搞「和平工作團」一樣推動「金融識字工作團」;英、俄早已決定強化金融教育,一個全球性的兒童金融教育計畫目前已在三十多個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展開。如何像在古代提高識字率,降低文盲一樣,在二十一世紀提高金融識字率,降低金融文盲,已成了許多國家的新目標。
但有一點必須釐清的,乃是強化金融教育,絕不能與窄化的投資理財並論。目前的確有些國家以金融教育為名,但卻以教導人們如何炒股賺錢為實,但目前有關投資理財,由於它長期被扭曲,經常已和投機相連,金融教育要教的不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知識,而是要教導人們對個人金融理財要有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也要有判斷力。近年來,耶魯大學金融教授許勒(Robert J. Shiller)的許多觀點日益受到重視,他的觀點之一就是「金融民主」。只有一般人金融判斷力增強,整個金融服務領域才會進步,金融風險才會降低。金融教育、金融判斷力、金融賦權、金融民主、金融共同福祉,這些才是一脈相連的目標。
許勒教授早已指出,由於近代訊息管理科技的進步,如果妥善運用,金融福祉早就有極大進展。但因金融民主和金融賦權不夠,整個金融秩序反而成了投機詐欺及無能更甚、風險更高的領域。金融教育之目的,不只是教人賺錢理財,而是要教人更大的民主與福祉。
輯三 安治力
修辭莫若修心
台灣近年來,上自部長、政要,中至官吏民代,種種說話不當甚至粗口惡言人事,多得一籮筐。當今政治人物頻頻凸槌或粗口惡言,暴露出他們的麻木不仁,他們並不愛台灣,他們在嘴巴壞了之前,心就已經壞了。
如果只是禁口或開始講究修辭,那麼壞了的心加上漂亮的語言包裝,它豈不就會像古代修辭演講祖師西塞羅(Marcus T. Cicero, 106-44BC)所說的,只是「鄉愿」與「奸巧」(Canning)嗎?西塞羅在所寫的《論責任》一書裡指出,參與政府乃是一種榮譽的志業,必須心誠意正,否則「利用別人的善意不察而獲得信任所帶來的利益,豈不傷到正義的原則?在世界上,沒有一種詛咒甚於戴上面具的奸巧了」。
因此對於種種凸槌與惡言,禁口及修辭是沒有意義的,修辭莫若修心。修心是將心比心,知道百姓的艱難與愁苦;修心也是恢復自己做為人而非官的身份,因而多生智慧。真正的修辭不是從口出發,而是從心開始。西塞羅在寫給兒子的書裡就說道:我那雄辯及修辭美好的演講集固然該讀,而我談人生,談道德的哲學集才更該讀,哲學與道德是心,說出來的話只是表,心大過言語。
在此特別提到古人西塞羅,因西塞羅乃西方世界最專業而傑出的修辭雄辯演說家,可說是這個領域的祖師級人物。他從青年期即開始鑽研修辭雄辯學,並成就一家之言,此外他也身體力行,因而成了古羅馬最著名的演說家。但他到了後期,眼看整個帝國修辭雄辯日益發達,但心的修養卻愈來愈差,欺騙與詐偽盛行,當語言已淪為替權力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用來彼此溝通及推行正道的載體,他遂對修辭雄辯學展開批判與重新定義。他說道:「如果人們荒廢了學習哲學與增加道德修養這種最高尚、最榮譽的事業,而將全副精神都用於演說修辭,那麼他的公共生活就會變成對自己無用,但對國家則是有害的東西。」
西塞羅在他的《修辭雄辯三書》這部對話集裡,有許多重新定義修辭雄辯的重要段落,在此姑且引用〈第一書〉裡的兩段:
「對我而言,沒有一件事比藉著修辭雄辯的力量,而將散亂的人群凝聚起來更重要了。靠著修辭雄辯的力量,可以召喚並贏得人們的善意,可以引導人們的願望。在每個自由國家或所有的社區,亦可藉此達到和平安寧的境界。有甚麼事情比受到尊敬的談話,以及被智慧的反省及尊貴的語言所打磨過,並因而促進相互了解更讓人高興呢?有甚麼成就會超過人們靠著修辭而讓群眾的活力,法官的良知,官吏的操守等意識被喚醒更榮耀呢?」
「雄辯修辭的更高貢獻多得不可勝數。有甚麼力量像它一樣,能夠凝聚散亂而差異的人群?有甚麼力量能帶領人遠離粗暴,達到現在公民這種文明的條件及建造出社群?因此,我的年輕朋友們,多多努力走向正道的修辭,讓你自己成為服務人群的一道清泉,也成為共和國裡一個值得尊敬的成員!」
在此不厭其煩的引述西塞羅,原因即在於他是西方世界最早即有系統的將不當的語言不但會誤人誤己,也會誤社會和誤國的道理說清楚的第一人。因此他才指出,修辭必先修心,他也主張任何依靠語言來活動的人物,都必須先具備人文教育的素養和追求榮譽的心靈。這個紀元前的人物,他的忠告在兩千多年後的現在,似乎更有效!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己愈來愈口業深重,許多當官的則習性傲慢而不自覺,因而總是不斷凸槌,這是「無心之禍」嗎?恰恰不是,因為他們正是最重要的心已出了問題。他們不是「不小心」的「無心」,而是「不用心」、「不安好心」的「無心」!
文明需要語言,語言就必然要講究修辭來提高附加價值。但歸根究柢,最重要的畢竟還是修心啊!
輯四 安治力
八卦經濟
日本人氣明星酒井法子失蹤及吸安的新聞曾經鬧得一陣子沸沸揚揚,但這段負面新聞有損於她的人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最近有三本她寫的以及別人寫她的書,都高踞日本排行榜的前面而爆賣,日本人把這個現象稱為「醜聞經濟」。
把酒井法子現象稱為「醜聞經濟」,這實在有點太超過,說它是「八卦經濟」或許倒更加吻合。現在的人只要不是失業或窮到家無隔宿糧,總是有不多的閒錢與太多的時間,這已使得倦怠無聊成了現代人最大的負擔,甚至是一種精神性的病痛,而八卦就是填補這種無聊的最佳妙藥。在這個消費的時代,最終極的消費就是消費無聊,於是「你的無聊是我的鈔票」這種八卦經濟遂告形成。我們可以試想一下:
現代人平時相互疏離,共同的話題都找不到幾個。太嚴肅的話題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門檻,有誰願意把自己搞得太過勞累;而每個人自己私人的苦樂又太過機密,只能和極少密友分享,這時候那種不必知識門檻的八卦,遂成了無聊但似乎有必要的交流最好的題材。
貧乏的現代人,八卦已成了同輩認同的記號與儀式。我們喜歡同樣的八卦,表示我們是同一國的;如果有某個正夯的八卦正在流傳,我進了辦公室,聽別人嘰嘰咕咕在談而自己矇然無知,插不上嘴,就會覺得跟不上潮流,被別人排斥在外。有了這種被孤立的感覺,回家的路上一定把有關酒井法子的八卦書報全都買遍,回家惡補,明天到辦公室就可以赫然變成酒井法子的八卦權威。
因此,八卦新聞是有用的,它是無聊時代的認同記號與儀式,而有了需求當然就會有供給,一個八卦經濟的市場遂告形成。而若我們再追究多一點,就當會發現到,這種八卦文化和八卦經濟,它的背後其實是更重要的「出名文化」。古代資源有限,因而出名困難,文人要白首窮經,十年寒窗;武人要提著腦袋上沙場立功;老夫子則要一輩子循規蹈矩,看看老年時能否立德。而到了現代,資源的競爭更嚴峻,無論任何行業要想出頭,已必須搶著立名。
立名的競爭,已讓原本的白色空間變得愈來愈灰,只要不是殺人放火,已無事不可為。鬧一點緋聞,劈幾個腿,露一點乳,吸一點安,拍幾張豔照,打幾場不致於去坐牢的小架,又有何妨?而這就是出名文化演變為八卦文化的過程。八卦文化與羞恥無關,與名聲的好壞無關,它已形成了一種不管好名壞名,只要出名就是好的新標準。出名本身就是一種表演,出了名自然會有人氣,就會上排行榜。酒井法子因為名氣太大,她的八卦醜聞經濟也規模大得多,但若細心觀察,在我們社會裡,這種八卦醜聞經濟不也在蒸蒸日上嗎?
出名文化、八卦文化、醜聞經濟當道,它已儼然成了當今各國內需經濟裡很大的一塊。對於這種現象,我們不太能一本正經像個LKK般的非議。當人類愈來愈無聊,無聊當有趣的八卦文化和醜聞經濟就自然而然會成為它的終點。
人們只能說,「聽,這是個自由社會,這是個自由市場!」將它一語帶過。
而比較值得討論的,乃是在一個八卦的社會,正式的政治文化新聞必須和八卦新聞天天競爭版面和時段,遂使得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也變得每天必須在表演上推陳出新搏版面搶時段。這是政治及文化人物的明星化和表演化。愈會表演的愈有人氣,當政治文化的判斷已脫離了實績,而成為一種表演,一種華而不實,漂亮但卻沒有內容的「風格政治」遂取代了「政績政治」。
當代批判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對歐巴馬做了極其銳利的批評,他檢視歐巴馬的講話,發現都是漂亮的動作,響亮的口號,滑溜的言辭,卻完全沒有具體的政策。因此,名人文化,八卦現象,醜聞經濟,表演政治,其實都是同一棵樹上長出來的東西!
輯一 領導力
領導的守則
在戰爭史或政治史上,當一個統治者接二連三的犯下領導錯誤,到了某個臨界的不歸點,他無論說甚麼和做甚麼,都再也不會讓人相信,這種情況就是最深沉的「信任危機」。
台灣的局面搞到日益不堪,最近重讀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舊作,讀到他寫的〈總統的六條守則〉不禁油然生感。彼得.杜拉克所謂的六條是:
守則一,「需要做什麼?」是總統首先要問的問題,他不能頑固而自以為是想要做的事,這涉及審度時勢的本領。
守則二,「集中力量做必須做的事。」需要做的事有很多,然而身為總統,只能為...
作者序
批判平庸,為台灣呼喚領導力! ☉南方朔
美國期中選舉,由於選民對歐巴馬政府不滿,民主黨因而遭到六十八年來的最嚴重挫敗。
民主黨慘敗之後,《洛杉磯時報》有一篇社論對歐巴馬的領導風格做出了針砭。該社論指出,歐巴馬乃是個「交易式的領袖風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不是「轉型式的領袖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它的意思是說,歐巴馬並不是沒做事,但他做事好像是做生意一樣的精打精算:這個要討好,那個不得罪,例如他推出的健保方案,討到了窮人的歡心,他在健保的執行上,他又向藥商及保險業者等示好放水,用舊式的說法,乃是他的改革非常的機會主義,顯得有點半生不熟的半調子。至於,「轉型式的領袖風格」則不然,這種領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有甚麼方向與目標,在方向的帶動下,他們的改革就會有較強的理想性,而歐巴馬的畏首畏尾,前後不一,其實已暴露出他的政客本質。選舉時,他信心滿滿高唱「改變」口號,好像是個改革政治家,美國選民也期待他是個改革政治家,但這場期中選舉下來,他那種改革政治家的光環已被打掉了。
因此,《洛杉磯時報》說他是「交易式的領袖風格」,而非「轉型式的領袖風格」,這對歐巴馬來說,乃是相當嚴重的指責,他擔不起「轉型」的重責大任。這時,我們已有必要去申論「轉型」這個概念了。
「轉型」這個詞,今天已成了全球在廣泛使用的時代關鍵字。如果我們稍做查考,即可發現這個詞乃是起源於一九八七年。當年「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PSA)在芝加哥舉行年會,在該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該小組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f Fishee)擔任召集人,美國名校許多位有關人文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學者,以及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者,還有電訊民主的專家都是重要成員。在該次會議後,「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開始進入了當代政治思想及實際政治的日程表,「轉型」也因而成了時代性的關鍵字。
根據美國加州聖瑪莉學院政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合著的《轉型政治學:理論、研究及實踐》一書所述,「轉型」這種概念乃是一種社會進化觀的顯露,從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以來,人類社會已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人們的意識改變,已使得女性主義和生態環境主義興起,尤其是資訊科技和傳播媒介的發展,人們的主體認知增強,已使得人際互動更趨複雜,這些都是社會內容的改變,已使得既有的社會及政治文法應接不暇。就知識理論而言,這意謂著人類社會已到了「舊典範」(Old Paradigm)難以為繼,而「新典範」(New Paradigm)開始登場的時候了。
美國學者用「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觀念,設定出「轉型」這種說法,在近當代政治學上乃是一個重大的觀念革命。因為「轉型」這種觀念乃是一種具有主體認知,有目標性和方向感的思惟方式,一個社會的型要往那邊去轉,這乃是一個社會重大的方向性決定,對該社會的領導階層乃是個至關重要的課題,這意謂著他們必須要有目的性的願景,而且還要有針對該願景去做出整體規劃的能力,而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可謂斷層已久。
近代西方,甚至全世界,由於都出現過許多政治狂人和災難,因而戰後的美國政治學遂開始不談領導的問題,只談民主,而且將民主絕對化,以為民主就可解決一切的領導問題。這種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的政治學,到了最後,它將一切都簡化成了民意。這種趨勢使得政治領袖們愈來愈不領導,任何人如果去談領導,很容易就被扣上是在鼓吹「強人人治」的帽子。
其實,早在民主政治發展之初,西方的理論家裡就已有人指出,民主誠可貴,但領導亦絕對不可廢,否則民主就只全讓「平庸」(Mediocrity)當道,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家裡,著名建築工程師克蘭穆(R. A. Cram, 1863-1916)即指出民主選舉當缺乏了有品質的領導,最後就會招致「平庸的報應」(The Nemesis of Mediocrity)。二十世紀這些民主理論家的觀點當然不一定對,但戰後政治學的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受到重要學者龐斯(Tames M. Burns)的注意,他發現到美國自從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之後,就再也沒有偉大的領袖型人物。他所謂的偉大,並不一定是要有甚麼豐功偉業,而是要替國家創造出新的可持續努力及分享的願景,他在一九七八年所著的《領導》一書裡,首次把「偉大」這個價值放進了政治領導人物的品質要求中。
戰後的政治學只談民主而不領導,除了政治學家本身有心理障礙,恐懼說領導會被誤認為是在鼓吹人治之外,這其實也和戰後的民意政治及媒體發展有關。戰後的社會發展加速,代表不同利益主張的民意日益蓬勃,特別是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社會的多元化加速,搞政治的人物顧得了這派民意就會得罪另一派民意,為了安全,遂養成一種「迴避」(Avoiding)的習性,那就是在各種民意眾訟來定時,就迴避掉問題,只有等到糾纏的民意自己理出了頭緒,才去做出選擇。在理論上這被稱為「社會過多元時的停滯不進」(Stagnation of Hyper-Pluralism),聰明的政客則是每天看著民意辦事,前總統柯林頓即是按民意辦事的翹楚,美國當代主要政論家喬‧克萊恩(Joe Kleine)即評論曰:「 一個領導人只是跟著變動不居的民意辦事,這種是誰都會做,我們還要你做甚麼?」
政治人物畏懼和討好民意的現象,喬治柏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則指出,一個成功的政客必須和通俗文化做觀眾注意力的競爭,因此他們主要的工作,乃是討好選民,讓他們感覺良好。於是只會做秀而不會做事的政治人物遂告出現,柯文教授甚至指出,在一個媒體緊密審視的社會,只會使得政治人物更加不誠實,他們只會討好公眾的胃口,以防止被罵。這種政治人物開始時胃了贏得選舉還會去冒著風險做出改革者的樣子,但當選後為了保住位子,就只求安全而去討好選民,已不可能去提出自己的願景。政治的大平庸遂告出現。
近當代政治學由於只談民主,不談領導,它造成了政治學的平庸化,而政治學的平庸化即現實政治平庸化的基礎,政治人物不再努力的殫精竭慮帶領國家創造新方向新共識,當時代的新問題出現,他們也無法去面對,如果我們回溯近代重大的方向性問題,如污染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它們都是社區人民發動激烈的抵抗運動所致,而這些運動初起時政府體制都強力的加以打壓。這即是政治人物領導性喪失的證明。也正因為政治學已不談領導,所以近代的領導學遂由政治學這個領域被割讓出來給了企管學,到了現在,企管中的領導學已逐漸由企業領導升高到談政治的領導。
由近代政治學及實際政治中在領導問題上的棄權和墜落,我們已可注意到近代政治領袖人物的平庸化與墮落,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政治學家不對政治領袖的領導功能做要求,政治人物在這個媒體時代,當然犯不著去扮演可能得罪人的領導角色,寧願像個明星式的天王去做秀,討得民眾的掌聲與歡心。歐巴馬這個失敗的例子,它那種「交易式的領袖關係」,已顯露出他其實不過是個擅於媒體操作,會讓自己在人民掌聲中竄起的人物,但在實質上它對美國社會卻缺乏了願景,因而這邊要討好那邊也要討好,向個精打細算的小生意人,最後終於難免「從那裡竄起來,也在那裡摔下去」的命運。
也正因此,「轉型」這個概念的出現,對政治學、實務政治或領導學,可以說是具有重大的意義。一個社會要往那個方向轉,在轉型的過程中有甚麼新價值和新制度要建立,這乃是領袖人物不可辭卻的職責,「轉型」這個字,它的真實意義乃是要恢復政治領袖級人物早已忘記掉的領導職能啊!
根據以上所述,已可看出和社會都需要有能力有擔當的領導人物,在民主社會尤其如此。由近年來全球的變化,人們已看到太多平庸型的領導人物,他們缺乏遠見和能力,可以一時之間利用歷史所給予的機會而竄上舞台,但因為缺乏願景與能力,最後終於錯失了這樣的機會,因而耽擱掉了整個歷史的轉型進程,而台灣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過去二十年,乃是台灣由威權過渡到自由民主的階段,就社會及政治發展的角度而言,這是個大轉型,要在轉型中超越過去的惡習和創傷不平,要在轉型中打造社會的新共識與新願景,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轉型中建造出良好的民主法治文化,在這樣的過程中,社會雖然有自己的任務要完成,但最關鍵的角色無疑的仍在於政治領導人物的身上。
台灣過去二十年,乃是民主轉型的混亂二十年。第一波登場的領導危機乃是李登輝時代的整個領導群亂局。眾所週知國民黨乃是個高度封建性的政黨,封建性的人際關係和權力關係建構出,國民黨權力上層的省籍矛盾,台灣的一般人由於生活領域的相同,早已沒有了省籍矛盾的因素,但搞政治的人卻都不得不承認,它乃是國民黨上層政治的主軸。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國民黨上層不斷分裂鬥爭,宛如古代宮廷鬥爭的現代版。當一群舊特權勢力集團,感覺到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而挾帶著群眾來掩護他們的失去權力的恐懼,這種由上層所發動的權力鬥爭,對一個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發展遺害最大也最久,國民黨舊勢力的這種鬥爭,由新黨而親民黨,再到連宋鬥,一直延續到後來的馬王鬥,它成了台灣政治轉型失敗的主線。當整個當權的國民黨上層都耽於權鬥,政治轉型的有效領導又怎麼可能?
及至陳水扁主政,除了朝小野大的惡性鬥爭持續之外,陳水扁又再把過去那種被迫害妄想擴大,另一種的愛台灣民粹主義又被煽起,甚至成了貪腐有理,台灣政治轉型再次成為不可能。
而到了二○○八年國民黨再次政黨輪替上台,這個政府擅長媒體操作,但卻缺乏足夠的治理能力:「八八水災」即充分暴露出那個政府在當為之時而不為的平庸無能,而它在財經問題上又只會一逕偏向於資方,惡化了台灣貧富差距,而胡亂搞的許多花大錢做秀,實惡化了台灣的財政,迄至目前,台灣的國債已達台幣五兆,而隱藏性負債則達十三‧三兆,這是何其可怕的情況。除了治理能力堪疑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這個政府已執政兩年半,但縱使到了今日,它還是動輒將問題推給前朝。這樣的風格又怎麼可能使人民對它有信心呢?
因此,台灣在過去二十年裡轉型轉得七七八八,歸根究柢,權力上層顯然要負擔很大的責任。這也是近來我的寫作主題之一,我深信政治評論者必須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只有站在這種位置上,對當權者進行評論,才可發揮監督警惕的作用,批評的功能等於是在為台灣呼喚領導力!我深信政治人物的天職,就是要對一個社會有願景,願景乃是一個社會共同福祉之所繫,政治人物如果怯於負責和領導,他是不夠資格坐在位子上的。
批判平庸,為台灣呼喚領導力! ☉南方朔
美國期中選舉,由於選民對歐巴馬政府不滿,民主黨因而遭到六十八年來的最嚴重挫敗。
民主黨慘敗之後,《洛杉磯時報》有一篇社論對歐巴馬的領導風格做出了針砭。該社論指出,歐巴馬乃是個「交易式的領袖風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不是「轉型式的領袖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它的意思是說,歐巴馬並不是沒做事,但他做事好像是做生意一樣的精打精算:這個要討好,那個不得罪,例如他推出的健保方案,討到了窮人的歡心,他在健保的執行上,他又...
目錄
自序 ☉南方朔
【輯一】領導力
領導人不要只盯著他們自己的那個位子,而是要去激勵、創造及分享一種能夠凝聚人心的願景。「偉大事務」不是要搞什麼豐功偉業,而是去和人民共享熱情與願景。
林肯的靈魂
伊莉莎白一世的逆境領導
領導的守則
誤國的自戀型領袖
當領袖不領導
BB玩具槍打不了仗
真無能,還是假孬種?
七宗壞領導
君子惡居下流
獅、狐、鴿、蛇的政治性格
領導的謊言
請鬼拿藥單
運氣不能當本領
水溝裡的萬言書
講話風格定勝負
優秀的個人搞出三流的國家
民主貴族傑佛遜
【輯二】經濟力
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他們的生命與事業結合為一體,他們的創業僚屬也自然而然的榮辱與共。他們像家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持警覺和警戒。有這種精神的國家和企業,等於是個生命狀態良好的有機體。
小羅斯福的經濟新政
消除金融文盲
認同經濟學
從美國金融國災到台灣政策災
經濟危機「戰」起來?
悲慘指數
畢業即失業
兩層經濟論
漲和不漲都不行
瞎子摸「數字」
回不去的幸福時光
聖誕老公公的政治
剝削到底的高鐵案
梭魚政治
徵不到的稅
切不斷、理欲亂的黨產問題
新富階級的低檔社會
經濟「內部自主性」
【輯三】安治力
一個夠資格的領導人應當是「一個組織團結與共識的象徵」,他必須是那個組織的凝聚點,而不能成為力量分散的來源;從掌權之日起他就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使自己的團隊與有榮焉,使對立的另一方視他為可敬的對手。
眾人皆懼我獨勇
不能射殺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
正當性危機
道德勇氣
無間道在台灣
黑白同一掛
黑白共治?
以反貪興,以貪腐亡
解析「金瓶梅」式的弊案劇情
人與獸一線間
製造問題的台灣領袖
誰用敗德詛咒台灣
修辭莫若修心
X很大,輸很大?
無能併發症
「和解」不等於「鄉愿」
柔性的宮廷版權鬥
危機倒數「內爆」
政府「推手」不「共構」
有土斯有財
誰該來共苦?
【輯四】開創力
「轉型」就是要把「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的事轉掉,而規劃「以前不可能,將來可能」的事。好領導全以膽識智慧開創希望,超越自己的限制與狹隘,在共同提升的領導下創造出追隨的氣氛。
全球化的新領導
台灣需要被重新「發明」
重建價值制高點
感恩與歉意的新政治
願他們被「更好天使」所觸摸
八卦經濟
「心服」才能「口服」
不被看見焦慮症
思想重建的國家
欠學很危險
媚俗火星文
胡錦濤和章子怡的「公關之旅」
歐墨洛教授的「失敗學」
願台灣政黨都有位金諾克
詮釋的循環
平庸政治
當Nobody變成Somebody
蓋洛普領導研究
催生「人道政府」
不向壓迫和誘惑低頭!
轉型政治學
自序 ☉南方朔
【輯一】領導力
領導人不要只盯著他們自己的那個位子,而是要去激勵、創造及分享一種能夠凝聚人心的願景。「偉大事務」不是要搞什麼豐功偉業,而是去和人民共享熱情與願景。
林肯的靈魂
伊莉莎白一世的逆境領導
領導的守則
誤國的自戀型領袖
當領袖不領導
BB玩具槍打不了仗
真無能,還是假孬種?
七宗壞領導
君子惡居下流
獅、狐、鴿、蛇的政治性格
領導的謊言
請鬼拿藥單
運氣不能當本領
水溝裡的萬言書
講話風格定勝負
優秀的個人搞出三流的國家
民主貴族傑佛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