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發展」有如人定勝天,只要有科技,所有事物都是可以改變的,但波斯曼擔心的是人在運用科技改變事物的同時,也被技術制約,成為科技的奴隸。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想像沒有電腦、電視、手機等科技產物的日子,就如同我們忘記過往諸多思想家在簡陋的物質環境中可以完成至今影響深遠的作品。
作者不反對科技,但是擔心人們運用科技的同時,卻忘記了科技的負作用影響!
本書特色
「科技發展」有如人定勝天,只要有科技,所有事物都是可以改變的,但波斯曼擔心的是人在運用科技改變事物的同時,也被技術制約,成為科技的奴隸。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想像沒有電腦、電視、手機等科技產物的日子,就如同我們忘記過往諸多思想家在簡陋的物質環境中可以完成至今影響深遠的作品。作者不反對科技,但是擔心人們運用科技的同時,卻忘記了科技的負作用影響!
作者簡介
尼爾.波斯曼 Neil Postman
美國傑出的社會觀察家
曾任紐約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院長
麥克魯漢後最具洞察力的媒介環境學派領袖
著有《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等暢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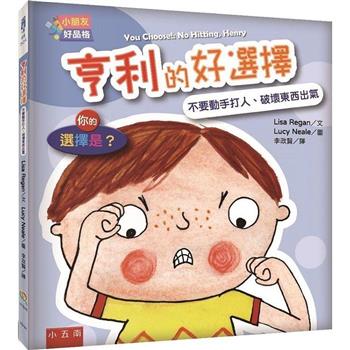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