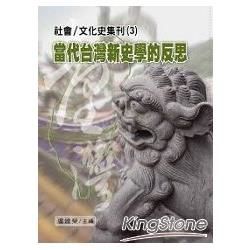台灣新史學運動一甲子(1949-2009)過程中,有六○年代許倬雲所發起、並提倡的以社會科學為輔以治史,以及九○年代李孝悌、蒲慕州、熊秉真等從事的新文化史研究風潮。前述許氏學風可追溯至大陸時期(一九三○、四○年代)的潘光旦,而新文化史學風可溯源自同時期的顧頡剛和台灣一九八○年代的陳其南和汪榮祖等人的治學風尚。
本期的編輯重點有二:首先,持續對台灣史學霸權機構和學閥、以及扈從的共犯結構,作深度探究;其次,讓新文化史的實踐作品以呈現更多元題材的方式給予登刊。關於前者,乃本期的專號。在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迄今只有盧建榮一人敢於用批判的路徑、去檢討學術後進國的種種弊病。本期也不例外,很可惜只邀到盧氏一人對台灣新史學業績加以評鑒。在台灣,有人標榜「新史學」辦雜誌,幾十年下來,有新史學味道的文章屈指可數。這大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況味。本誌為幫讀者把關,來稿都經層層過濾,所有陳年老貨都在排除之列,這點還請讀者寬心。本期盧文原寫於六年前,因故未能即時刊出,今日得見,一點都未過時。可見學界弊端,一時三刻仍不易去除。本誌還特邀盧氏對於該稿受阻一事予以敘述原委。此事事涉台灣學術威權主義,值得關心台灣學術前途的讀者多予留意。台灣的秘密審查制和大學評鑒制,正是暴露台灣學術威權主義的兩件指標性公共事務。要明瞭台灣學術威權主義有多惡劣,只消親近審查制和評鑒制便可感受很深。
本期有五篇新文化史的實踐作品。來自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張仲民,是當今中國投身新文化史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博論寫關於晚清民初文化菁英如何打造衛生文化,早已是我用作研究生的訓練教材。他這次的演出是一次博士後新開發領域的成功之作,這證明他有拓植新領域的能力。他處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問題,以湖南省會的地方知識份子如何串連全國知名人士來打造新文化,使之在地方著床、生根。這樣的研究大有直追法國新文化史大家達涅勒‧侯胥(Daniel R.che)從事法國啟蒙運動如何透過地方知識團體向全國傳播的研究情形。這樣的研究很值得作中西比較。
另有一文是關於古代中國上層文化如何向下層滲透的問題,由沈柏宏所提供。他用的是學者熟悉的一份材料,即《禮記‧曲禮》篇此一文本,卻發人所未發,解答了上古中國文明如何誕生和傳播的疑問。這是一個重大學術課題,幸賴研究裝備更新才得以提出一個饒富創意的假設性學說。當今西方新文化史的先驅大師諾伯特‧埃里亞斯(N.rbert Elias)追索近代西歐文明的搖籃,提出文藝復興末期原屬各個宮廷的一套行為準則,因文化菁英轉教給下層社會,導致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沈柏宏所究的製禮文本作者和記載禮儀事件的史家乃是轉輸上古中國宮廷文化至民間社會的有為之士。這些文化菁英的轉輸文化工作其實是一種文化傳播的過程。這跟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所為有異曲同工之處。上古中國禮文化不下庶人的禁制被摧破,造就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躍升。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就文化塑模過程中,也少不了文化菁英將新文化「神火」「偷盜」到民間去。中國現代文化菁英要裂解的是舊文化對人思維的禁制。
有了張仲民、沈柏宏兩文的今古對照,應讓讀者對文化傳播的問題,用新文化史的方式來作會更加印象深刻。
再來一篇貢獻也很大,而且,更重要地,作者能跳脫禁錮人心達一百三十年的舊思維,予以廓清。這位作者是莊勝全先生,允為台灣史研究領域的明日之星。話說清朝治理台灣,是治權達不到原住民生存空間的,但原住民偶會殺害路過其地盤的洋人,卻讓清廷陷入國際交外紛爭事務中。清廷為避免外人遭原民殺害事件的發生,乃祭出開山撫番的政策,思一舉將山區的原住民納入帝國控制。這是大清帝國以武力為後盾,將掌握中的原住民施以同化政策的嚆矢。從清末以迄今日,現代學者多採當年帝國的視角視開山撫番為正面價值之事。現在莊文指出,清帝國在無力施行種族屠殺辦法下,乃以文化帝國主義的辦法去消滅原住民文化。有清治台官員涉及「開山撫番」事務者於事後都有書刊出版,這些書刊文本正是莊勝全賴以分析文化帝國主義的材料。這是史家治清史,頭一遭站在弱勢原住民,而非仰帝國鼻息在進行歷史書寫。其學術意義格外重大。
再來一篇是由宋天瀚提供的有關兩岸華語電影的歷史建構問題。近二十年來中、台電影的文化創投產值正好高下懸殊。兩岸在華語世界影像化之下各有不同的文創策略。台灣由政府所行的輔導金制證明開創不出大格局。台灣這三年票房破億的電影,諸如〈海角七號〉和〈艋舺〉,其成功既與輔導金制無關,其故事也非歷史古裝片。中國電影以大堆頭方式大拍古裝片,和台灣以小成本方式拍現狀寫實片,形成有趣的對照。多年前我引介史界要留意電影作為一種新興史料、要如何透過它來書寫歷史、解釋現在,因而有法國安娜學派史家馬克‧費侯(Marc Ferr.)《電影與歷史》一書中譯本的推出。很欣慰在華語世界有宋先生願意試走馬克‧費侯的路:以電影為材料來研究歷史。
又有一篇是由褚文哲寫關於一位負面形象帝王傳記的形成這一問題。作者從兩《唐書‧中宗本紀》本文的敘事結構,發現到在位僅五年卻任命二十七位宰相的高人事變動率,以及第二次改年號後縱情遊樂事件的引人注目等兩項情節編織。這活像中宗皇帝只有這兩類事值得紀載似的。事實上,中宗發表過許多人事命令,不止宰相任命案,他也做過許多旁的事;在他任內的後半即令玩樂節目增多,他還是要做許多皇帝該做的事。作者指出如此偏枯紀載的背後大有玄機。那就是代表士大夫立場的史官第一忽視中宗長期處在驚弓之鳥的心理歷程和外戚集團為皇帝縱容的心理歷程與狀態,以及第二視危及士大夫政治地位的後宮勢力和外戚集團為皇帝縱容的結果,因而在潛意識裡對中宗是敵視的。這樣的史家記載法暴露了一則不具同理心去神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二則太過忘情投入歷史情境,以致認可敵對雙方的任一方,特別是與史家相同文化背景的那一方。這幾乎觸碰到了傳統史家認知歷史薄弱的一面。
最後,要介紹的一篇是由傳播學者夏春祥所提供的關於新聞史新研究取向的討論。夏先生於1998發表其成名作〈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一文,即預示了他將來在傳播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博論是探討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政治過程中如何被報導、評論,以及如何被挪用作文化政治的武器這樣的問題。當該作被正式出版後,即獲數項傳播學界的大獎,遑論佳評如潮了。另外,夏先生另一項學術貢獻,是台灣於上一世紀九0年代將集體記憶課題提出學術議程表上,他是少數二、三位先驅者之一,這形成王明珂代表歷史學界,蕭阿勤代表社會學界,而夏先生則代表傳播學界,在這學術議題領域的深耕經營。在本期夏文中,夏先生對新聞史/傳播史的研究提出另一個替代方案,那就是不再究心於報人、名編、名記者等報業從業菁英其政治立場的挖掘,改而針對媒體人從事職守的過程中,他們如何與外部社會條件產生某種依存關係,再由此去界定他們報導新聞的可行性。不論媒體人如何受限於外部種種社會機制,他們留下來的業績是資產、而不是負債。從而新聞史的寫作不再是聚焦於媒體人如何實踐其新聞專業倫理這一點而已。夏先生所提的前瞻性學術大計,在我看來,是傳播學導入歷史面向的新趨勢,正是本刊所側重的新文化研究的重要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