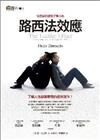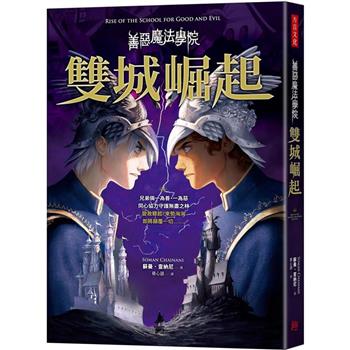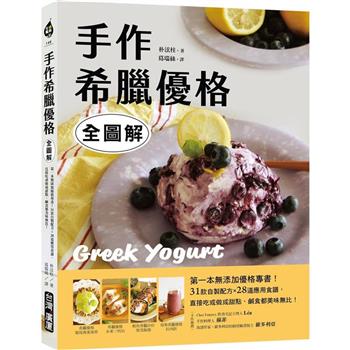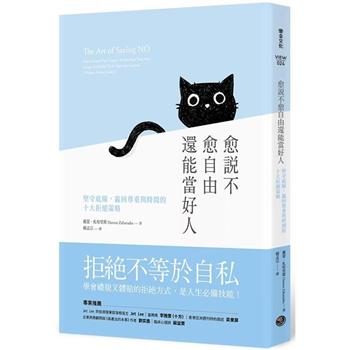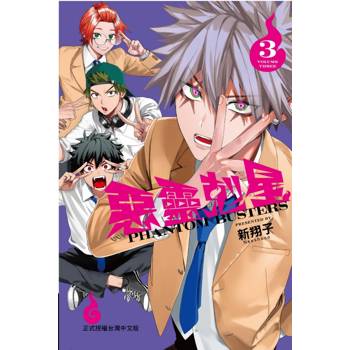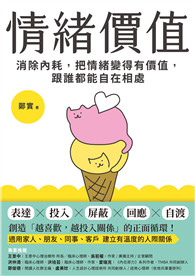全球最具傳奇的真人實境實驗,了解人性最需要看的經典著作!
一九七一年,社會心理學家金巴多教授主導「史丹福監獄實驗」;該實驗有如一發震撼彈,引爆全球心理學界重新審視以往對人性的天真看法。
三十年後,金巴多教授以《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首度親自撰述、並呼應從「史丹福監獄實驗」到「伊拉克監獄虐囚案」三十多年來觀察到的社會現象,深度剖析複雜的人性,全盤且深入解釋「情境力量」影響個人行為的概念。
在實驗中以標準的生理與心理測驗,挑選了自願擔任受試者、身心健康且情緒穩定的大學生,被隨機分派到「守衛」和「犯人」兩組,接著讓他們身處模擬的監獄環境。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角色規範的影響,努力去扮演被指定的角色。實驗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轉變為殘暴不仁的守衛或是情緒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分,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為期兩週的實驗不得不宣告中止。
為什麼握有權力的人,很輕易地為「以控制他人為樂」所誘惑?而置身弱勢角色的人,為什麼卻常以沉默來面對問題?。藉由獨具開創性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研究,金巴多教授將為讀者解釋「情境力量」和「團體動力」如何能使平凡男女變成殘忍的魔鬼。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努力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例如「男性-女性」、「上司-員工」、「父母-子女」、「老師-學生」、「醫生-病人」等關係,在這些社會角色劇本的規範與束縛下,我們是否會像上帝最愛的天使路西法一樣不知不覺而對他人做出難以置信的事?
本書提供認識地位和權力角色差異的原因;了解在環境中影響個人思考、情感及行動的形成及改變原因;幫助讀者重新審視、了解自己,一旦面臨陌生情境,自己「會做什麼」及「不會做什麼」,以及面對情境的強大壓力,如何勇敢反抗「路西法效應」。
章節試閱
天使、惡魔,以及其他泛泛眾生的轉變
我寫《路西法效應》是為了試圖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轉變為去為非作歹的過程。首先,我們得面對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讓人為惡?」我們暫且摒除宗教的善惡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後天失調的原則。我們將以生活中的真實人們為例子,看他們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並且在人性混雜的大鍋爐中生存下來。換句話說,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強大情境壓力下產生轉變?
讓我們為邪惡下一個定義。我的定義十分簡單,基於心理學一個原則:邪惡建立於涉及傷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毀滅無辜他者的刻意行為,或使用權威、系統力量鼓勵且允許他人這麼做,並從中取得利益。簡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驅使人類行為的動力為何?是什麼決定了人類的思考和行動?是什麼讓我們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而相對地又是什麼讓人容易拋棄禮規、犯下罪錯?我們在回答這些人性問題時,是否都先假設是「內在因子」決定了我們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而都忽略了「外在因子」對於人類思考、感覺及行動的影響?在什麼狀況下我們會成為情境或群體行為下的產物?有什麼事是你自信絕不會在任何脅迫下做出的呢?
因為自我中心的偏見,大多數人都有認為自己是最特別的幻覺。這個自利歸因的保護罩,讓許多人一廂情願地相信自己在許多自陳測驗中處於平均值之上。我們往往習慣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窺天,卻常常忽略了腳下踩踏著滑溜的斜坡。這種情況在強調個人取向的社會中十分常見,例如歐美社會,但較少見於亞洲、非洲和中東等強調群體取向社會。
在我們探索良善與邪惡的旅程中,請你先試著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擁有那些優點、那些缺點?你的自我認知,是來自一個過去曾經出現相同行為的類似情境,還是在一個過去習慣飽受挑戰的新情境?根據這個脈絡來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與你互動的人們,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書其中一項重點就在於強調,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往往來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經驗,這其中牽涉了規則、法律、政策等各種外在壓力。我們上學、度假、聚會,支付帳單和稅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當我們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環境下,過去經驗或習慣無法應付時,會是如何呢?開始一個新工作、第一次和網友見面、參加新社團、被警察逮捕、從軍當兵、參加某個教派,或自願擔任實驗受試者……,當習以為常的遊戲規則動搖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將不如從前一般好用。
現在,我希望你在看見不同形式的惡行時,能不斷詢問自己:「我也會這麼做嗎?」我們將在後面章節檢視「盧安達屠殺事件」、發生在南美洲蓋亞那的「人民聖殿集體自殺事件」、越南的「美萊大屠殺」,駭人的納粹集中營、全世界軍事和警方的嚴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隆」和「世界通訊」詐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恥欺瞞行為的有關跡象。
最後,我們會看看從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線索,能如何解釋可怕的阿布葛拉伊布監獄虐囚案。本書背後驅使的動力,是為了了解美軍如何及為何會對位在伊拉克的阿布葛拉伊布監獄犯人做出生理和心理的虐待行為。這些虐待影像證據於二○○四年五月在全世界爆發,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如此鮮明的歷史記錄:年輕的美國男性和女性,用令人無法想像的方式虐待他們應該保衛的人民。這些軍人在施展暴力行為時,甚至還以數位影像捕捉受害人遭受的痛苦。
為什麼要留下這些一旦公開就會讓他們陷入麻煩的影像證據?在這些如戰利品般的照片裡,他們就像獵人展示獵物般驕傲,我們看到微笑的男人和女人在虐待卑微的動物。這些影像有拳擊、摑耳光、踢犯人,跳到犯人的腳上,強迫他們赤裸,給他們戴上動物的毛和角錐。強迫赤裸的犯人在頭上戴女性內衣,強迫男性犯人在拍照或攝影時對微笑的女軍人手淫或口交。甚至把犯人掛在屋椽一段時間,用約束帶綁著犯人的頸子拖行,用沒有戴嘴套的惡犬嚇這些犯人……
我們將會發現這些都與心理學研究提供的線索環環相扣,特別是史丹福監獄實驗,緊緊關係著這些殘暴事件。
犯人8612成為不定時炸彈
道格8612並不是個合作的傢伙,他不接受剛從申訴委員會回來同伴的說法,然而他越是這樣,就讓他越有機會再進「黑洞」,手銬無時無刻都在手上。他說他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要求見典獄長。過一會兒,典獄長傑夫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他,聽他抱怨守衛的行為如何專制且「殘暴」。傑夫告訴他,是因為他的行為引發了守衛們的強烈反彈,如果他願意更合作的話,傑夫可以保證守衛對他的態度會變緩和。8612卻說,除非這樣的情況很快就可以到來,不然現在他就想要出去。傑夫也擔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還詢問8612要不要去看醫生。犯人被護送回他的囚房,但一回房他就開始和理奇1037互吐苦水。理奇同樣抱怨令人難以忍受的情境,還有他也想要去看醫生。
即使好像在見過典獄長後有稍被安撫,但是犯人8612用誇張的音調大聲呼喊,堅持要面見「他媽的金巴多博士」,也就是「警務長」本人我。我立刻答應見他一面。
沒多久,一個悶悶不樂、叛逆、憤怒且有些意識不清的年輕男子走進了辦公室。
「什麼事情讓你心煩呢,年輕人?」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這些守衛不斷地騷擾我,他們總是挑我毛病,隨時隨地都要把我放進「黑洞」裡,而且──」
「好,從我知道的看來,我想你這樣是自找的;你是整個監獄裡頭最反叛、最不守規則的犯人。」
「我才不在乎,你們違反了所有合約上的規定,我並沒預期自己會被這樣對待,你──」
「站著別動!小流氓!」卡羅(這個實驗的顧問,曾在獄中服刑)猛然用兇悍的口吻抨擊8612:「你說你沒辦法撐下去?伏地挺身、青蛙跳,守衛嘲笑你,向你大吼?那就是你所說的『騷擾』嗎?別打斷我!然後你哭著說他們把你丟在櫥櫃裡幾個小時?讓我來教育你一下,白種男孩,你在聖昆丁監獄撐不到一天的,我們會嗅出你的恐懼和軟弱。你的守衛會從你的頭上一棒揮下,並且把你丟到真正讓你感覺到無比孤獨、空無一物的坑洞裡,我在那裡忍受過一次就是幾星期的生活,而你才這樣就受不了。不知死活,如果遇到壞透了的上頭,就會塞給你兩、三包香菸,讓你的屁股鮮血直流,青一塊紫一塊,而那只是將你變成娘娘腔的第一步而已。」
8612被卡羅一席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嚇傻了。我覺得卡羅就要爆炸了,可能是他看見我們監獄中的擺設,勾起了他前幾個月在監獄中的血淚回憶。
「8612,如果你選擇留下來並且好好配合,你知道我有權力讓那些守衛不要再騷擾你。你需要這些錢嗎?如果你決定提早結束,就會失去剩餘的酬金。」
「哦,當然,不過……」
「好,那麼我們就這麼先說定了,不會再有守衛騷擾你,你留下來賺剩下的酬金,可是你要以好好合作來回報,並且任何我有需要的時候,你都必須提供我訊息,好讓我可以正常運作這座監獄。」
「這個嘛……」
「聽著,想想我答應給你的優惠,然後接下來,晚餐過後如果你依然想離開,那沒有關係,我們會依照你的時間算給你酬金。但是,如果你決定繼續留下來賺足全部的酬金,不被騷擾並且和我合作,我們就可以把第一天的問題拋在腦後,好好地從重新來一遍,同意嗎?」
「說不定可以,但是──」
「沒有必要現在就做決定,你可以好好考慮我給你的優惠,然後晚一點再做決定,好嗎?」
8612小聲地說:「好吧,就這樣。」我送他到隔壁典獄長的辦公室,讓傑夫送他回大廳。我也告訴傑夫,他仍然還沒決定要留下來或是離開。
當下我想了一下這個浮士德交易,我決定表現得像一個邪惡的監獄管理者,而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大教授(我認為我應該是)。作為警務長,我不希望8612離開,因為這樣會給其他犯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我認為,只要守衛收回對他的責罵管教,他應該會更合作才是。我也邀請反叛頭頭8612成為「告密者」、「線人」,作為我給予他特殊權利的回報。在監獄生態裡頭,告密者是最低微的階層,並且常常被當局隔離到禁閉室裡,因為他的同伴知道他告密後,有可能謀殺他。
犯人告訴大家:誰都不准走!
在大廳後面,守衛亞涅特和大蘭德里在他們日班交班之前,要犯人各個面牆開始報數。監獄入口打開時發出尖銳的聲音,整齊成列的犯人們看著8612在和監獄高層會面後走入大廳。在見我之前,8612對他們宣稱這會是一個一路順風的會面。他要退出,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他再停留一分一秒。但現在,道格8612擠過隊伍,回到二號囚房,把自己丟到床上。
「8612,出來面對著牆!」亞涅特命令他。
「去你媽的!」他帶著藐視的意味回答。
「給我面牆!8612!」
「去你媽的!」8612還是這麼回答。
亞涅特:「叫誰來幫他一下忙!」
大蘭德里問亞涅特:「你有這副手銬的鑰匙嗎?長官?」
就在他的房間裡,8612大叫:「就算必須待在這裡,我也不會去做任何你們要我做的該死事情!」當他終於漫步到大廳時,幾乎一半的犯人都在二號囚房裡頭兩面排開,道格8612告訴他們一個糟透了的事實:「我指的是,你知道的,真的,我指的是,我不能離開這裡!我花了所有時間和醫生、律師們談……」
他的聲音漸漸轉小,越來越讓人聽不清楚,其他犯人咯咯偷笑,但他還是站在其他犯人面前,違抗必須面牆站立的命令。8612狠很地給了他的同伴一記上鉤拳,又用大聲、激昂地高八度音調嘶吼:「我不能出去!他們不讓我出去!你們也休想出去!」
他的同伴一聽,先前的咯咯輕笑立刻轉變成帶點緊張的苦笑。守衛們決定暫時不理8612,繼續找尋消失的手銬鑰匙。因為如果他再這樣胡鬧下去,他們就必須盡快銬住8612,再一次把他塞回「黑洞」裡。
一個犯人問8612:「你是說,你不能違背合約?」
「那我可以取消我的合約嗎?」另一個犯人絕望地問,其他人都豎起了耳朵。
亞涅特強硬地說:「在隊伍中不准講話,8612等等就遭殃了,跟他講話的人也一樣。」
從他們敬重的領導口中講出來的這段話,對他們而言是一大打擊,打擊著他們的違抗意志和決心。
葛蘭3401事後報告了8612的說詞對他的影響:「他說『你們都不能出去』時,讓我感覺自己真的是一個犯人。或許你不過只是金巴多實驗裡頭的一個犯人,也許你是因為酬金才來坐牢,但你真的是個犯人了!」
他開始想像故事可能發生的最糟情節:「我們把我們的命給簽了給賣了,包括身體和靈魂,這真是非常令人感到害怕。『我們是真的犯人』的這個信念,實際上越來越真實──沒有人可以逃離開這個,除非採取強烈的手段,但強烈的手段卻會帶來一大串不可知的後果。帕洛阿圖市的警察會再把我們抓走一次嗎?我們會得到酬金嗎?怎樣我才可以拿回我的皮夾呢?」
這個事件也讓守衛整天看管的大麻煩──理奇1037,目瞪口呆。他在事後報告:「當我聽說我不能離開的那個當下,我覺得這是個真正的監獄。我無法形容我那時的感受,只能說我感到徹徹底底的絕望,有生以來第一次那麼絕望。」
這讓我清楚明白,8612已經讓自己身陷於無數的兩難之中,他想要成為強悍的反叛領頭,但是又不想要守衛不停地緊盯騷擾,他想要留下來賺更多酬金,但是又不想成為我的線人。他或許想過要怎麼兩頭通吃──對我說謊,或者誤導我有關犯人的行動,但是他並不確定自己有這方面的能耐。他也大可當面回絕我的優惠,拒絕當我正式的告密者來換取舒服的日子,但是他卻沒有。在那個當下,如果他堅持要離開,我也只能同意他的抉擇。也可能只是因為卡羅的教導和喊罵,讓他感到太過羞愧。這些可用的心理遊戲讓他打定主意,對其他人堅稱官方決定不釋放他,把這一切都怪罪給整個系統。
再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對犯人產生這樣強大轉變的影響,突來的消息表明,他們將失去要求中止的自由,喪失他們走出監獄的權力。在那個當下,史丹福實驗監獄瞬間轉化為史丹福監獄,不是經由工作人員上對下的宣告,而是來自他們底層犯人中的一員。正如犯人反叛改變了守衛們對犯人的想法,他們開始覺得犯人是危險的,而犯人之一堅定的說詞,告訴大家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也讓這些「假犯人」開始感到,他們的新處境真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犯人」。
報數的新意義
正式形式上,就我可以想到的報數有兩種功能:讓犯人熟悉自己的識別號碼,並且在每次交班的時候確認大家都在。在許多監獄裡,報數被視為一種訓練犯人的手段,但縱使一開始的報數顯得單純,我們每晚的報數和他們早就出現對立的角色,到最後變成了一種逐漸擴大增強的痛苦經驗。
「好,男孩們,我們要來做個小小的報數!這會很好玩的!」
守衛赫爾曼(Hellmann)咧嘴笑著告訴他們,守衛小蘭德里很快地補充:「你越快做,就會越早結束。」這些疲累的犯人走到大廳、排好隊伍時,都沉默地繃著臉,眼神沒有交集。對他們來說,這已經是漫長的一天,誰知道他們昨晚最後終於入睡之前,心裡是怎麼想這個實驗的?
小蘭德里下命令:「向後轉,手抬起來抵著牆壁。不准交談!你希望整晚都一直做這個動作嗎?我們就做到你們做對為止,開始一個一個報數!」赫爾曼跟著火上加油:「給我做快點!給我大聲喊出來!」犯人們遵從了,但是:「我還是沒聽清楚,再做一次,小伙子,做的糟透了,慢吞吞的,再給我做一遍。」「這就對了!」小蘭德里插話,「但我們必須再做一次。」幾個成員馬上大聲呼喊,赫爾曼卻更大聲地吼叫:「停!這叫做大聲?或許你們沒有聽清楚我的話。我說要再大聲一點,我說要再清楚一點。」「讓我看看他們能不能倒著數回來,現在從另一頭數回來!」小蘭德里一副開玩笑的樣子說,「嘿,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個人偷笑!」赫爾曼則粗暴地說:「我們今晚就在這裡做到對為止!」
有些犯人已經察覺,支配優勢之爭已在赫爾曼和小蘭德里兩個守衛中引爆開來。從不認真看待這一切的犯人819,開始大聲嘲笑赫爾曼和小蘭德里「犧牲犯人的時間為的只是彼此較勁」。「嘿,819,我說過你可以笑嗎?或許你沒有聽清楚我說什麼!」赫爾曼第一次發脾氣,正對著犯人的臉,身體傾向他對他施加壓力,一邊用警棍推擠他。小蘭德里趕緊把他的同事推到旁邊,並且命令819做二十下伏地挺身,819乖乖地照做。
赫爾曼接著回到舞台中心:「就是現在!唱歌!」當犯人們正在報數的同時,他打斷他們,「你們沒有聽到我叫你們唱歌嗎?或許是你們頭上這個絲襪帽太緊了,緊到你們聽不清楚我說話。」他變得在控制技巧和對話上越來越有心得,轉身面向犯人1037,用走音的方式唱著他的號碼並且命令他做二十下青蛙跳。當他做完,赫爾曼又說:「你可以再為我多做十個嗎?為什麼你做的時候會有咯咯的聲音?」做青蛙跳的時候,誰的膝蓋不會咯咯作響的呢?這些命令變得越來越無理取鬧,但是,守衛也開始從發佈命令強迫犯人就範中找到樂趣。
雖然對他們而言,叫犯人們「唱數」是挺有趣的,但是兩個犯人選擇勇敢挺身而出:「這一點都不有趣!」,並抱怨:「這實在是糟透了,感覺差到極點了!」「再來一次,」赫爾曼卻告訴他們「你們給我唱,這次我要『甜』一點的聲音。」然後犯人一個接著一個做伏地挺身,只因為他們唱得太慢或是唱得太難聽。
當替代守衛柏登和典獄長一同出現時,這生動的雙簧二人組──赫爾曼和小蘭德里──立即轉而要求犯人們以識別號碼報數,而非原先排列由1到9的順序報數,想當然爾他們喊得零零落落。赫爾曼堅持他們不可以偷看自己的號碼,因為他們早該背得滾瓜爛熟,所以如果任何一個人背錯他的號碼,懲罰就是每個人都做十二下伏地挺身。赫爾曼變得更加專制無理,暗地裡仍然和小蘭德里競爭守衛的權勢位階:「我不喜歡你做伏地挺身『下去』時報數的方式,我要你在『上來』的時候給我報數。再給我做十個可以嗎?5486?」這個犯人更明快地執行指令,卻反而增強了守衛予取予求的私心。赫爾曼說:「好,這很好。為什麼你們現在不唱給我聽呢?你們這些人唱得實在不怎麼樣,對我而言,聲音一點都不甜美。」小蘭德里跟著說:「我不認為他們有準確地跟上拍子,是不是可以唱得再細膩一點、甜美一些,讓耳朵好好享受一下?」819和5486在這個過程裡不斷遭遇挫敗,但是說也奇怪,竟肯順從守衛的要求,接受更多青蛙跳的處罰。
新的守衛,柏登,比任何其他守衛都還要快進入狀況,也剛好有兩個前輩模範讓他有個現成的在職訓練,「喔,那真是太棒了,我就是要你這麼做,3401,出來自己秀一下,告訴我們你的號碼!」柏登站在他的同事後面,伸手將這位犯人從隊伍中拉出來,好讓他在大眾面前獨秀報數。
緊接著被盯上的,是犯人史都華819。他被要求一次又一次獨唱,但是他的歌聲始終被認定「不夠甜美」。守衛們爭先恐後地戲謔他:「他肯定沒辦法甜美的啦。」「不,對我而言這樣還不夠甜美。」「再來個十次!」赫爾曼好像很高興柏登開始像個守衛了,不過他並不準備放棄對他或小蘭德里的控制,開始叫犯人背誦隔壁犯人的號碼,如果他們不知道,那就是再來幾個伏地挺身。但是,當然大部分人都不記得下一個人的號碼。
「5486,你看起來好像真的很累,你不能再做得更好了嗎?讓我們再來個五下如何?」赫爾曼靈光一閃,又想到新點子,開始教導怎麼才絕對不會忘記傑瑞5486號碼的記法:「一開始先做五個伏地挺身,再來四個青蛙跳,接著八個伏地挺身加上六個青蛙跳,這樣一來,你就會完全正確地記得他的號碼是5486」。他已經開始更機靈地設計新的處罰方式,創造邪惡之第一個徵兆。
小蘭德里忽然退到大廳的另一邊,顯然是將權勢交給了赫爾曼。他一離開,柏登就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並非與赫爾曼競爭,而是助紂為虐,在一邊加油添醋或誇大其詞。但是小蘭德里並沒有真的離開,很快就又回過頭來命令另一個犯人報數,因為他不滿意,所以要求他們一次兩個人一起數,接下來三個四個往上累積。他顯然不像赫爾曼那麼有創意,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暗潮洶湧地相互較勁。5486開始糊塗了,伏地挺身越做越多,赫爾曼突然間打斷他,說:「我要你七秒鐘內做完,但是我知道你沒有那麼厲害,所以過來這裡拿你的毛毯。」小蘭德里卻有意見:「等等,先別動,將手頂在牆上。」赫爾曼並沒有下這個命令,大夥在權威戰中「牆頭草,一面倒」,沒有人理會小蘭德里最後下的命令。赫爾曼叫大家解散,各自拿自己的床單和毛毯,整理床舖,並在自己的囚房裡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赫爾曼得到了保管鑰匙的權利,上鎖囚房。
天使、惡魔,以及其他泛泛眾生的轉變我寫《路西法效應》是為了試圖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轉變為去為非作歹的過程。首先,我們得面對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讓人為惡?」我們暫且摒除宗教的善惡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後天失調的原則。我們將以生活中的真實人們為例子,看他們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並且在人性混雜的大鍋爐中生存下來。換句話說,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強大情境壓力下產生轉變?讓我們為邪惡下一個定義。我的定義十分簡單,基於心理學一個原則:邪惡建立於涉及傷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毀滅無辜他者的刻意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