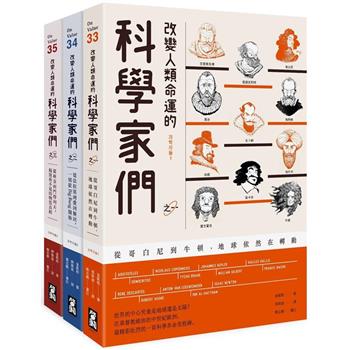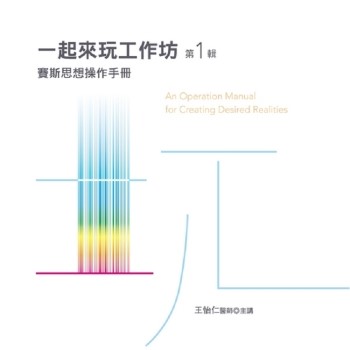兩千年前的羅馬帝國官方語言拉丁文,為何至今它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拉丁文對西方世界有什麼深厚的影響?拉丁文漸漸沒落,在西方宗教界、學術界仍處處出現拉丁文,這又是為什麼?拉丁文為現代社會提供了一幅怎樣的想像願景?
隨著羅馬帝國打遍天下的拉丁文,曾是西方文明和知識的重要源頭。雖然羅馬帝國瓦解於五世紀,拉丁文深厚的文化和知識寶庫依然讓這種語文流傳近兩千年的歷史。拉丁文曾經孕育了許多文明的種子,它的文字深深影響了西方世界各種語文,至今,所有生物物種的學名以拉丁文命名。
文藝復興運動後,拉丁文在十六世紀獲得史無前例的重視。天主教教會決定以拉丁文作為禮儀語言,學校也以教育拉丁文為主,西方世界沉浸在拉丁文的世界中。雖然當時各地方言日益抬頭,拉丁文仍以其優異的文化傳統屹立不搖。拉丁文是各種方言詞彙之母,是學習語言所無法規避的必經之路。
然而隨著講求效益、實用的近代社會出現,西方世界正面臨了一場語文的大革命。拉丁文面臨了經濟效益和實用性的大考驗。雖然各界領袖極力擁護拉丁文,聲稱拉丁文是人文主義教育的根源,仍然不敵實用性的挑戰。《拉丁文帝國》作者瓦克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和文化史專家,精彩且詳細描繪了西方世界這一段的語文陣痛期,並分析了為何在教會、教育界和貴族的支持下,為何最終還是走向衰弱一途。
二十世紀,拉丁文不再獨佔教會禮儀,學校也不再強制學習拉丁文,但仍有些許學生投入拉丁文的懷抱,緬懷那份文明源頭的歷史。想要理解拉丁文的命運,以及它之所以曾為西方世界文明的搖籃,這本歷史資料豐富、分析透澈的《拉丁文帝國》將你走一回拉丁文及西方文化的近代史。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瓦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撰寫多本歐洲文化史的專著,包括《王朝復辟時期或舊制度重現下的皇室節慶》、《法國模式與博學的義大利。文學界的自我意識與對他人的感知,一六六○至一七五○年》、《文壇朝聖者葛羅諾維斯:探討十七世紀的學術之旅》、《文學界》等。譯者簡介:
章節試閱
一五七八年,蒙特佩利爾醫學教授儒貝爾獻一本書給納瓦爾女王馬格麗特,標題是《醫學和養生法常見的錯誤》。雖然標題是這麼寫,內容主要卻是探討產科學。這點使它遭到很多醫生強烈譴責。他們責備這位同行把一本含有「所謂下流題材」的書,獻給一位「最貞節、高貴的女王侯」。他們指出「這一切用拉丁文比用法文合適」:其中一個理由是,「這些話用外語聽起來,不像用通俗語言那麼糟,而且會對這些話甚感羞恥的婦女和少女,過去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佛羅倫斯人科泰利尼出版《人體解剖學入門》時(Instituzioni dellanatomia del corpo umano,一六五一年),也遭到同樣指責:有人指控他淫穢,因為他用義大利文論述解剖學,而且沒有用拉丁文描述人體(至少人體的某些部位),因而使女性的端莊陷於危險境地。
在英國,基於社會因素,所謂「大眾化」的醫學作品在清教徒革命期間開始出現,這些作品雖以原著為主,但更多是拉丁文著作的譯本。它們的作者和譯者放棄拉丁文,改用被視為「粗俗的」英文詞彙描述性器官和生殖過程,對此他們不得不為自己提出辯解;他們聲明自己正大光明,沒有散布淫詞穢語的不良企圖。他們也努力向讀者(尤其女性)再三保證,讀這類著作不會對他們的「正經」構成任何威脅。
十八世紀期間,醫學著作中不但有類似的意圖聲明,而且都訴諸古代語言。一七三六年,身兼御醫和皇家中學教師的阿斯特律克,以拉丁文發表一部論及性病的著作。他並非不知道如此一來,這本書對不懂古代語言的外科醫生幾乎沒有助益;但更崇高的理由占了上風:不外乎強調「得體」,對於用法文探討某些疾病、描述身體的某些部位感到「可恥」。為了支持自己的立場,阿斯特律克引述醫學權威塞爾塔斯的話。後者在不得不論述陰部感染的疾病時,曾寫道:「陳述這類主題的適當詞彙,用希臘文較能令人接受,也較普遍得到習俗的認可……用拉丁文描述這種疾病反而顯得下流,而且冒犯了正經人士。」因此,拉丁文(可說是現代人的希臘文)在使用上有了正當性。
拉丁文在醫學界的這種用法持續很久,尤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探討性病理學的醫生和精神科醫師的著作中。一八五七年,法國醫生塔迪厄(後來成為巴黎醫學院院長)透過專門出版醫學著作的出版商巴耶爾,發表一部作品,標題是:《妨害風化罪的醫學法律研究》。這部作品探討妨害風化罪、強姦、雞姦和男性間的肛交。在序言中,作者為使用法文辯解,並以專業上的職責為由。
這個主題本質上需要一些用來激發所有正經與羞愧感的細節,但我認為不應在這一切面前退縮。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任何創傷,無論有多腐敗,都不應嚇倒獻身於人類科學的人,而醫生神聖的職務,在要求他必須什麼都看、什麼都知道的同時,也允許他什麼都說。除一點外,我甚至認為不應藉拉丁語來掩飾……
事實上,在提到「雞姦患者的某些類型」時,塔迪厄改用拉丁文陳述,他的解釋是:「如果有人不允許我用簡短而委婉的拉丁文掩蓋這一切,我很可能在這些淫邪的細節面前退縮。」醫生神聖的職務在這裡碰到了極限。幾年後,這段藉助拉丁文的簡短文字(實際上足足占了半頁),原封不動出現在維也納精神科醫師克拉夫特艾兵的著作《性心理變態》中(一八八六年),這是第一部有系統地描述當時所謂的性倒錯或性疾患的作品。克拉夫特艾兵不僅引述塔迪厄的話,也在〈反常的性情感〉那章,將敘述語言由德文改為拉丁文,根據他的自白,這麼做是「基於明顯的理由」。
藉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醫生在論述解剖學、產科學或性疾患時,會再三強調自己心存正念。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別人會如何解讀這些著作:拿來當作性教育手冊、甚至刺激性慾的工具。一六三九年,赫爾姆斯特大學醫學教授梅邦以拉丁文出版一部作品,標題是De flagrorum in re venerea usu(《性事中的鞭打行為》)。書中,他以嚴格的醫學用語檢視並解釋性無能的男女,如何在未被鞭打的情況下有性關係。一六七○年,梅邦的兒子反對再版,並公開表示他生怕該書會引起某些人放蕩;但最後他樂觀其成,因為一想到這個版本將以「只有博學者熟悉的語言」發行,他的顧慮就減輕了。一七一八年的英文版(明顯具有淫穢特色),證實梅邦之子的顧忌不是沒有道理。
拿拉丁文來掩蓋某些事實的做法,並不限於醫學等負有責任的傳統領域。事實上,它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學科著作和記載中。在十八世紀,英國有人用拉丁文寫私人日誌,以記錄不大能公開承認的醫療和疾病的細節。歷史故事偶爾也會改用拉丁文記述。因此,索利尼亞克在著作《波蘭通史》中,為了「不冒犯讀者的高尚正直」,而改用拉丁文敘述十世紀專給私通者和通姦者的性刑罰。歷史學家吉朋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遇到需要描述性方面的事實(如:拜占庭皇后狄奧多拉的「不道德行為」),他改用拉丁文;面對有人抨擊他的作品下流,他不得不為自己辯解,還特別以下述論點反駁對方:「我的英文作品很純潔,所有淫穢的段落都隱蔽在一個學術語言中。」文學也有類似的例子,甚至出現在不被視為一本正經的作家著作中。
法國作家布蘭多默在著作《蕩婦》中,提到義大利作家阿雷蒂諾描繪的性愛姿勢時,放棄使用法文:他先重述以理性和基督教教義為準則的決疑論者的說明,再以拉丁文表達接下來的部分。布勒東是自己主動在著作《尼古拉先生》中,用古代語言記述最初的性衝動:「要描述這個,」他寫道,「我會採用學術語言……」他的做法是,在正文中直接由法文轉換到拉丁文,或將無法在正文中「說明」的部分,移到拉丁文注釋。
以上粗略的研究,不能沒有考慮學校界就下結論。從十六到二十世紀期間,大量使用拉丁文的學校界,同樣賦予這個語言培育人和道德教育的作用。這點導致學校拒絕採用很可能刺激少年,甚至引發他們產生所謂有害思想的著作。儘管如此,仍有一些確實有危險的作品,基於各種因素,叫人無法完全忽略。雖然所謂的「古典」精選版本是主要的解決辦法,偶爾還是有人用拉丁文改寫一些著作。這種改寫舊作的做法,在十九世紀中葉依然盛行;一八八七年泰倫斯作品的英文版(「經審慎刪改以供學校使用的」版本),正是如此。
在一篇標題為《佛密歐》的劇作中,專門拉皮條的多力歐同時被描述成leno(淫媒)和mercator(商人),至於他看管年輕女人的理由則沒有任何交代;因此,某幾行必須改寫,最起碼要換掉leno這個字,結果為了顧及拉丁文韻律學和格律學的規則,造成一連串的修改。同樣在學校界,拉丁文也用來翻譯希臘文學中被視為猥褻、淫穢或有失禮節的段落。例如,阿爾托在一八四一年以法文翻譯《阿哈奈人》(希臘最傑出的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劇作)時,不得不在第一二二○行插入:「至於我,我想要上床睡覺;我受不了了,我需要放鬆一下。」後面的注解是:「這些粗俗的詞語……無法譯成法文。」接著,他用毫無忌諱的拉丁文譯出:Tentigine rumpor, et in tenebris futuere gestio。
在前面引述的許多著作中,作者使用拉丁文是為了「正經」人士著想,講白一點,即不能失去「端莊」的女性。用她們不懂的語言描寫一些事情,或許就能避免冒犯她們。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想一下,女性接觸拉丁文是直到很後期才有的現象。在十七世紀,懂拉丁文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況且,大家舉的例子都大同小異。而懂這個語言的女人,也會把這個事實「當作一種罪過」加以隱瞞,因為她們很清楚這種知識會讓她們在道德上遭受質疑。事實上,拉丁文過去被視為使女人墮落的根源。布蘭多默指出,讓女性學拉丁文,閱讀如奧維德的《變形記》這類作品是有危險的。當然,法國、義大利或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也會有「色情故事」和「淫詞穢語」;但那些都是個人私下的讀物,和研讀拉丁文大相逕庭。後者通常由家庭教師指導,而且一定是男性;當時這必然也是特殊課程,在「密室和小房間裡,閒著沒事的時候」進行。
除了這種一對一教學具有潛在危險外,作品本身也有危險。當出現不拘禮節的段落時,家庭教師不是跳過這一頁(當下反而引起最後總是得勝的好奇心),就是立即提出評注(這種意譯實際上比直譯為害更大)。布蘭多默還提到因此由拉丁文造成的致命影響,和正等著「女大學生」的墮落。一個世紀後,一位始終隱姓埋名的作家也表達同樣的觀點,但他是為女性有得到知識的理由和權利辯護。這位作家一開始就對「知識會帶給女性道德上的危險」這種說法表示反對,他還說:「人家常說學語言是一種惡兆,尤其是學拉丁文。俗話說:『女人講拉丁語,準沒好下場。』」他先以幾位貞風亮節但博學多聞的貴婦為依據,對這種「真理」加以駁斥,接著又質疑支持該論點的理由:「或許有人說,我們在這些學術語言中,發現無人敢用活語言寫出來的淫詞穢語,而這會讓女孩子學到我們想要隱瞞她們的事情。」
然而,拉丁文也出現在被當作「學者的語言」(也就是男性文化菁英的語言)引用的例子中。在這裡,我們的問題是:如果信息都一樣,當領受者是懂拉丁文的男性時,究竟是哪方面沒有冒犯人的特性?當時的教學法提供了答案。雖然拉丁文肯定會讓女性墮落,但對男性而言,學這個語言卻反而對他們有益:拉丁文被視為男性的一種補品,能訓練他們的判斷力,不僅防止他們犯錯,也提防他們落入第一印象。
當拉丁文終於和所有不「得體」之事畫上等號,語言學方面的省思針對這點提供了解釋與證實。波爾羅亞爾社團的邏輯學家因此對詞義下了一些評注,其中包括他們視為基礎的以下這點:「……一個詞除了被視為該詞本義的主要概念外,還會產生好幾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可稱之為次要概念),儘管後者已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印象,我們卻沒有注意到它們。」其次,他們提出「不得體」的字眼和措辭的問題,以便知道它們是否表達了「不得體」之事;在這點上,一些原本沒有這種含義的字眼和措辭之所以變成那樣,同樣完全取決於人賦予它們的次要概念。一六八五年,當培爾不得不對耶穌會士曼布爾的著作《加爾文教義史》作出回應時,也重申同樣的論據。關於某些作者大膽說出侮辱的話,培爾表示「想要激動,用拉丁文比用通俗語言較不易受責備。」和法文比較起來,用拉丁文說侮辱的話較不會冒犯人。他以對照的方式繼續說道:
我們的語言已變得如此高尚,就連用法文發表解剖學演說的醫生,面對全場的男士聽眾,也會改用拉丁文表達很多事。這些醫生從學者的語言借來的詞彙,與他們不敢使用的法文詞彙意思相同,只是前者冒犯人的程度還是小於後者。
接著,他重申上述波爾羅亞爾的論文「邏輯或思考的藝術」,並從中引出結論:
……我們應有理由相信,用法文和用拉丁文講同一件事的兩人,後者比前者正經,因為他雖喚起自己避免用法文表示的事物概念,卻未喚起這些法文話被賦予的放肆無禮和缺乏尊重的概念。
因此,雖然「民族對高尚正經的重視已用於本世紀」,且阻止我們使用某些法語詞彙,我們還是可以用拉丁文述說同樣的事,而「不會顯示出我們藐視這個新禮節。我們並未賦予這個語言新的概念:社交禮節並未使這些措辭變得比昔日更不堪入耳、更粗俗。」只要使用拉丁文,作者就不會冒犯讀者或使對方產生不良企圖,而讀者也不會把作者想成放肆無恥的傢伙,反而會認為他是完全合乎當代社會標準的人;為此,眾人心照不宣的一個中立規約被拿來使用。
一五七八年,蒙特佩利爾醫學教授儒貝爾獻一本書給納瓦爾女王馬格麗特,標題是《醫學和養生法常見的錯誤》。雖然標題是這麼寫,內容主要卻是探討產科學。這點使它遭到很多醫生強烈譴責。他們責備這位同行把一本含有「所謂下流題材」的書,獻給一位「最貞節、高貴的女王侯」。他們指出「這一切用拉丁文比用法文合適」:其中一個理由是,「這些話用外語聽起來,不像用通俗語言那麼糟,而且會對這些話甚感羞恥的婦女和少女,過去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佛羅倫斯人科泰利尼出版《人體解剖學入門》時(Instituzioni dellanatomia del corpo 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