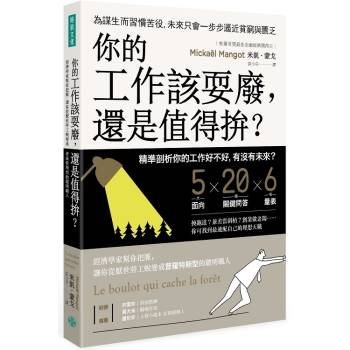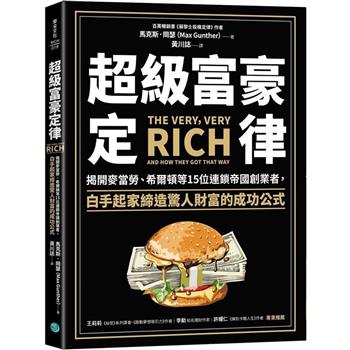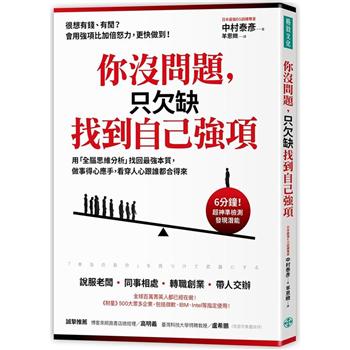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作家唯色出生於西藏軍區總醫院。當時她的父親是中國駐藏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也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透過鏡頭,這位軍官記錄了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影像。
「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少了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文革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這也是唯色父親所遺留下來的文革底片之所以意義重大的原因。
全書珍貴歷史圖片近三百幅,唯色帶著這些相片,花六年時光訪談七十餘位耆老,為的是還原歷史影像背後更深沉而真實的記憶與傷痛。她的散文集《名為西藏的詩》(原名《西藏筆記》)曾被中共官方認定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遭查禁,她同時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與文革時代依然如出一轍。這也使得唯色不再有所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發表本書。
傳統藏語並無「革命」一辭。半個多世紀前,中共解放軍進駐西藏,刻意結合原先藏文的「新」與「更換」才造出這一個全新的辭彙。藏語「革命」的漢語發音近似「殺劫」,恰恰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革命」為西藏帶來的種種劫難。
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席捲西藏。「殺劫」之前於是再被加上「文化」一辭。藏語的「文化」與漢語的「人類」發音近似。對西藏民族而言,這場「文化大革命」無疑成了「人類殺劫」。
作者簡介:
唯色(Woeser)
女,藏人。1966年出生于「文革」中的拉薩。籍貫為藏東康地的德格。1988年畢業於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曾長期在拉薩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2003年,因散文集《西藏筆記》(繁體版《名為西藏的詩》,大塊文化出版)的批判言論,被當局查禁,並限制出境。2006年,在中國大旗網、藏人文化網上的部落格被關閉。西方學者認為唯色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運用現代傳媒表達觀點的第一位藏人」。著有詩歌、散文等十多種選集,在中國多家出版社出版,並被譯為英文和法文。另有繁體版著作《殺?》《西藏記憶》(皆為大塊文化出版)等。現為自由作家。
章節試閱
「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中文拼音為Sha Jie,藏文為我我我我 。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辭彙。半個多世紀前,當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為「新」的 和原意為「更換」的 合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 )。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的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四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殺劫」之前被加上了 (文化)。 的發音,中文拼音為Ren Lei,與漢語的「人類」發音相近,所以用漢語表達藏語中的 (文化大革命)一詞,就成了對西藏民族而言的 「人類殺劫」。
序 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裡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文件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網際網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裡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覆傾聽他們的驚慄、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對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年整
「殺劫」是藏語「革命」的發音,中文拼音為Sha Jie,藏文為我我我我 。傳統藏語中從無這個辭彙。半個多世紀前,當共產黨的軍隊開進西藏,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詞,將原意為「新」的 和原意為「更換」的 合而為一,從此有了「革命」( )。據說這是因新時代的降臨而派生的無數新詞中,在翻譯上最為準確的一個。 (革命)在漢語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選擇的是「殺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的革命給西藏帶來的劫難。四十年前,又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捲西藏,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