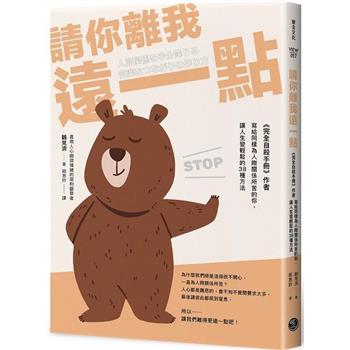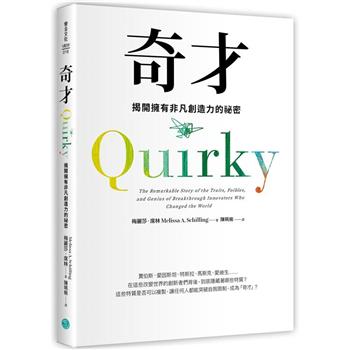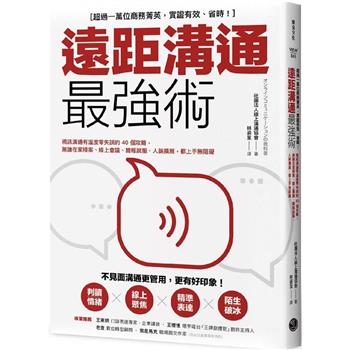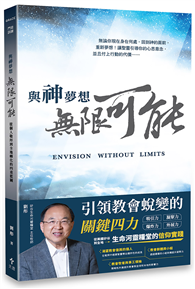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濁水溪畔二二八的圖書 |
 |
濁水溪畔二二八 作者:陳儀深計畫主持 出版社: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5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台灣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濁水溪畔二二八
本書是陳儀深教授接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委託,從2008年7月迄2009年1月所做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範圍包括雲林縣的斗六、古坑、北港、虎尾、林內,以及南投縣的竹山。重點事件是虎尾機場被攻佔,及衍生 出來的竹山青年陣亡、林內士紳出面講和(繳械)事件;以及陳篡地率領民軍退往古坑樟湖,在桶頭與整編21師 相戰,及所衍生來自北港、朴子民軍在古坑梅山交界被中國兵伏擊的事件。根據檔案,整編21師自認「樟湖之戰 」是台灣中部轉為安定的轉捩點,而陳篡地率領的民軍是在四月六日才被一四五旅四三四團驅散。這真是二二八 的最後一戰。本書做為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調查,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陳教授宣稱這是「以口述訪談作為 歷史研究的一次演練」,值得各界關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儀深計畫主持
- 出版社: 草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3-01 ISBN/ISSN:9789868510609
-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