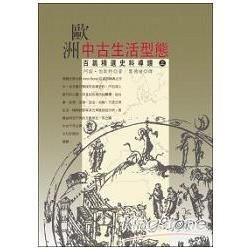前言 生活型態: 訴求 / 變異 / 推論
上卷 生存條件
第一章: 時間與經歷
光陰
剎那—— 從627年諾桑布里亞國王的猶豫皈依,看基督教的時代意涵
傾圮—— 從1341年佩托拉克的羅馬憶往,看文藝復興的歷史觀點
家庭
祖先—— 從643年羅塔瑞的倫巴第王室譜系,看政權背後的盤根錯節
子孫—— 從1343年瑞士鄉間的家庭竊案,看法律倫理的矛盾衝突
婦女
蹂躪—— 從12世紀西班牙的西得史詩,看貴族婦女的政治婚配
照拂—— 從1393年巴黎市民的治家格言,看夫妻生活的情愛真諦
少年
桀驁—— 從995年降世的歐拉夫成長歷程,看維京戰士的飛揚青春
乖順—— 從1064年出生的吉貝爾童年自傳,看宗教人士的養成教育
高潮
盛會—— 從1184年紅鬍子腓特烈的宮廷大會,看貴族雲集的隆重慶典
婚禮—— 從13世紀雷門史林的成親故事,看強盜群中的社交儀節
轉捩
暴富—— 從11世紀貧農安歐克斯的致富童話,看鄉間地位的競逐
守貧—— 從1173年里昂商人瓦爾德的散財濟貧,看城市秩序的動搖
死亡
天譴—— 從873年萊因河流域的年鑑,看疾病天災帶來的人心恐懼
瘟疫—— 從1350年薄伽丘的十日談,看黑死病造成的行為變異
追憶
令譽—— 從836年艾因哈特的傳記前言,看查理大帝的歷史定位
誹謗—— 從1490年科米涅的回憶記實,看勃艮第公爵的好大喜功
第二章: 空間與環境
空間
天堂—— 從10世紀撰寫的布蘭登傳奇,看西方極樂之島的仙境描繪
寰宇—— 從13/ 14世紀艾伯斯朵夫的祭壇壁畫,看中古的世界圖像
交通
遊學—— 從991年修士黎雪的尋書之旅,看交通運輸的困難險阻
朝聖—— 從1387年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看朝聖群眾的旅遊之樂
聚落
修院—— 從612年哥倫邦的修院興築,看原始莽林中的信仰據點
村莊—— 從1359年卡希米爾的功臣分封,看波蘭境內的墾殖政策
家宅
鄉愁—— 從7世紀倫巴第人的脫困返鄉,看凝聚家族的和平之境
蝸居—— 從16世紀初德意志的騎士城堡,看浪漫生活的幕後真相
飲食
歡宴—— 從911年聖.加倫的王者造訪,看禁欲修院的百年盛事
貪饞—— 從13世紀飲食方面的告誡警語,看暴飲暴食的社會背景
穿著
便服—— 從776年查理大帝的打獵行裝,看貴族治裝的奢華風尚
衣冠—— 從1260年法蘭西的朝臣口角,看優雅服飾的社會作用
自然
熊蹤—— 從6世紀熊隻牧羊的傳奇故事,看面對動物的矛盾情結
狐影—— 從12世紀法蘭西的《瑞那狐傳》,看人獸之間的生存抗爭
技術
鍛造—— 從8世紀英格蘭聚落的傳教受阻,看傳統鐵匠的惡魔形象
建築—— 從12世紀坎特伯里的巨大工程,看哥德教堂的鬼斧神工
第三章: 人群與社會
同類
詭詐—— 從6世紀克洛維的勢力擴張,看鬥智逞狠的王者天命
嘲諷—— 從13世紀義大利的軼聞趣事,看尖酸幽默的市民風格
個體
癲狂—— 從12世紀法蘭西的騎士小說,看心理危機下的自我放逐
思索—— 從15世紀尼德蘭的修道運動,看獨居斗室的靜思自得
聯盟
醫院—— 從1182年耶路撒冷的醫療武士團規章,看博愛理想的發揚
行會—— 從1389年英格蘭的裁縫師公會簡報,看互助精神的實踐
身分
領主—— 從837年貴族泰剛的排外論調,看出身層級的界線突破
僕役—— 從1381年英格蘭的農民起義,看經濟利益的持續對立
法律
異議—— 從1019年瑞典的人民大會,看安內攘外的集體議決
王法—— 從1231年西西里的法典編纂,看新式立法的理性訴求
民族
祖國—— 從1068年波希米亞的主教選舉,看尚在醞釀的民族情結
世仇—— 從1415年英法戰爭的懸殊武力,看民族之間的凶殘仇殺
語言
拉丁—— 從7世紀伊希多爾的語言研究,看歷史和社會的持續影響
方言—— 從1305年但丁的口語分析,看拉丁文與方言的各擅勝場
信徒
聖戰—— 從1095年首次十字軍的號召,看上帝子民的狂熱士氣
選舉—— 從1417年教宗選舉的過程,看基督教世界的彌合契機
(參考地圖46幅,中古圖像27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