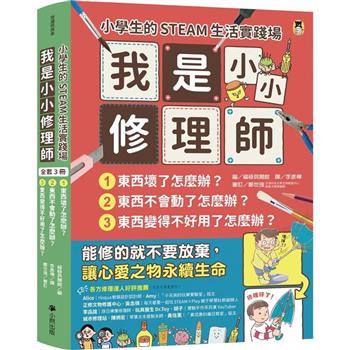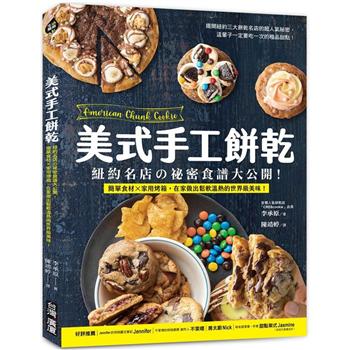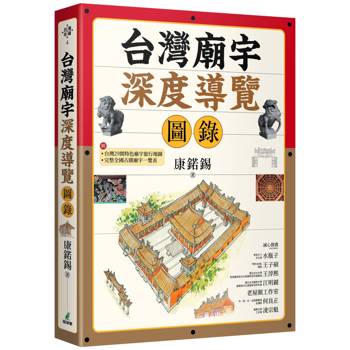《一些人》
1.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們相信
世界是一個偉大的商場
他們是良善的服務員
在門口中央,在資本中活命
偶然吃素,但大多傾向穩定
都是右撇子,會犯拿筷子的錯誤
他們愛好平和,週日顯得虔誠
儘管流浪者和動物
在外面無處容身。
2. 另一些人
另一些人追求無浪的海
到田野嚼食生活的真義
假期時用陶泥捏出原初的碗
但有時嚮往不過是一個抽象的詞語
他們也咒罵,養撿回來的貓
篤信理論和天秤
把世界暱稱成一頭溫柔的水牛
可制度確實充滿雜質
只好吟唱牧者的頌歌
他們仍在城市討食
整個下午都無法離開
3. 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人在邊防伐木
絕望磨成長矛,築起欄柵
讓宰豬的血濺滿路徑而無所畏懼
把雜交的蛋燉成另一個無眠的清晨
「報告長官
有人在邊陲種飼磚瓦」
與獵人們對峙時
他們用傢俱疊成堡壘
掏出筆桿和它尖利的頭
在轉角位置屏息
守著最後一道門,把鑰匙吞掉
就戰鬥,直至他們成為了一代人
4. 還有一些人
還有一些人總是滿腹懷疑
裝成理智而具哲思的先知
與所有人握手但從不脫下手套
不曾咒罵並保持微笑
也就是這樣了
他們習慣在潮湧的房間等待
否定門或窗之必要
漸成浮動的鰭
《發條》
後來,他們在罪犯的背裝上發條
手太短而無法觸摸疼痛
頹廢的午後在牆角栽種青苔
有貓在遠遠的窗跳開而我們仰望
一幅一幅陽光撕下後這裡只剩下沉默
他們說,要學習沙丁魚的姿態也要學習直線走路
有人往後退有人伸展四肢以換取獄卒
把背部結好的疤再一次用力整塊剝下,反覆如此致使
傷口紅腫發炎滲出膿水,潰爛
住在監獄我們的影子被剪下貼在牆上
哪處呻吟而哪處咆哮的聲音總是隔絕在
門欄和門欄間的距離中
在潮熱的日子無法抑止抽一支
用灰燼捲成的煙
獄卒提槍微笑而不聽話的犯人喜歡在他面前
脫下衣服以及內褲瘋狂做愛
被抓起處決,跪在地上他們在眼裡悄悄藏起天空
獄卒又開始微笑於是
剩下的只好開始玩球跑步,動作一致而規矩
沒有異樣的總能得到一隻盛在狗盆裡的雞翼
總是怒喊因此我們瘦骨嶙峋
起風的那天我爬上鐵網終於
看到天空,計量好高度便縱身
而他們仍在討論關於發條失靈的問題
《到資料館》
跟其他任何日子相同的早上
快要十一時了,原爆資料館裡
一群白人擁簇像車禍旁觀的途人
導遊的英語與紀錄片中的日語交雜
都被嬰兒哭啼聲蓋過
十一時零二分,死之閃光
「發生了甚麼事?到處都起火了!」
被削去上帝的浦上天主堂
人們收集斑斕的彩色碎片,閃閃如金平糖
註述:溶解的念珠像粘甜的水果糖塊
孩子在教堂旁與母親一同死去
他的臉是黑色的
女孩的飯盒裡有焦黑的米
父親回到家裡,只剩下血紅的石頭
還有女子,從一個地方逃亡到另一個地方
口袋裡還放有脆薄的紙幣
液化的瓶子、肥皂、錢幣。液化
而扭曲地依存時間依存成達利的鐘
而死者寄生於平面上,留下影子
(一位茫然而不知所措的女子
呆立在燒焦的屍體旁)相片描述如是說
我茫然而不知所措呆立在鑲好的照片旁
但我還是偏激而難過地
看著如常的人喝咖啡,買明信片
無法相信彩色的千羽鶴串
卻也不知應當相信甚麼
《生活》
他一直夢見女兒,在遠方
燒開水的手總是太小
照顧祖父褲子又濕了一腿
臉色蒼白,彷彿在火車站送別他時
負不起他的行李箱,又如他的心情
就揉她的頭說,乖
火車駛進城市的血管
把他的影子撕成兩半
一半在家鄉
一半在車廂
他在城市的海中擱淺,船隻沉沒
所有履歷表一再成為回力鏢,擊傷額頭
總是來不及射死一個工作職位就有別人跑得更快
又有鳥兒飛過,定是南歸
而他只能在馬路和馬路間步履不穩
迷路,成為預設的罐頭或是螞蟻
派傳單和紙巾,有時是眼鏡,有時是指甲
只能把所有躁動折合成小小的打火機
抽一根無望的煙
又想起女兒,在遠方
赤著足賣火柴
未癒的咳嗽綿長不斷,醫生呢是
不能看的。樓下茶餐廳新聞說今天全年最熱
37℃他住籠屋,躺在鐵板上
一如童年阿母帶他去餐廳,點豬扒鐵板餐,伴燒汁
送來時冒出一個又一個像星星的爆花
便開始估計自己背上正爆著多少朵花
一枚紫荊花硬幣滾落
他的廣東話仍未純熟
便在夢中繼續有狼跨過欄杆
把他撕成兩半
一半在這裡
一半在那裡
《狗》
狗開始死去,有的病死,有的交通意外,屍體橫陳於市。人們吃狗的肉,廉價粗糙的肉,勝在廉價。狗知道,從牠爬不上月台一瞬開始,牠就得死。穿著工作服的女子說:「列車總是只會往前走的。」
人們為狗憑弔,但把狗的屍體棄於荒野。也有些人,開始咬別的人,嘶吼而叫。狗則在籠中,每天等待糧食,牠們乖巧,從來不吠。當又有一隻狗被亂棍擊斃,便又有另一個人被推下月台。
《在最大風的日子買一個氣球吊死自己》
顛簸的頻率滲滿車廂
最近窗的座位總有一絲救贖
適合垂死掙扎的人
你說我們都是乘著同一班車的囚犯
彷彿一出生就無從卸下
為了推翻這點,你一下車就嘔吐
站在灰色的人流中央,彷徨無助
經過沒有船的碼頭
只剩下一個沉在海底的垃圾筒,長滿青苔
側臥總是意味缺乏安全感。你說
便想起你睡覺時習慣吮吸拇指(我的或你的)
一如那個人們釘死蝴蝶的晚上
有一隻躲到你眼瞼上,彷徨不安
終於走到花市入口,猶豫不決
要學習穩定走路,模仿大多數人的姿勢以及歡笑
嘗試牽手燃燒出賣的勇氣
竭力提醒自己黑布蒙眼之必要
閉上眼,野獸總應該踏回牢籠
買了兩個氣球,黃色的還有白色
你談起那個討論自殺的週末
否決溺斃否決臥軌否決服藥
我們害怕仍要在焦灼的陽光下等待
不如
在最大風的日子買一個氣球
吊死自己
耳語過後我們只能放手
偷去風信子的氣味後
我們登上與目的地背向的列車
暗自默許彼此老是上錯車的壞習慣
待列車潛進城市的隙縫後,便入睡
《標本——給自殺者》
在成為難看的繭以前
他們還是逐一墜下於燈前
春日的霧讓一切都無法安定
只能仰賴於光
「但也不過是一些溺水的孑孓。」
如常明媚的午後一個女子如常說道
城市沒有給予足夠的
為死亡而悲傷的額量
霧一直沒有散去,換季的渺渺
餘下的人欠缺提示奔行
而我們脆弱的定位,雜音及光
在來回丟失班次的月台上
遠方總是長滿青苔
遁入隧道後
我們來設想一個
再無歉意和羞愧的黃昏
井然安坐於尚未明亮的房間
透過撫觸漸然習得生活的紋
醒來後
我們將是良好的標本
2 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
浪潮浸沒了海島最易尷尬的部位
海島披上沙灘,一排排
押韻的浪在呼吸岸
在失眠,在整理髮綹上花瓣的奶白彷彿
正在悼念昨晚
沒有如期浮現的夢境:
今夜我們就再次一同倚傍不同
但相似的玻璃窗
交換因為時差所延續彼此的嘆息;我們
已經換上不稱身的軀體,不可能蜻蜓般
低飛於湖上,不可能預測甚麼:
你是猜不透的謎語
在濛濛雨的日子,你是我不願猜透的謎語。
水平線不曾因為我的潛藏而上升
你躺在自己的身上,尋找
空中的白象和馬。
然而辛勞的人
已經陸續以各式的輪子把光運走
動物早已逃往市郊漆黑的天空
默默地牠們流淚、絕種,而我們
苦無對策
撐著傘子免受新一輪的感染
—— 而我確信
有些門能通往海
以一股孤獨在魚缸中找尋共類者
嘴巴永遠朝向你
張開
張開
但永遠無法超越長滿窗口的青苔
3 你說這是無可解譯的遠古寓言
候鳥回來
便無需離開了,羽毛
織造出交曡的林蔭
你整裝待發
每天穿梭其中
秘密地採摘光合作用
白堊紀被重新繁殖
海洋收集更遼闊的海洋
水平線因為你偶爾的哀傷
加倍綻放更多誤時的菊石
而到了那個無可趕上的時刻
涼風送往白紙上依然濕潤的螺殼
讓無奈感埋藏於那碩大的比喻裡
你說這就是無可解譯的寓言
僅能停駐於一種來自沙的遠古語言之中
那些成長中的觸鬚
依舊搔癢著每串沈默的島嶼
海港有船駛過、有船靠岸
後山的碉堡將不再孤獨
你還是好好的
冷靜地把一行行的密碼傳與戰友。
這刻,你又想像
野兔如何能夠在天上跳動出更多的童話
烏龜如何比自己
競跑得更快
5 我所認識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
走到帳篷中央,哄
一頭愛上說謊的大象
不然就把記憶棄置於獅子的口腔裡
把出走的路線圖託與
獨輪車,以及善於塗改憂愁的小丑
然後我們就於黑箱作業
恣意地咬破乾燥的下唇
執行安排已久的秘密任務譬如
剖析胸膛底下失控的心跳
又譬如勘察一行行眼淚的流向
馴獸師以未竟的時間賄賂一本日記
那些雨季的斜線重讀你
沒有被日子淋溼的衣肩
可是我們太愛迷途的拖鞋
在危機四伏的都市,撿拾彼此拋擲過的利器
然後悄悄地我們又爬回各自的樹洞做厭世的事
把秘密鎖在房間讓潮濕的影子發霉
我們定時按電話上的重撥鍵直到它
己不能夠承諾接通另一位悲情的角色
今夜無風
在高台上我們量度我們之間的時間和眼神
就像那位我所認識
卻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
專注地交換每一棒
極棒的心跳
8 如染上一種遺傳病
終於
能夠
帶你到沙灘撿拾時間的樣本
是星光的歷練 X P
黑夜恆久
除非你還孤泣於
不守時的辦公桌,試圖守時
你中年的手心,染上這刻滑行的窗
如染上一種遺傳病
低頭,哈欠,一句句嘆息
一句恥笑 ^^
× 2
快樂和痛皆單純
凝聚於掀動的手指和手槍
我知道
但不解釋
你便定時但怠倦地
更換鋪在慣睡的床上的
那匹馬虎的床~
單
9 夢以黑暗統治它們自己
這個城市再沒有能夠令人無法平靜下來的秘密了
螢幕上的立體谷歌地圖,呈現一種
現實仿效歷史現實的現實狀況
譬如,汽車約以時速卌二公里凝結
在馬路上,彌漫一種目光穿透
玻璃窗的呆視神情。
車外的景物,水般橫渡
我們的腦袋只能微晃
從未能夠有實質的前行
畢竟探訪位於中央伺服器的路已被堵住
面貌模糊的我們
不能夠再辨別那位坐在行人道上的青年是否
多年前的我
我們唯有依賴衣服的顏色
作出一個初步結論 —— 他究竟在說甚麼呢?
除了夜這件越穿越冷的隱身大衣
所有蓋著棉被的人已經光明
入睡,秘密做夢:一處
我們艱辛地醒來之後就
幾乎會把所有情節都忘掉
的地方。正如
手的影子,夢永遠無法掌握甚麼了
它只是光源之下對手的模仿,又或者
它只是手本身自我性格的投射:
漆黑而無法穿越
於是小孩都願意住進那個地方
想像雙手是牆壁上不留痕跡自由的鳥
或忠實的狗或
或圍困於動物園的大笨象:
一個個童話故事因此而被虛構
在這個城市的晚上
然而夜是星光的墳墓啊!
來自數十光年以外的繁華
寂然於晨光中消失
因此他們的笑容被埋葬於影子的隊伍中
他們背著一個個能了解未來的解譯
而我們則偶爾潛回逝去的歲月
悄悄行走、悄悄
弔唁那些最輕易發生但沒有發生的結局
來自遺憾的快感慢慢
滲進我們的心臟裡
直到它,再沒有足夠空間讓
我們馴服地呼吸
是的,一陣來自世界的胸膛的雨
總會於這類運動過後發生作用 ——
雨水朝著英雄的方向
灑,彷彿決鬥
注定需要在泥沼中發生
而當一個人倒下,另一個
永遠無法逃離那個競技場
猶如影子,儘管那隻不留痕跡自由的鳥
已經長大,牠永遠不會離開你
除非你把所有燈火都熄滅
以黑暗
統治它們自己
患有眼疾的人
因為能在人海中被無法想像之物事
推撞而獲得方向
在浪花中從善而流彷彿
周遭皆不存在惡念
所有妖邪都有致地躲在寺廟的晨鐘裡
於黑夜過後被釋放到街頭
但相比之下,你是那位
活在舒適下的受害者
從小,發聲是如此簡單直接的事
媽媽告訴你
那些眼淚沒有無奈
沒有耿耿於懷,它們
是夏天的雷雨
落地就會有新的樹苗長出來
而我們大概都能夠把整個世界收藏
於鏡子裡,除了眼睛背後
那一平方尺左右
最懂得淹沒稱之為腦海的地方
22 張開眼你和我一同消失
沒甚麼
比物件所呈現的象徵性更加充滿危機,
他因為一朵花所包含的意思
被驅逐,房間
希望把秘密上鎖所以她在門上
掛上玫瑰;一朵紅色的玫瑰
因為愛,死於剪刀然後被插在
營養的水份中
再死一次。
於是在夢裡我無法
入睡,閉上眼睛
只是為了再見你一眼,而張開眼
我們便一同消失。今早
我依舊順利地成長以慢慢投往衰老。
雪悄悄的落下卻很快再被清理,
堆到路邊做新一輪冬季的勘察者:
我們皆等待機會,做點
預料之中的事,尤其在晚上
一個不應該有第三者的地方
遇上你,然而它不是陽光穿透雨點的時刻
沒有短暫的虹彩。
也許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讓春陰作出
適當的彌漫,需要更多低沈的弦樂
以凸顯一種重生的主題。可是
我們只是純粹的雨點
著地後就失去名字。又或者
我們從來都不怎麼重要,
擁抱的時候,天已放晴。
但花的死亡不代表我將哭泣啊
我坐在你家門外,觀察行人
與行人之間的芒刺,是甚麼時候
我們開始害怕擁抱彼此:
彷彿擁抱將導致摩擦;摩擦
將帶來閃電般的破壞力 ——
如果我們是唯一站在平原的一對,
沒有樹、沒有傳說中
張揚的長頸鹿和長毛象。
的確,這時候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藏身的洞穴
又或者是一顆旋螺,讓我在岸邊的石縫
寄居蟹般橫行於其中。
如一首沒有堅持
把自己豎排的現代詩在
紙張上,
從左至右緩緩駛過,
偶爾因為紅色的交通燈而煞車停下
讓一群正趕回家全身濕透的學生
橫過斑馬線,小心翼翼不被打擾。
黃昏過後,受傷的天空開始復原。
黑夜閃著沒有走慌的星光,
它不再是一面長有雙臂的時鐘:
需要睡覺便睡覺了
如果
明天是能讓你休息的星期天,
如果她也睡在你的旁邊。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雜音標本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雜音標本
年青詩人梁莉姿首本詩集《雜音標本》於上月(2017年7月)出版,得樊善標、關夢南和曾淦賢撰文作序言和後記,及畫家梁嘉賢以插畫故事來貫穿全集。詩集於香港書展舉辦的簽售會反應熱烈,足見作者也有不少fans。
作者簡介:
梁莉姿筆名白懿,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四年級,寫詩、小說、散文和評論,「關於詩社」成員。中學時期開始投稿,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城市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獎等。作品散見於《字花》、《聲韻詩刊》、《大頭菜》等,2014年出版首部小說集《住在安全島上的人》。
TOP
章節試閱
《一些人》
1.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們相信
世界是一個偉大的商場
他們是良善的服務員
在門口中央,在資本中活命
偶然吃素,但大多傾向穩定
都是右撇子,會犯拿筷子的錯誤
他們愛好平和,週日顯得虔誠
儘管流浪者和動物
在外面無處容身。
2. 另一些人
另一些人追求無浪的海
到田野嚼食生活的真義
假期時用陶泥捏出原初的碗
但有時嚮往不過是一個抽象的詞語
他們也咒罵,養撿回來的貓
篤信理論和天秤
把世界暱稱成一頭溫柔的水牛
可制度確實充滿雜質
只好吟唱牧者的頌歌
他們仍在城市討食
整個下午都無法離開
3. 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
1.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們相信
世界是一個偉大的商場
他們是良善的服務員
在門口中央,在資本中活命
偶然吃素,但大多傾向穩定
都是右撇子,會犯拿筷子的錯誤
他們愛好平和,週日顯得虔誠
儘管流浪者和動物
在外面無處容身。
2. 另一些人
另一些人追求無浪的海
到田野嚼食生活的真義
假期時用陶泥捏出原初的碗
但有時嚮往不過是一個抽象的詞語
他們也咒罵,養撿回來的貓
篤信理論和天秤
把世界暱稱成一頭溫柔的水牛
可制度確實充滿雜質
只好吟唱牧者的頌歌
他們仍在城市討食
整個下午都無法離開
3. 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序(一)雜音與雜草—樊善標
最初知道梁莉姿這個名字,大概是在2011年關夢南先生熱情鼓勵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幾位得主的文章裡,但真正留下印象的,是兩年後《明報》的訪問記。那時梁莉姿是當屆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她說升學目標是中大中文系。我一向認為創作只是中文系課業的一環,很擔心一往無前的文學少年期望愈大失望愈大。就在讀到訪問記後不久,竟收到她的電郵,請求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中學生文學夏令營破格錄取她,因為這一年後,她就不符資格了,信中好像還說這個夏令營對她「絕對」重要云云。這更加深了我的憂慮,結果當然是提早讓她...
最初知道梁莉姿這個名字,大概是在2011年關夢南先生熱情鼓勵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幾位得主的文章裡,但真正留下印象的,是兩年後《明報》的訪問記。那時梁莉姿是當屆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她說升學目標是中大中文系。我一向認為創作只是中文系課業的一環,很擔心一往無前的文學少年期望愈大失望愈大。就在讀到訪問記後不久,竟收到她的電郵,請求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中學生文學夏令營破格錄取她,因為這一年後,她就不符資格了,信中好像還說這個夏令營對她「絕對」重要云云。這更加深了我的憂慮,結果當然是提早讓她...
»看全部
TOP
目錄
輯一:但言語總是貧瘠如凸起的背骨
有一些人
她——給K
末日
投擲
發條
Boredom
星期五
輯二:Music is the first world problem
給外婆
給外婆(二)
古巴早餐
到資料館
Music is the first world problem
生活
狗
石頭
落點
燕子巢
輯三:因為無法成為鳥
沮喪
經過
親愛的
無題(一)
無題(二)
無題(三)
你們都優秀哀傷
碼頭
逐一
馬戲班
應該,或是無可避免
好看
彷彿一切都是那天開始壞掉的
輯四:我仍在反覆經過自己
在最大風的日子買一個氣球吊死自己
我們只能在窗裡窒息
這種天氣我像輕微溺水的病人
在十號風球的深夜煮...
有一些人
她——給K
末日
投擲
發條
Boredom
星期五
輯二:Music is the first world problem
給外婆
給外婆(二)
古巴早餐
到資料館
Music is the first world problem
生活
狗
石頭
落點
燕子巢
輯三:因為無法成為鳥
沮喪
經過
親愛的
無題(一)
無題(二)
無題(三)
你們都優秀哀傷
碼頭
逐一
馬戲班
應該,或是無可避免
好看
彷彿一切都是那天開始壞掉的
輯四:我仍在反覆經過自己
在最大風的日子買一個氣球吊死自己
我們只能在窗裡窒息
這種天氣我像輕微溺水的病人
在十號風球的深夜煮...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梁莉姿
- 出版社: 石磬文化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ISSN:978988142529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14.8*21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