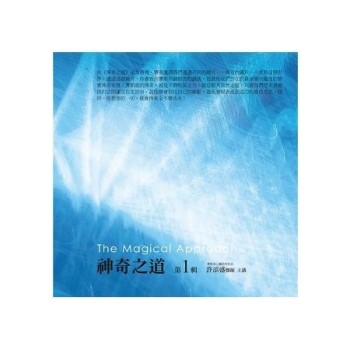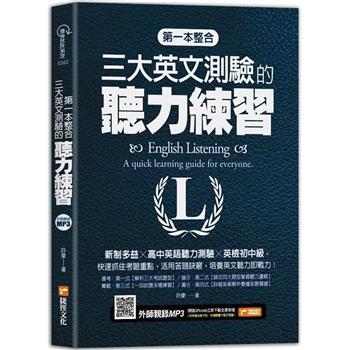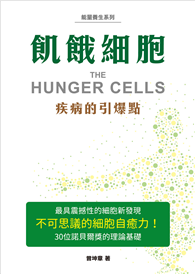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遙念吾師徐復觀
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提及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老師個子不高,不胖不瘦。……外形上,他沒有錢穆的儒雅,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言談上,沒有徐復觀的威儀,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
「新亞」諸師之中,徐復觀是影響筆者最深的授業師,而他在外形言談上常常予人威儀抑抑,震懾人心的感覺。
余生雖晚,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而當中的徐師,於筆者而言,倒是真的尾班車。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既屬有緣,更感有幸。
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徐師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他敢言敢罵的性格、激濁揚清的言論,我等後輩,當然多有知聞。及後在所期間,立雪徐門,親聆教誨,感受益深。
那一年徐師在所開了一科「《文心雕龍》」。論科目,在研究所講論劉勰的《文心雕龍》,倒沒有什麼很特別;最特別之處,是課堂不設於校內,而是老師的住所。
順帶一提,當年在所期間,筆者遇到三位光是上課的做法方面已叫筆者感動萬分的老師。其一是前文提到的汪經昌老師,他身患眼疾,視力不佳但仍堅持摸着路旁外牆回校授課;其二是王韶生老師,他教務繁忙,須於珠海書院任教,以致無暇回校授課,但仍歡迎「新亞」學生逕自跑去「珠海」,以便他乘隙晤談講授;其三是身罹絕症仍堅持登壇授課的徐復觀老師。
他們那種忘我無私,誨人不倦,但教一息尚存仍忠於教職的精神,確實帶給後輩很大激勵。
筆者雖自愧粗疏,但時刻秉持列位先師的精神,在此花甲之年,仍樂意與後進分享各式課題。
年邁體弱 堅守崗位
徐師開「《文心雕龍》」時,已經動完胃癌手術,在家休養。我們幾位同學按時前往徐師位於美孚新邨的寓所,在客廳裏敬聆教澤。每次開講之前,只見師母王世高夫人端上一杯熱牛奶給老師潤口補充。徐師鑑於自己手術後形神俱損、血氣不佳以致聲柔語弱,於是備有一塊小白板。每當我們面露疑惑,他就在那小白板寫上幾個關鍵字。親睹這位歲暮體弱的學者仍然堅守崗位以夕陽餘暉光照學子,怎不崇敬萬分?
他所授科目,雖然名為「《文心雕龍》」,但回顧整年的課堂,直接與《文心雕龍》有關的內容,他倒沒說太多。今天看來,這種情況可能視為偷工減料,有虧職守。其實絕非如此。
記得月前在「憶吾師汪經昌」拙文提過:「幾十年前的研究所,教學模式與今天很不相同。老師絕少在課堂上教授相關知識,因為他們都認為,我們身為研究生,理應具備相關知識,即便缺乏知識,也應自行翻閱書本。他們在課堂大都集中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
教導我們 治學法則
他在課堂上花了很多時間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他深信,只要好好掌握法則,不論從事任何研究,哪管讀什麼書,定必手到拈來,了無畏懼。因此,在所期間的莫大得益,是學懂掌握治學法則。他日不管碰到任何課題,也從容自若,明辨肌理,識分主次。
徐師與汪師授課,明顯有別:汪師只管自話自說,徐師卻愛「問書」,往往話至中途,就稍予停頓,轉而詰問學生。
不過,當年的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課堂上整班學生都是同級同輩,則可自由隨意回答老師提問。如果學生之間有長幼之別,例如筆者在徐師的課堂上屬於小師弟一輩,則回答問題的「重責」,例必落在大師哥身上。
斬釘截鐵 一字以決
本來老師提問,學生答錯,又或答得未如理想,實屬平常。畢竟是學生嘛,犯錯乃所應當,老師何須苛責?不過,上徐師的課,情況可不一樣。
首先說明,徐師雖愛罵人,而且罵人無數,但記憶所及,他對於晚輩後學,從不責罵。不過,他那種斬釘截鐵,一字以決的回應,倒叫人不寒而慄,沮喪半天。
很多時候,真的很替扛肩回答之責的大師兄難受。眼看他一句回話還沒說完,而往往只說了半句,徐師即以柔弱但決絕的語氣說:「錯!」當時筆者年少,而且慣受西方教學法(在所期間,同學都譏笑筆者是「番書仔」,蓋因筆者進所之前,主修西洋文學),西方老師縱使聽到學生荒誕離奇、匪夷所思的答案,而即使班上同學哄堂大笑,老師只會微笑回答:Nice try 或 It's very interesting。然後才以開放式回應:「但你有沒有想過……」;又或:「我們不妨從這方面想想……」哪有學生話未說完,就被老師斷然否定?
止步轉向 以矯錯誤
當時筆者年少,既缺學養,亦乏歷練,只覺得徐師有點霸道,對學生不夠體恤。然而,當自己踏入知命之年,赫然發覺,不管在公職上提示下級,抑或在藝術上啟導後輩,也步了徐師後塵,每每聽到對方明顯錯誤的回答,便斷然說:「錯!」
原來,當自己真確知道對方是概念出 錯,即 conceptually wrong,或錯於方向,我們便會斷然說「錯!」至於那些不涉對錯的課題,則不在此限。
打個比方,如果你站在中環,本想去柴灣,但偏偏上了去堅尼地城的車,不管你坐了多少個站,你仍是錯了方向,只有回頭轉向才可抵達目的地。治學之事,也是一樣,萬一錯了方向,就必須止步轉向。
擔心後輩 積錯難返
當然,做學問功夫,你必須在概念上掌握透徹,方可決斷如徐師。何況當年的徐師,已處於生命盡頭,而沒多久便離世,他那種焦急決斷,惟恐後輩積錯難返的心情,我們必須體諒。
徐師身為一代大儒,學問既淵且博;但他的道路,與別不同。一般學者,都是自年輕開始,便一邊教學,一邊著述。反觀他早年從事軍政,做過軍隊文官,而官拜少將;後來棄官從學,設帳授徒,埋首寫作。
徐師弟子眾多,港、台均有,但數目上當以台灣較多。關於徐師生平,網上資料頗多,茲不贅。
著作等身 種類繁多
徐師除教學外,亦勤於寫作,既有專論,亦有雜文,堪稱著作等身。單以筆者手執早年刊於台灣的書籍而言,可以粗分為幾大類。
其一,思想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公孫龍子講疏》、七十年代的《兩漢思想史》(卷一至卷三)(當中的卷一原稱《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
其二,藝術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藝術精神》、七十年代的《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其三,經學論著;即八十年代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其四,雜文類,多收於九十年代的《徐復觀文存》(此《文存》收錄早已絕版的一套四冊《徐復觀文錄》內的所有文章但不包括《徐復觀文錄選粹》已予收錄者);以及
其五,家書類,即收錄六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精選》,以及收錄七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集》。前者由學長曹永洋編校;後者由曹學長連同黎漢基編校。
以上僅屬坊間可以買到的徐師著作,至於其他例如五十年代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兩集)、六十年代的《石濤之一研究》、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續篇》等書,不是絕版,就是難在坊間找到。
徐師著作,絕大部分由學生書局印行,只有少數例外,比如《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及《徐復觀家書集》,則分別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專刊」印行。
內地重輯 另自刊行
另一方面,內地不同出版社亦將徐師的部分文章,重新輯錄,另自刊行,例如《遊心太玄》、《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中國人的生命精神》、《中國學術精神》,而其內的文章,大都取自《徐復觀文存》及《徐復觀文錄選粹》;還有最後期的《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
順帶一提,曹永洋學長於徐師逝世後向各界廣集鴻文,編成《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於一九八四年由台灣時報書系印行。書內集得文章近百篇,全由學林友好及晚輩後進提筆紀念。
其實,不論你對哪門學問有興趣,只要撿起徐師任何一本論著,都可從書內所展現的學術精神及治學態度而有所感悟,深得裨益。
捧讀徐書 自有別趣
再者,捧讀徐書,自有別趣。
趣?徐師選題嚴肅,治學惟謹,行文認真,何以言趣?敢問趣從何來?
原來他愛在文裏罵人。提起徐師,當年整個學術界都知道,他最愛罵人,而且是誰人都罵。哪怕你是誰,只要你在他眼中有任何重大缺失,他都罵。當年掌權者及政界強人,他敢罵;文化名人,他當然罵;教授專家,他固然罵;學界翹楚,他更罵,而且每罵必狠。
徐師罵人的方式,當然不像一般潑婦莽夫,而是依據學術常識,發文質疑對方,令致被罵者語塞詞窮,無法應對,只有捱罵的份兒;又或轉以攻訐,圖求解窘。每讀及此,頓覺有趣。
有人認為他罵人罵得過於辛辣;有人認為他十分難纏。其實,只消靜心分析,就知他罵必有理,伐必有因。比方說,他罵紅學專家潘重規,是因為他認定潘重規研究方法欠通,痛惜他誤人子弟。他罵胡適學問根基不穩,出言欠缺客觀理據,是因為胡適既然貴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執掌最高學術組織,位高名大,如果言而無據,焉能為學林表率?
胡適學問 備受質疑
提起徐師痛罵胡適,倒是當年學林逸事,蓋因胡適恍惚是徐師恆常痛罵的對象。徐師在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性論史》初版的序言,就向胡適發炮:「胡適認為《尚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按:引自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這大概不是常識所能承認的。」(頁三)
換言之,胡適不是學術研判出錯,而是違背常識,也即是今天所謂「犯了低級錯誤」。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是學術界最高代表,他的言論居然被人謾罵違背常識,而偏偏確實違背常識,忒也有趣。
徐師為說明對方何以違背常識,在序裏繼而指出:「對於馮友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的說法及胡適『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的說法(按:前者引自馮著《中國哲學史》;後者引自胡著《淮南王書》的手稿本),都完全不能了解。」(頁三)
把人家的說法,形容為「完全不能了解」,只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對方學說高深,自己卻才疏學淺,以致無從理解;其二是對方論之缺據,言之無理,以致不能了解,而且是「完全不能了解。」
違背常識 治學不嚴
徐師此間所言,當然是指後者。按照一般情況,如果某學者認為對方立論不確,頂多贈以一句「值得商榷」或「未敢苟同」;至於反駁或詰問對方,也例必冠以「討教」、「請指正」的字眼。怎會像徐師直言「完全不能了解」?小孩年幼胡言,我們尚可用「完全不能了解」評之,但若以此評論黌舍翹楚,學界大儒,則等同謾罵。
不過,徐師絕非只管罵人而不講道理。他在文內隨即指出「我國古代思想中的《詩》、《書》、《禮》、《樂》、仁、義、禮、知、忠、孝、信等,在道家思想中並未加以肯定,而道家以虛、無為體的思想,亦為道家以前所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則胡氏的所謂『集大成』,到底作何解釋呢?」(頁三)短短數言,簡單一詰,即證胡適的確犯了低級錯誤。
印象中,胡適是徐師罵得最多,亦罵得最狠的學術領袖。無他,胡適違背常識。看他當年為急於提倡白話文而竟然違背常識,鼓勵中文走向晚清詩人黃遵憲所言的「我手寫我口」的低劣境地,就足以給社會痛罵一生。須知某民族的文字(書面語)與語言(口頭語)相差越遠,其文化涵養就越深厚。我們當然理解,胡適當時所處身的國家,亟須破舊立新,但急於扔掉傳統包袱的當兒,總不能提倡這種「口手如一」的荒謬言論。至於他當年提出的《改良文學芻議》,也即時人所稱的「八不主義」,當中多項違反常理,因而惹來批評,招致詬病。由於此事知者極多,於此不贅。
再者,胡適從來治學欠認真,考證不嚴謹,以致他的學問功夫,備受質疑。何況,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地位至高,而居然常犯一如前述的「低級錯誤」,因此在徐師眼中,絕對該罵,怪你不知身分,誤導蒼生。
胡適卻成 悲劇書生
徐師雖然長期痛罵胡適,但在一九六二年當知道這位「中研院」院長遽然辭世,便立刻停罵,反而以「一位偉大書生的悲劇」為題,撰文悼念這位自由民主的追求者。
文章首段書明:「剛才從廣播中,知道胡適之先生,已於今日……突然逝世,數月來與他在文化上的爭論,立刻轉變為無限哀悼之情。」(按:依照學林規矩以至社會倫理,你儘可抨擊某位在世的人,甚至謾罵。然而,當他離世,就必須停口,皆因對方已經沒有能力「回敬」你。如果你仍舊抨擊對方,人家就視你為缺德;你的評語,只會換來鄙夷。當然,如果你以客觀法則評論死者的學術論著,則屬另一回事。)
文內第二段隨即說明胡適是「悲劇性的書生」:「胡先生二十多歲,已負天下大名。爾後四十多年,始終能維持他的清望於不墜。……他是這一時代中最幸運的書生。但是從某一方面說,他依然是一個悲劇性的書生。……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尊重胡適 追求民主
徐師隨後稱許胡適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於胡先生的學問,雖有微辭(按:「微辭」是客套話;口誅筆伐才是實情);於胡先生對文化的態度,雖有責難;但一貫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我雖然有時覺得以他的地位,應當追求得更勇敢一點;但他在自由民主之前,從沒有變過節,也不像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為了一時的目的,以枉尺直尋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些手段。……他回到臺灣以後,表面是熱鬧,但他內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書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沒有兩樣。」
文章下半部簡評胡適畢生的光景:「我常想,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却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臺灣,則既無兵,又無將;即是既無青年,又無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對現實的;……我曾寫文章,強調自由民主,是超學術上的是非的;所以主張大家不應以學術的是非爭論,影響到自由民主的團結。」
無法自遏 不評胡適
徐師隨後敘述他如何無法遏止自己批評胡適:「我曾很天真的試圖說服胡先生,今日在臺灣,不必在學術的異同上計錙銖,計恩怨;應當從民主自由上來一個團結運動。我自己曾多少次抑制自己,希望不要與胡先生發生文化上的爭論;……但結果,在文化問題上,依然由我對他作了一次嚴酷的譴責,這實在是萬分的不幸。」
從徐師的剖白得知,他深感矛盾,在自由民主的團結這個大前提下,他強抑批評對方的心,可惜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在文化議題上嚴酷譴責對方。
其實,單以這篇悼念文章而言,徐師雖然凛遵倫理,敬守禮數,沒有半字狠批對方,但可從上述引文看到他對胡適的終生評價。
首先,他稱對方為「書生」,即便冠以「偉大」二字,也只不是個書生,並不是成就非凡而足可在「中研院」院長這高位上領導群儒的學者。
再者,文內絕對沒有像一般悼文,頌揚死者的學術成就,更沒表彰他對後世的貢獻,而只「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過,徐師一邊說尊重,一邊卻惋惜對方處身在那個時代而沒有憑藉自己崇高地位而「追求得更勇敢一點」,致令自己成為悲劇書生。徐師此番蓋棺論定,昭然可見。
到了文末,徐師有感於胡適這位書生逝世而心生宏願:「我常想到,生在歷史專制時代的少數書生,他們的艱苦,他們內心的委曲,必有千百倍於我們;所以我對這少數書生,在他們的環境中,依然能吐露出從良心血性裡湧出的真話,傳給我們,總不禁激起一番感動,而不忍隨便加以抹煞。……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的良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的徹底結束。」(此文見於《徐復觀雜文》,亦刊於《中國人的生命精神》)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學林踽樂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學林踽樂
作者二零一六年退休之初,應某報館誠邀,為其「人文歷史」專刊撰寫文章,題目任定。三年下來,合共寫了三幾十篇;每篇簡介一位大都是作者少年即中四至中七期間開始認識的文史名家。
當時為專刊撰文,礙於篇幅,每版連插圖以及間或有三幾百字的配稿在內,只可約載四五千字。以此字數簡介名家,當然難求稱心順遂。
過去兩年,作者經不起各方敦促,認為不把這些文章編輯成書,根本愧對列位先師,更有負學子所為,只得奮起精神,重新檢視,並酌增原文,補述不可或缺的資料。
為方便翻閱,本輯文章特意分成兩部分,其一是「新亞學者系列」,專敘當年新亞研究所列位恩師;其二是「二十世紀文史名家系列」,介紹兩岸三地文史翹楚。年前為了拓闊報館「人文歷史」專刊的範疇,間或敘及西方名家。
書內有所提述的名家,儘管享譽學林,但按作者多年觀察,未必位位堪稱楷模;當中有些反而大有商榷之處。凡此觀察,都寫在相關文內,期與讀者共鑑。
作者慶幸並非久廁上庠,否則未必可以如此順乎學術良心,秉乎士子良知,說一些很多學者都不敢說的話。此書的本意,正正是要說一些了無畏懼的良心話。殷冀大家互勉互進,在各自崗位敬誠其事,同心仿效先輩前賢,為這個早已扭曲至不成常形的世界,多傳木鐸,盡振金聲。如此,學林幸甚,蒼生幸甚!
作者簡介:
塵紓
•文史專欄作家
•師從汪經昌、徐復觀等「新亞」學者
•資深藝評人
章節試閱
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遙念吾師徐復觀
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提及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老師個子不高,不胖不瘦。……外形上,他沒有錢穆的儒雅,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言談上,沒有徐復觀的威儀,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
「新亞」諸師之中,徐復觀是影響筆者最深的授業師,而他在外形言談上常常予人威儀抑抑,震懾人心的感覺。
余生雖晚,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而當中的徐師,於筆者而言,倒是真的尾班車。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既屬有緣,更感有幸。
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
遙念吾師徐復觀
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提及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老師個子不高,不胖不瘦。……外形上,他沒有錢穆的儒雅,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言談上,沒有徐復觀的威儀,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
「新亞」諸師之中,徐復觀是影響筆者最深的授業師,而他在外形言談上常常予人威儀抑抑,震懾人心的感覺。
余生雖晚,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而當中的徐師,於筆者而言,倒是真的尾班車。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既屬有緣,更感有幸。
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
黌舍翹楚傳木鐸 學林大儒振金聲
真不意,第一本刊行的拙作,居然是《學林踽樂》,而不是《梨園偶拾》,也不是《閒話音樂》。
回望三十年硯田樂,以筆名塵紓所撰的戲曲文章,少說也有兩千篇,而以其他筆名寫就的音樂文章,又何止一千?雖然歷年愛看拙作的朋友不斷催促我把已刊文章結集成書,但老是提不起勁。或許,縈繞胸臆的那種闌珊之感,就是對戲曲以至音樂現況的無奈之嘆吧。惟有把疊疊文稿束之高閣,暫且免提。
每篇一位 文史名家
二零一六年退休之初,應某報館誠邀,為其「人文歷史」專刊撰寫文章,題目任定。三年下來,合共寫...
黌舍翹楚傳木鐸 學林大儒振金聲
真不意,第一本刊行的拙作,居然是《學林踽樂》,而不是《梨園偶拾》,也不是《閒話音樂》。
回望三十年硯田樂,以筆名塵紓所撰的戲曲文章,少說也有兩千篇,而以其他筆名寫就的音樂文章,又何止一千?雖然歷年愛看拙作的朋友不斷催促我把已刊文章結集成書,但老是提不起勁。或許,縈繞胸臆的那種闌珊之感,就是對戲曲以至音樂現況的無奈之嘆吧。惟有把疊疊文稿束之高閣,暫且免提。
每篇一位 文史名家
二零一六年退休之初,應某報館誠邀,為其「人文歷史」專刊撰寫文章,題目任定。三年下來,合共寫...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黌舍翹楚傳木鐸 學林大儒振金聲
「新亞」學者系列
風趣幽默 從不吹噓 常念吾師汪經昌
(配稿)汪師同門盧前 詞曲論著簡介
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遙念吾師徐復觀
講學認真 語帶笑容 敬憶吾師全漢昇
廣博精深 嚴肅凝練 嚴耕望史學卓然大成
錢穆親授 瀟灑爽朗 仰思所長孫國棟
經史兼擅 沉默寡言 遙敬陳垣弟子牟潤孫
學者作家繫一身 緬念業師王韶生
哲學大儒牟宗三 隨地吐痰視等閒
二十世紀文史名家系列
經世致用一儒生 務實文膽潘小磐
長憶恩師「橋伯伯」 遙敬祖師爺Kitto
各族本同根 齊心創新天 民族史學者徐松石
學...
「新亞」學者系列
風趣幽默 從不吹噓 常念吾師汪經昌
(配稿)汪師同門盧前 詞曲論著簡介
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遙念吾師徐復觀
講學認真 語帶笑容 敬憶吾師全漢昇
廣博精深 嚴肅凝練 嚴耕望史學卓然大成
錢穆親授 瀟灑爽朗 仰思所長孫國棟
經史兼擅 沉默寡言 遙敬陳垣弟子牟潤孫
學者作家繫一身 緬念業師王韶生
哲學大儒牟宗三 隨地吐痰視等閒
二十世紀文史名家系列
經世致用一儒生 務實文膽潘小磐
長憶恩師「橋伯伯」 遙敬祖師爺Kitto
各族本同根 齊心創新天 民族史學者徐松石
學...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