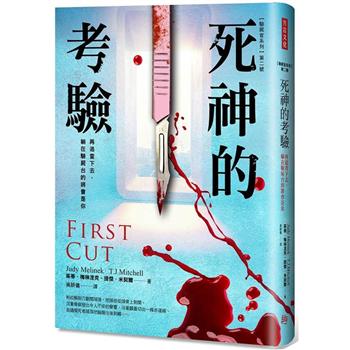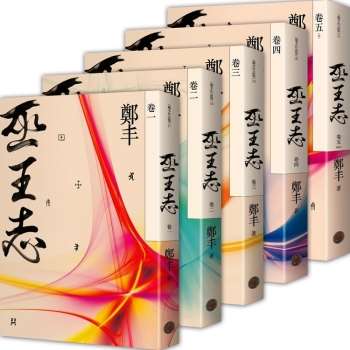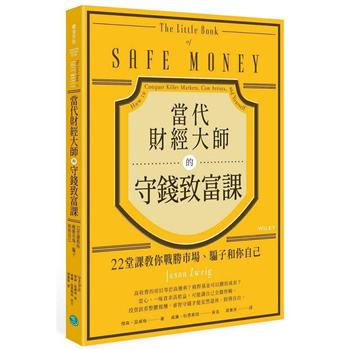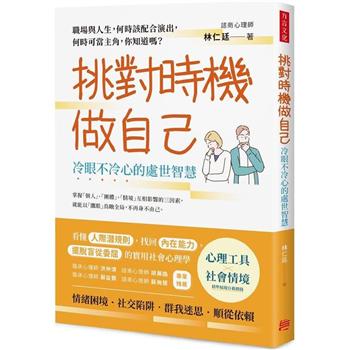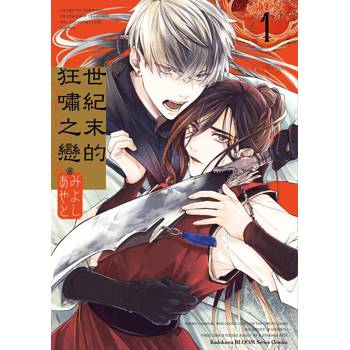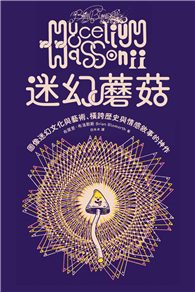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Benjamin Yalom的圖書 |
 |
$ 379 | 心靈時刻:亞隆與22位來訪者的一期一會【博客來獨家書封版】(首刷限定:歐文亞隆父子印簽及給台灣讀者的一段話)
作者: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Benjamin Yalom) / 譯者:鄧伯宸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日期:2025-05-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96頁 / 14.8 x 21 x 1.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469 ~ 1102 | Hour of the Heart
作者:Irvin D. Yalom,Benjamin Yalom 出版社:HarperCollins 出版日期:2024-12-10 語言:英文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