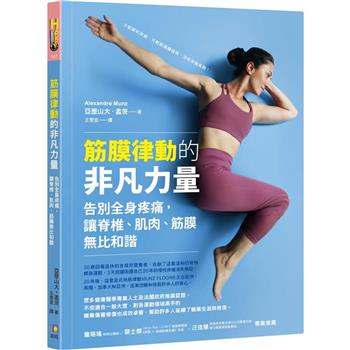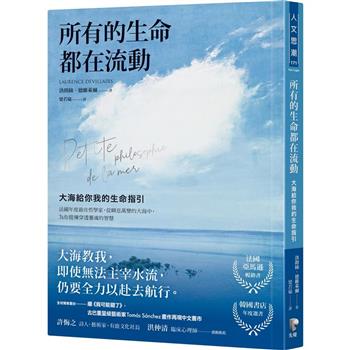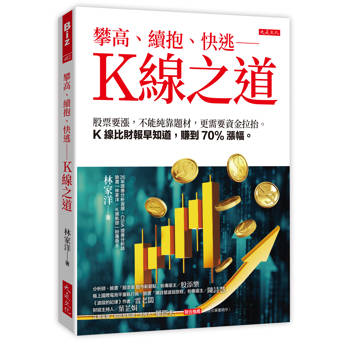要談二十世紀的代表人物,第一號宗教人物捨「達賴喇嘛」還有誰呢?
在一般人眼中,達賴喇嘛是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領袖,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在藏傳佛教徒眼中,他是格魯派的法王,也是觀世音菩薩的轉世;在流亡的西藏人眼中,他則是帶領西藏人民歸返故鄉的精神導師。
這樣一位睿智、幽默與親切的和平主義者,究竟是如何長成和養成的?他的少年時代和我們一般人有何不同?他成長的西藏高原有著怎樣的景緻?他的藏傳佛教信仰又帶給他怎樣的文化承傳?而他生來注定的法王地位,又如何轉動他的命運之輪?他一路走來,又有什麼樣的訊息預告著他這樣不平凡的人生?
他,生於小農之家,當他被認證為達賴喇嘛十四世時,就得在與世隔絕的拉薩岩山上的布達拉宮,接受啟蒙,熟讀佛經和學習禪修。在這房室成百上千的古老建築中,他這個小孩,雖有一群出家人陪著他念經,有著比任何西藏小孩還多的西洋機械玩具和新奇玩意兒,卻遠比任何小孩都還孤獨和不自由。
中國入侵,他親眼目睹了和他的信仰相悖的暴行,他被迫提早告別少年時代,擔負起整個西藏民族的興亡。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淚點,關鍵的1959年,也就是他從西藏出走踏上印度的那一天,達賴喇嘛就再也不是專屬西藏人民的領袖,他已選擇走向世界,讓全世界認識了西藏,認識了藏傳佛教,那時的達賴喇嘛才不到二十四歲。
透過作者獨特的敘事角度和達賴喇嘛姪子凱度頓珠所提供的第一手精采歷史照片,影響達賴喇嘛的關鍵人物將一一現身,悠悠帶引我們走進達賴喇嘛告別西藏高原的重要歷史時刻。
作者簡介
珂蘿德.勒文森(Claude B. Leveson)
達賴喇嘛的朋友,可說是最了解達賴喇嘛的人之一,這位記者熱中於西藏議題,出版過許多關於西藏的著作。學生時代受的是斯拉夫學和東方學的訓練,翻譯作品包括俄國作家曼德爾斯坦姆(Mandelstam)、賴因可(Amaury de Riencourt)和贊米亞亭(Zamiatine)等人的作品,以及達賴喇嘛的法語集。

 共
共